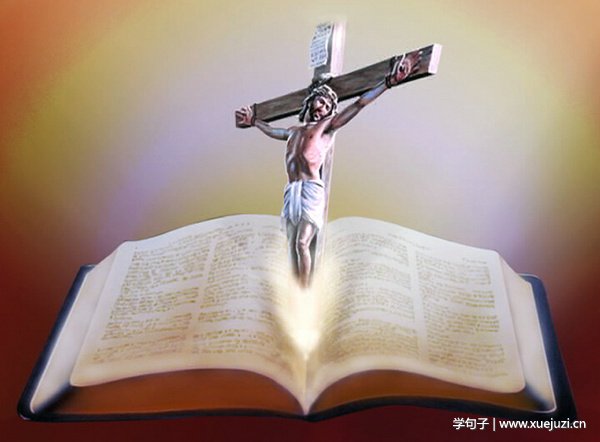
去一家店里看衣服,卖家为我推荐一件中长雪纺衫。这件衣服,我穿在身上虽舒服,但那颜色和图案有些不喜欢。
想起一位相熟的店家说过的话:“我发觉你只适合灰呀黑的,或者黑白配,或者咖啡色,太鲜艳的不行。”
我深以为然。
所有光鲜亮丽的颜色似乎都不适合我,我不认为这是自己的着装习惯使然。我以为,每个人所能承受的颜色其实很有限,这并非单纯由肤色所决定。大概人的内心总会外化为一种表情、神态,而这些东西都是无声的语言,它会发散出一种气息,这气息对有些颜色是排斥的。所以挂在那里很好看的衣服,穿在身上却未必搭调。
我喜欢灰色,深灰、浅灰、蓝灰都行;我也喜欢白色,米白、象牙白、乳白都行。
在我眼里,米白、象牙白和乳白,才是纯正的白色。而雪白,则不是。因为雪白,是冷色调。
冷色调,也许是我生命的色调吧!
冷色——总是透着几分凉意。秋冬之际,经常有人会问:“你是不是很冷?”夏天里有朋友说:“看着你就凉爽。”我无言以对。而我无意中起的网名——月照寒潭,似乎更加印证了这样一种印象。
生之基调因何而定,因何而起,很难说得清楚。哪些事成全了你,哪些事败坏了你,谁能记得分明呢?
小时候对于衣服是绝对没有选择余地的,倘能遮体,不破不露,已经是令人艳羡的了。
母亲是个极要强的人,即使深夜不眠,也不会让我们姐弟三个穿着破烂的衣服鞋子去上学。无数次看着她在昏暗的灯下缝缝补补,拆了棉衣做成夹衣,长袖衣服破了剪成短袖,露了洞的地方打好补丁。看着她在闷热的夏日纳鞋底,听着麻绳穿过鞋底时刺啦刺啦的声音,看着她大颗汗珠渍湿了额前的头发……
母亲有时会抱怨:“浑身上下好像都长了牙,刚做的新衣新鞋,好歹就给咬坏啦。”每当这时,我们姐弟都不敢做声,其实即使再怎么不懂事,也明白母亲一针一线的不容易。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她的辛劳。所以母亲让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哪怕再怎么不喜欢。而且对每一件衣服鞋袜都万分珍惜,唯恐穿坏。
记得当时我在离家三里的外村读初中。父亲在供销社上班,供销社经销一种进口化肥,他看到装化肥的袋子是一种类似于人造棉的一种布料,就收拾了两个带回家,母亲买了颜料把它染成了粉红色,精心地给我裁了一件短袖衫。那件衣服虽然质地柔软,穿着很舒服,但看着粉色无法遮盖的黑字还是有几分疑忌。穿着这件新衣去上学,外村的几个男生便在我身后指指点点,然后齐声喊着“日——本——产——”。我的头嗡的一下似乎受到了猛击,脊背也随之发热,那一天不知如何熬过……
而且,自此,我便落得了个“日本产”的绰号,时不时地被那几个同班男生喊叫。
从小就不会和人吵架的我,就像祥林嫂带着额头那个伤疤一样带着这个绰号,渡过了整个初中阶段,它带给我的耻辱是刻骨铭心的。我没有因此辍学,其间的隐忍,现在想来令自己骇然。
有些事我从不对人提及,即使对父母也不说,只在无人处舔舐伤口。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性情中有很阴郁的一面,对遥远的往事中那些曾经的伤害不能秉持一种宽悯的态度彻底释怀,而是耿耿于心,孤寂落寞时翻动,仍会被飘飞的尘埃惹动伤怀。
也反思那时为何对一个绰号如此在意,是我太过敏感,太过脆弱吗?
目睹女儿这一代被人呼之为大虾、蚊子之类总是会轻松地面对,自然地应承,似乎叫什么也无关痛痒,不过代号而已,无关面子。
优裕的生活赐予了她们生命的底气,一种发自心底的自信,使他们从里到外散发着阳光。
曾经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同女儿讲起我那段关于衣裳的尴尬记忆。惊诧和怜悯,清楚地写在女儿的脸上。我在心里说:“妈妈一定努力,争取永远不让你受到这样的困窘。”
经常会主动给女儿买衣服,虽然她自己一直忙着学业,不太在意衣着打扮,可我还是希望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拥有一个完好的花季。我被生活剥夺的'东西,总想极力在女儿身上得到补偿。恐怕每个母亲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其实我知道,她的花季被另一种东西——学业剥夺了,这是另一种残忍,我依然无奈。或许每一代母亲都有属于她们的无奈吧!
我们生逢那样一个时代,贫穷像一把刀,一点点剥去了我们的尊严,让我们过早地看清了生活的本质。那一件印着黑字的粉红色上衣,就那样定格于我生命的履历,再也无法抹去。它让我对一切色彩明艳的衣饰都避之唯恐不及。
我也曾因此怨怪母亲,现在明白,那是贫穷的过错,是日子的无情,而不是母亲的。实际上,母亲曾经竭尽心力地保护我不受伤害,而我终究未能幸免。也许至今她也不知道,那一件印着黑色大字的粉色上衣带给我的伤害有多深,它残忍地践踏了我的自尊,踩碎了一个花季少女关于美丽的所有想象。多年以后,我一直都不敢穿比较招眼的衣服,总想躲在一个别人不太注意的目光的角落,默默无声。
长久的自卑和胆怯,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吗?
生活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垫底儿的,抽掉了一些必须的东西,就会失了底气,失了镇定与从容。特别是对于女孩、女人来说。
一直喜欢棉麻类的衣服,喜欢那份舒适随意,喜欢那种朴质天然。前年,买了一件驼色针织开衫,披肩式的宽松样式。一个同事说:大姐怎么买了一块麻袋片披上了?我一笑“怎么啦,我就是喜欢这麻袋片的舒适随意。”他又补说:“大姐穿个麻袋片也美丽!”不禁莞尔。
我知道,我该和过去的一切彻底和解了。那些自己穿着补丁衣服嘲笑我的坏小子们,如今都不如我活得优雅,他们人生的狼狈和尴尬,或许也是注定的吧?记得我们班上那个最优秀的男生从未喊过我的绰号,他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去年高中同学聚会时,我道出了当年对他特别的好感,但没有说理由,他应该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人的天性品质或许会影响一生的命运,那些无聊、厌学、放任、恶劣的孩子,终究不会有大出息。他们或许会很有钱,但很难活得高贵(我是说骨子里的高贵)。这也许是他们的生命底色吧。
总觉得一个人天性不善良,是一种很严重的生命缺失。而没有律己的习惯也会败坏固有的聪明才智。所谓从小看大,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个春天的日子里,忆起旧事,发些感慨,如此而已。
忽然想起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的一句话:“记忆会从内测温暖你的身体,同时又从内测剧烈地切割你的身体。”被切割,或许会对过去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知。
年轻的同事要我传授如何做到好心态的秘密。其实我并没有比一般人命更好,我出生成长在物质和文化都极度匮乏年代的偏远农村,少女时我没有令少年倾心的俊俏,青春时期我的自信被现实无情地抛弃,我嫁的夫家一贫如洗,丈夫也是壳厚得一针扎不到底,我在职场上曾被几个上海女人折磨得不能坚守,也曾经为同僚间的尔虞我诈夜不能寐,我父母的早逝在我心口留下经年不愈的伤。但是我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哪里跌了一跤,爬起来看看是什么将我绊倒,然后继续赶我幸福的路程。也许有人认为为此我要付出多少的努力,需要多大的勇气,其实不然,做到这些对我来讲,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这源于我太阳般明亮的生命底色,那是生命的源动力。
因为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所以我得到的爱和关注更多些,我再闹父母也没有把我扔给长姐长兄带,我记得很大还在吃母乳,直到五六岁还和父母同住,我记忆中的幼年都是在妈妈温暖的怀里。在那个年代我可能营养不良,但对爱的需求确是充分的满足,幼年时期充分的爱为我的人生打下了明亮的基调。我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足够的关注和爱,让我的人生充满亮丽的色彩。有一个从事心理行为学方面培训的讲师,女儿三岁了还在给她
人的幸福感跟金钱和财富到底有多大关系是讨论不清楚的话题,但和生命的底色确有着直接的关系。生命的底色形成于我们的婴幼儿时期,尤其是三岁之前,这底色是明亮还是灰暗,与物质没有任何的关系,婴儿期需求充分满足的孩子,底色就是生命原本的`亮丽色彩,而有多少的不满足,在这底布上就有多少的阴霾,再多了就连底色也变成灰暗的了。要知道这底色对人有多重要,有着明亮生命底色的人也会有创伤,也会有阴云密布,但一旦散去,漏出来生命底色便是阳光灿烂。他们的生命像阳光般明亮,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也都如太阳般温暖照亮着别人。而如果底色是灰暗的呢?无论曾经有过多少温暖和欢喜,消散之后挥不去的依然是忧伤阴郁。“谁敢说一个笑容可掬的人,其灿烂表像下不会是一张流着泪的脸?”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一定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无数心理学家在不停呼吁,给孩子他们应该得到的关注。因为这关乎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旅程。一位大师在他的书里写道: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拥有一种品质,那么请祈
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在中国如此不普及,真是个悲剧。也许这发源于西方的人文科学总有一点神秘,也许心理学家都过分的理性,写出的文字晦涩难懂,而可以写出打动人心文字的文人又太过感性,跳不出自己认知局限,走不进这门理性的学科。这门学科实际非常易懂,但又对人生有如此重要的指导作用,虽然不是让我们摆脱所有烦恼,但至少对我们孩子的教育会非常受益。
很多我们没有记忆的幼儿时期的经历,全部被填入了生命的底色,而我们长大后全部的努力和经营,都是在这块底色上构建搭起。比如有的人很难给家人拥抱,源于他婴儿期没有得到母亲足够的拥抱,人给不了自己没有的东西,正如没有吃过梨子的人,他不懂得他的甘甜可以消除病痛。得到充分关爱的婴儿长大后可以关爱家人,因为他们有。而没有被充足关爱的婴儿,长大后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麻木和冷漠。
严重不被满足的孩子,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会积累仇恨,所以很多人会恨社会恨别人,再严重就是报复,那都是世界欠了他的,小时候没有得到他该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这在那些有寄养和遗弃经历的孩子身上,不难被证明。报复心理也并不全是穷凶极恶的暴徒持枪杀人,这种心理渗透在生活中。有个母亲听到孩子哭会有快感,有的家长教训孩子时会露出得意的笑容,这都源于小时候同样的创痛。自我感觉敏感的人意识到这种不正常的情绪,会马上停止对孩子的这种报复,然而又有多少人连感觉都找不到呢?所以性格会遗传,仇恨更会。每个父母都爱孩子,但当一个人心里充满的全是世界欠他的东西时,他能拿出来的又能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底色已经是灰暗的颜色,也不意味着要灰暗地度过一生。只要努力,只要不放弃,多和自己的内心联系,慢慢体会到自己的感觉,就可以将底色上的灰暗一块块除去。也许需要付出多一些的努力,但那完全值得。任何人都有幸福快乐的机会和可能,只要自己不放弃这样的权利。
秋日的早晨尤其的清爽,美美地在故乡的静夜睡了一宿,充足而恬静的睡眠像一场细雨,洗净了多年在城市里堆积的风尘和压抑,站在场院上,温热的阳光透过泡桐树的枝叶,漏下片片亮黄,一旦从林立的钢筋水泥空间里走出来,转身之际,发现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才能深刻地触摸到灵魂的柔软处,那一瓣日渐消瘦的记忆之花和清澈如秋空的明朗豁达。
上小学三年级时,在书本上,认识了大海,海的一望无边,海是蓝色的自那时起,常常会仰望蓝天,想象着自己到了海边。我奔跑在净蓝的天底下,大声地呼喊,尽情地欢笑,当跑得浑身无力时,就滚倒在田埂边,吮吸青草的芳香,只要一伸手,就可摘到两三朵蓝色或黄色的野花,贴近鼻翼,清香阵阵。闭上眼,幻想自己长大后躺在海边的沙滩上,风吹乱了我的头发;睁开眼,碧蓝如洗的天空仿佛就在上方,朵朵白云如棉花般,携带着我的梦想,轻盈地飘向远方。
那种对蓝色和白色着迷的程度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裸露无遗,连自己穿衣服也钟情于蓝,纯棉的蓝花布裙子,一直到现在还时常穿着。记得我照的第一张照片,就是穿了一件蓝色底子上织着白碎花的棉布衬衣,那一年,我11岁。
当我还在睡梦中时,母亲在床边叫着我的小名,我睡眼惺忪,模糊间看到母亲手里的一件蓝底白花的新衬衣,开心得一跃而起,母亲给我穿上新衣服,笑着说,真合身。我低头扣着那一排圆圆的浅蓝色纽扣,心里喜滋滋的,昨晚听父母说,大伯要给我们拍照,所以连夜清扫了屋前的场地,一尘不染的样子,晚饭后,大大小小近二十个人好像到了过年的光景,围坐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动人的笑容。
大伯居住在上海,每次回乡下,总会带来一些新奇的事物。我看着他手中的照相机,心中迷惑不解,这么大一个东西竟然能装进我们一群人。大伯笑呵呵地让我们几个小孩在前面蹬着,他把照相机安置在一个架子上,嘴里说着话,手却灵活地动作着,然后,让我们都别动,保持微笑,他迅速跑过来,站到刚才空出的位置,只听见喀嚓一声,大伯说:好啦。"
大伯又给我们单独照相,我说,我要和蓝天白云拍在一块。他笑了,说,好,可是,拍出来的照片是黑白的啊。我再次迷惑,明明这个世界是五颜六色的,怎么到了大伯的照相机里会变成黑白的'?以致我那张照片上的神情一片茫然。直到后来出现彩色成像的相机,我才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和大伯的相机无关,和这个世界有关,和人类有关,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思考,依着一些线索去寻求万事万物的神秘之处,可往往会迷途而返,无法真正获得通向答案之门的钥匙。
打开我的相册,有一组照片总是令我欢欣激越,那是年轻时第一次在海边游玩拍的照片,天空和大海的蓝是如此接近,如此神奇,这里的蓝和白真实得无与伦比,白云在蓝天上不断地变幻出各种姿态,组合成一幅幅洁净动感的画面,或聚,或散,奇妙莫测,面对着这样恢弘深邃的生命意境,沉静凝思,有些解读总在成长中越来越清晰,而那一刻,在个体存在的天地间,年少时的困惑重现,显得笨拙无能,连一个赞美的词汇也找不到,只无端地走进了一道谜里,无法抽身。
记忆中的美,就像行驶在海上的快艇,乘风破浪,给我一种真实的欢乐,灵魂自由地飞翔在蔚蓝的天空里,顾盼的光芒在瞬息万变的色彩变迁中徘徊,流连。当这种感觉栖息于心灵深处时,觉得还不能完全精准地再现自己的感知,一刹那的最初的感动,强烈得会无法把握幸福的体验,凝视着震慑心灵的蓝和白,一切纷繁自体内剥落。在执笔的迟疑之间,流失了本该喷薄而出的热情,在传递心声的甬道上,遇见了无数次的梦想和挫折,能体验的,能明澈心扉的,也就是定格在生命版图上的那神秘色彩了,其它已经不再重要。
回转故里,在欣赏久违的蓝天和白云的同时,更多的是领略多年来被污染了的生命底色,常年在逼仄的天空下生活,忽略了那开阔与透明的蓝天白云,僵硬的肢体在经年累月中麻痹得连自己也不认识,渴望被柔软而清明的事物包围,渺小的我需要重拾当年的梦幻和灵性,让渐渐老去的躯壳注射进新的活力,那么,即使坐在城市办公室的窗口,于狭窄的一片,看云卷云舒,也会温暖地联想那蓝和白的广阔悠远,清明纯净。
走进田野,踩在沾着湿湿露水的草丛中,蔚蓝色天空下的大片大片的水稻成熟在望,隐约可闻稻花的香气,挥手握住一把,似是活了,如青烟浮动飘逸。在这广袤的背景里,纵然带着相机,也少却了调试镜头的念想,只希望自己回到三十年前的光景,肆意地奔跑在田埂上,向生命作一次小小的挑战,在蓝色和白色的世界里享受生命的美丽,不要任何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