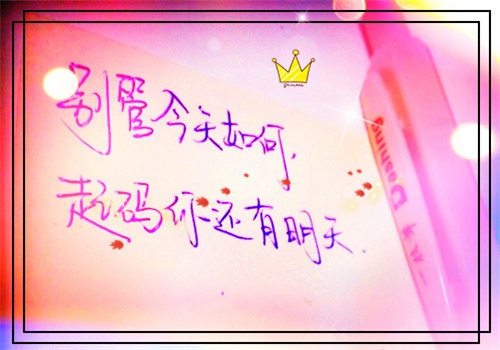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大致有三种类型: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其中,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最深重。在小说《明天》、《祝福》中,鲁迅先生成功塑造了单四嫂子、祥林嫂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她们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精神摧残,揭露了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
一 天生苦命,饱受摧残
1.单四嫂子的形象。
单四嫂子生前守了寡,为了生存,只能靠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自己和他三岁的儿子,在深更半夜就开始张罗明天的生活。艰难与困苦并未让在饿死边缘挣扎的单四嫂子对生活失去信心,皆因自己三岁的儿子——宝儿。丈夫死后,所有的寄托和希望,都押在了宝儿身上。然而,厄运却向她袭来。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单四嫂子失去了希望,她没有了明天,面对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梦里,希望在梦里与宝儿见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 ,但明天又会怎样?“作者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却通过种种迹象,把一个残酷的世界,摆在了读者面前。”
2.苦命的祥林嫂。
在丽春之日,祥林嫂的丈夫夭折。严厉的婆婆决定把她象商品一样卖掉。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祥林嫂逃到鲁家做工。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强嫁给山里人贺老六,并有了儿子。可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上”、孩子也“给狼衔去了”。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 她再次来到鲁家,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在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凄然死去。
二 封建礼教,毒害妇女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宣扬“以贞励天下”的伦理道德观,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对于不节烈的妇女,不但给其加上“害了国家”的罪名,还造出许多无端的故事来加以恫吓。长期以来这种封建节烈观宛如一把杀戳妇女的利刀戕害着许许多多善良的女性,单四嫂子和祥林嫂就是这把利刀下的羔羊。
祥林嫂和单四嫂子一样,都是死去丈夫的寡妇,她们有着相同的命运:首先是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下,她们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在家从夫,夫死从子”。其次是她们都是靠自己劳动生活的寡妇。祥林嫂在鲁四爷家当女佣,出卖自己劳动力,养活自己;单四嫂子是靠纺纱糊口。第三是她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都是被人欺负的奴隶。祥林嫂被婆婆抓回卖给贺老六,她成了换成八十千吊钱的物品,蓝皮阿五借故帮单四嫂子抱宝儿,只是为了占点便宜。第四是她们都遇上悲惨的恶运。丈夫早逝,只有寄情于儿子,而儿子又夭折,鬼神把她们推向更悲惨的境地。
但是,她们又有着自己不同的遭遇。
在《明天》中,通过凸现出神祗、庸医、无赖、蓝皮、邻居以及众帮人,构成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封建礼教的桎梏,尤其是在那塞满诱惑、欺骗、暴力的混浊险恶的环境中,单四嫂子不是死在悬梁自戕的绳索上而是淹死在这个封建礼教的桎梏下。
《祝福》中的祥林嫂,首先是族权和夫权统治下的牺牲品。从她嫁之日起,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丈夫死后,她想摆脱夫家的束缚,只身逃到鲁家做工。然而祥林嫂自食其力的理想,在族权统治下只不过是一个梦。她被当作一件物品卖给山里的贺老六。第二个丈夫贺老六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
其次,祥林嫂是神权摧残下的殉葬品。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为了避免因“失节”而到阴间被“锯开”,祥林嫂相信所谓“神”的力量。她将辛苦积存的十二千大钱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了门槛,以求“赎了这一世”的罪名,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和自我安慰。但她仍然是一个不洁之人。鲁四爷歧视她,不准她参加祭祀活动,怕败坏风俗。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使她的精神彻底的崩溃。
鲁迅正是通过单四嫂子和祥林嫂的形象,谴责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劳动妇女的吞噬、绞杀,形象地告诉人们,要想改变中国劳动妇女的命运,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积极彻底地推毁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推翻“节”和“烈”这两座压在妇女头上的'大山,受迫害的妇女才能真正解放出来。
三 反抗无果,难逃厄运
面对封建礼教的种种迫害, 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又是怎样做出了不同形式的反抗呢?
我们再来回顾单四嫂子在丧夫失子之后仍然呆呆地“等待明天”,不难看出,面对封建礼教的迫害,她总是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
对于单四嫂子的逆来顺受,祥林嫂进行了盲目的反抗,结果却是惨重的。为了逃避婆家的难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抗婆家的捆绑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为了摆脱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临死前大胆的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些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她被卖改嫁时的出格反抗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是受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临死怀疑鬼神有无,是她听了柳妈的迷信话语,怕死后被据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因此,她的反抗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抗争是为了做稳奴隶的抗争,她的抗争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
鲁迅笔下这两个主要女性的悲剧人生,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鲁迅剖析的是国民的灵魂,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精神,挽救国民的灵魂;同时,也预示了社会制度必须要革命,国民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鲁迅深刻的思想,他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我们今天重读鲁迅的小说,继续研究其思想内涵,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 要】鲁迅毕生关注着女性的命运,思考和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他将妇女解放作为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内容,以妇女解放为反封建的突破日,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最深刻的批判。本文通过分析鲁迅作品中妇女的生存困境,展示他对女性悲剧的态度,探讨他创作中对女性摆脱悲剧命运出路的思索。
【关键词】鲁迅 女性主义悲剧 生存困境 女性解放
鲁迅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具体反映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对于悲剧女性的态度,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成为反封建斗争中争取女性解放咀嚼不尽的话题。
一、鲁迅创作中对女性生存困境的艺术再现
在鲁迅笔下的文学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无爱的人间”。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压迫,正常的人性被扭曲变形,失去自我;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下,她们除了被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所禁锢,受尽迫害,还要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最后悲惨地了却一生。这无爱的人间,成了女性逃不出的死亡之谷。
(一)道德习俗的奴役
《祝福》中祥林嫂是由整个鲁镇无所不在的道德习俗窒息而死的。所有鲁镇的人都是道德习俗的奴隶,并以共同遵循的道德习俗准则来衡量处于鲁镇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更为悲哀的是,祥林嫂自己也被鲁镇这样的道德习俗所主宰了。她丝毫不敢怀疑这种道德习俗的荒谬性,而是试图用自己的言行,唤起人们原谅她为了生存才迫不得已违背道德习俗的过失。
这是一个怎样的荒谬社会:社会在剥夺祥林嫂守寡的权力同时,却将祥林嫂不守寡的所有“罪责”都推到她身上,不允许她有任何“救赎”的机会,一步步的将她逼向死亡的境地。在这场共同的道德谋杀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凶手,都自认为是正义的道德法官。当一个社会与民族对亲手炮制的悲剧视为理所当然或视而不见时,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些受奴役的女性自然也就终老于这种窠臼之中了,或麻木不仁,或痛不欲生。
(二)权威的蒙蔽
爱姑的生存环境要比祥林嫂优越得多。爱姑的父亲庄木三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在对待离婚问题上,爱姑开始是拒绝离婚的,而支撑她这种观点的力量来源于她的生存处境优势。但七大人凭着自己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权威性慑服了爱姑,让她陷入丧失主见的境地,放弃了一直坚持的拒不离婚的主张。
鲁迅对爱姑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女性要想获得独立,必须打破对束缚自己的陈腐权威的迷信,将决定自己命运的辨别权、判断权、选择权勇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女性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能指望权威替自己说公道话。
(三)爱情的束缚
《伤逝》中的子君作为知识女性,对把握自己的命运有着远比祥林嫂、爱姑更自觉的意识和追求,她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观,大胆地反抗社会道德习俗和亲权的干涉,发出那个时代女性反抗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的坚强与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追求爱情、反抗社会习俗的过程中,但她在获得了爱情、与涓生同居后,也陷入了具体的生存困境中,原本由自己主掌的命运不再属于自己。
子君的悲剧命运与她对待爱情的态度密切相关。作者在此处向我们表明“时代已给女性指出了冲破父权制家庭的道路,可是,却没有让她们成熟到如何在新的两性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因而她们在摆脱了一种形式的束缚后,又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羁绊。
二、鲁迅对女性悲剧的态度
鲁迅笔下的女性没有哪一个是幸运的,她们的悲剧结局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仅仅为表现而表现。这种“万艳同悲”的现象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而被塑造的。鲁迅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深切关注妇女问题,苦苦地探寻着女性解放的道路。
(一)呼唤思想解放,实现人格独立
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把女性牢牢地固定在“贤妻良母”的位置上,使其循规蹈矩,“忘我生活”,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完全丧失了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和“独立”。几千年因袭的传统思想,使女性心甘情愿地固守在封建礼教、封建习俗所划定的角色上,她们事事依附、盲从,甚至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而不惜摧残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鲁迅从拯救迷途中的苦难女性出发,将批判的笔锋指向封建礼教,揭露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残害,希望能唤醒沉疴中的女性超度重负下的灵魂。
(二)倡导经济独立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呼声不断高涨,《伤逝》中的子君,就是受个性解放思想的感召而觉醒的都市知识女性,她那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人”的呼唤,使人禁不住“狂喜”。好像看到了中国女性“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然而,子君毕竟是中国传统女性,她虽有现代的追求,却又未能卸下沉重的传统思想包袱。婚姻自主后,子君心满意足了,她没有像其他新女性一样出去工作,掌握经济自主权,而是陶醉于自己的小家庭之中。
子君她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模式几乎无任何不同。鲁迅塑造子君这一形象的真实目的是他要告诉人们,个性解放并不等同于婚恋自由。妇女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必须掌握经济自主权。
(三)批判男性中心主义
首先,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均无属于自己的“姓”和“名”,杨二嫂、华大妈等名字是由丈夫的姓氏、排行加上具有年龄倾向的数目字而构成的,鲁迅笔下的寡妇也是如此。名字的缺失则意味着封建时代中国的妇女,从生到死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其次是男性意识对女性的伤害。《伤势》中,子君是不顾礼教的束缚、家庭的阻止与涓生走在一起的,可是当外来的打击——失业到来时,涓生发现“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于是他将自己的原因推给子君“现在忍受着这生活的压迫的苦痛,大半到是为她……”于是乎慨叹“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并以“无爱”为由将子君逼走,而在子君离开之后,又忏悔“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整个过程,涓生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来对待子君的,这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
三、女性摆脱悲剧困境的出路——女性解放
鲁迅在文学创作中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使反封建斗争达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他对女性生存困境艺术的再现从实质上揭示了悲剧的根源,即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女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获得女性解放。
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鲁迅一方面认识到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束缚妇女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沉重枷锁,并加以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鲁迅也清醒地看到,在几千年的因袭重负下,女性认同了“吃人”的合理性,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而这种弱点又恰恰妨碍了女性自身对解放的追求。
参考文献:
[1]李希凡.《呐喊》《仿徨》的思想与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陈鸣树.鲁迅小说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3]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王国缓.鲁迅论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