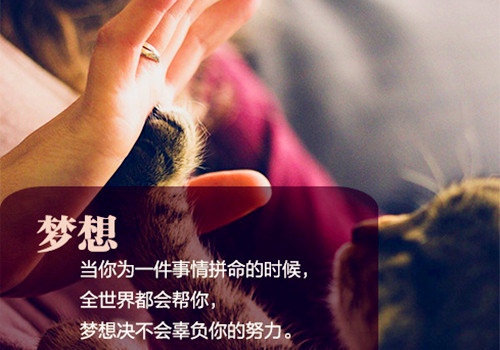普愿在他长达八十六年的人生中不仅创建了南泉禅院(道场),从而让中国的农禅制度得以扩大和升华,在其一生的弘法中,更是创作了一系列语录(公案),使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夜之间可以产生许多个暴发户,三代人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贵族。”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对人类经济生活所得出结论,同样可以归纳到中国佛教史上来。就像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异峰突起一样,在中国佛教中被称为精神贵族的中国禅宗,于这一时期更是表现出一种特行独立的品格,并培养出一代代具有人格魅力的杰出禅师。
中国禅宗自达摩发端,集大成者无疑是慧能一派。人们习惯于把曹溪慧能作为南宗顿门的开创者和思想先驱,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至江西马祖道一和湖南石头希迁这一代,才达到渐趋成熟的阶段。两位禅师在当时影响甚远,四方求法者纷至沓来,以至于形成后来人们所说的″走江湖″之说。
在马祖道一的弟子中,最让人难以忘怀,最具有个人人格魅力的无疑是南泉普愿禅师。普愿(748-834)郑州新郑人(今河南省新郑县),俗姓王,亦称“王老师”。因其长期弘化于池阳南泉山而被人习惯称为南泉普愿。普愿九岁跪请父母请求出家,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禅师受业,后又参学于多位祖师,因而使得他的禅法“言辞锋利,无不披靡”。但最后使他得究竟之法的却是马祖道一。追根溯源,马祖道一师从于南岳怀让,怀让是曹溪慧能的高徒,是普愿的祖师。由此可见,普愿的禅法出自于名门正派,是真正的禅门贵族。
一
普愿一生的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师事江西马祖道一求法时期;池阳开辟南泉禅院时期;因陆亘所请,下山至宣城一带开坛演法时期。
普愿在师事马祖道一时,追随在道一身边的弟子有数百人。在这些人中,不乏学有成就的高徒,如首座百丈怀海、有道一亲授袈裟的西堂智藏、有被人称作禅门明珠的大珠慧海、有破解迅猛,素以“弓箭手”称雄的石巩慧藏等。后来者普愿在同学中同样具有崭露头角的表现,被道一称为“独超象外”。
这位性情刚烈的北方僧人在他最初与老师马祖道一相识的日子里,即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范。一次在给僧人分粥的时候,马祖道一随口问了一句:“那桶里是什么?”在场学人无一敢答。对于那些平庸的学人来说,道一这样的祖师和权威,哪怕是一句极普通的问话,或许都深藏着无尽的禅意和智慧,所有的学人必然要对道一的一字一言作一番认真的猜度,唯恐答出错来。而初来乍到的普愿却对着尊敬的老师呵斥道:“这老汉闭上嘴,说出这样的话来。”在普愿看来,那桶里是什么,你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啊,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啊,这也用得着去问别人吗?在场的学人或许都被普愿的这种胆大妄为吓坏了,然而,正是这种不事权威,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和呵佛骂祖的禅风,与马祖道一一以贯之的禅门风格发生了奇妙契应,这也许正是马祖道一对这位不平凡的学生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所在。而普愿在突然中对老师的这种超乎寻常的斥责,恰如一柄凌空劈下的利剑,让所有的'学人在这种猝不及防的骂呵中顿然醒悟,从而明白,只有将深深隐匿于各种权威、礼仪、规范以及世俗常情等等厚重外衣下的原本活泼泼、光闪闪的心意彻底地显露出来,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问题,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才能获得心灵的真正解脱。
普愿的这种不事权威、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对待老师的态度上,同样也表现在他对待至尊至上的佛祖的态度上。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随老师道一以及同参西堂、百丈等人一同出门赏月,美好的夜晚激发了禅师们各自的想象。道一随口说,这样月朗风清的时分,做一点什么最好呢?西堂说,供佛最好;百丈说,坐禅最佳,唯有普愿拂袖而去,引得在场人面面相觑。于是马祖道一感慨说:经入西堂,禅归百丈,唯普愿超然于物外。
超然物外,正是禅师们所追求的至高的精神境界,也是历代禅师们启悟弟子的中心所在。禅,归根到底是要在内心里改变自己,让自己从一切现有的规范和束缚中解脱出来,进而以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这世上的一切,用自己的思考去认识这世上的一切,唯有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但多少年来,人们却被一切现成的法则障蔽了自己的双眼,迷失了自己原本活泼而自在的本性,从而让自己变成一部随世运转、人云亦云的机器。这是世人的执着,也是世人的悲哀。
二
贞元十一年(795),普愿离开自己的老师来到杏花江南的池阳南泉山(今安徽省贵池境内),不下南泉三十余年,带领弟子过起了自给自足的农禅生活。江南的山水,给了这位已了心意的杰出禅师更多的独立思考的品性,在南泉山,普愿依然以他的南泉普愿似的强毅禅风接引学人,化导众生。
虽然是师出名门,但普愿并不把老师们的禅法当作教条。“即心即佛”即出于他的老师马祖道一,然而,普愿却反其道而言之,他只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学人们也许是被这位古怪的禅师弄糊涂了,于是就有人问他:“连马祖都说即心即佛,你为什么要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呢?”普愿坚持说:“我就是要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难道有什么错吗?”谁也不能认为普愿的说法有错,《华严经》就说过“心、佛、众生(物)三差别”。世上万物,其本质是相同的,表现则各有差异。禅,只关心本质,不关心其外在表现。是和非,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件事后来传到马祖那儿,奇怪的是,马祖竟也改变了自己的说法,从此也说起“非心非佛”了。并非马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而是他从普愿的说法中意识到,那些愚笨的学人早已把一句“即心即佛”奉为了圣典,并不加实证地认为:心就是佛,心就是道,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字和理念上的执着,非反其道而行之不能改变那些学人的执着和愚顽。
就像心与佛的同异一样,什么是“祖师西来意”,这曾被无数学人困扰过的问题同样也曾困扰着普愿的弟子们。据说当初有人问马祖道一这一问题时,道一推说:“我今日头痛,可问西堂智藏去。”僧去问智藏,智藏说:“今日没有闲功夫,你去问海师兄。”僧问怀海,怀海说:“我不会。”非是这些禅师们没闲功夫或是不会,而是禅师们觉得,达摩祖师千里迢迢西来之目的,就是要让你等凡夫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在这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里领悟属于自己的真理所在啊,为什么总是要问个不休呢?祖师西来之意与你又有什么干系呢?很多年后,当普愿的弟子赵州和尚再次把同样的问题提到普愿面前的时候,普愿干脆离座而去。无论是道一,还是普愿,他们所要告诉人们的是:人们,千万不要在言语上兜圈子,不要在义理上生执着啊。天晴就要出太阳,下雨地上就会湿,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让祖师们来下定义呢?
禅不可说;禅,完全是一种个人的体验,而对禅的体验又不能像其他的知识那样在师生间用口和文字加以授受,这就是禅门中历来认为有禅而无师的道理。于是,就有了呵佛骂祖者,就有了烧佛取暖者,就有了面对祖上的圣典拂袖而去的凛然正气,因此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个个杰出禅师的人格魅力。
劈下的利剑,在猝不及防中斩断了凡夫的执着之念,砍断了那些执着于理念的学人们精神上的种种羁绊。而普愿自己也常常以刀来譬如自己。据说有一次外地求法的僧人前来问路,恰遇普愿在野地割草,当那问路的僧人问如何去南泉院,谁是普愿禅师时,普愿没有正面回答那位问话的僧人,而是举起了手中割草的镰刀:看到这刀子了吗,我就是啊。
禅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正所谓“一说便是错”。作为“王老师”,普愿一生的教诲就是要让学人们丢掉一切执着之念,用自己心意去认识事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普愿这把锋利的刀子不惜做出被后来的无数人褒贬不一的杀生行为,这就是有名的南泉斩猫。在那些执着于外界事物的凡夫面前,一切有形的事物都会成为障蔽心意的桎梏,乃至一草一木,一线一针。于是,就发生了东西两堂僧人争夺一只猫儿的闹剧。对于那些连一只猫儿也不肯放下的僧人来说,又何谈独具智慧和人生的解脱呢?于是,当两堂的僧人为那只可怜的猫儿争吵不休的时候,普愿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斩猫的动作。执着的对象消失了,“一切有相,皆为虚妄”(《金刚经》偈句),学人们执着外相的意识也在这刀光剑影中警醒了。在普愿看来,所损失的是一只无辜的猫,还有自己被无数人指责的杀生的罪名,但他却觉得,能让东西两堂乃至后来无数的学人从此警醒,那是比什么都合算的。普愿让人们懂得:凡事不可执着,最要紧的,还是要像恰好前来的赵州一样,将自己的鞋儿顶在头上扬长而去的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这正如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先生所言:禅不是教化,禅是要把一切羁绊彻底抛却。(《禅者的思考》)。
在南泉普愿心目中,一切现成的规矩都是人心的羁绊,人必须冲破传统的樊篱,将无限盈然的心意展现出来,以确立自己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当一位僧人以供手站立的姿态向他问候的时候,普愿鄙夷地说他“太俗气”,而那位不知所措的僧人又改为双手合掌向老师问讯时,普愿又说他“太僧气”。普愿也许的确很瞧不起这位除了俗气便是僧气的僧人,普愿一定在心里说,难道你就没有你自己的方式吗?
三
太和初年(827),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廉使陆亘因仰慕南泉普愿独行世人的人格精神,遂与护军彭城刘济一起恭请他下山说法,师事礼拜。
据说陆亘在宣城一带多有善政,而对禅法也十分热衷。然而他毕竟是一个被无数理念灌输得有些麻木的士大夫,他所热衷的,是文字上的教条,是理念上的执着。这也是中唐以后中国禅流于形式的普遍现象。一次,当陆亘请普愿来家中做客时,陆亘指着院子里的一块大石说:这块石头,弟子有时坐在上面,有时躺在上面,但我现在又想把它雕成佛像,老师说行吗?普愿说:“行啊。”陆亘表示怀疑,这曾被自己的身子亵渎过的石头真能雕刻成一尊纯洁的佛像吗?于是他说,恐怕不行吧?对于陆亘的执着,普愿只好说,不行不行。在普愿看来,石也好,佛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木佛可以烧火取暖,顽石当然也可以雕刻成佛像了,行与不行,又有什么差别呢?
陆亘对文字禅的执着还不止如此,一次他不知又从哪儿掉来一只大大的书袋,他问普愿:“古人瓶中养一鹅,鹅渐渐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师父您怎样让鹅出瓶?”日本的禅学者铃木大拙说,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不毁瓶又不损鹅,恐怕那鹅永远也取不出来吧!事实上,被养于瓶中而进出不能的非是一只虚拟的肥鹅,而是被禅的理念束缚得近乎呆痴的陆亘大夫。于是,普愿再次挥舞起他那柄利剑,突然大唤:“大夫!”陆亘应声而答。南泉高兴地说:“出来啦!”陆亘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南泉一声呼唤,把一时陷入思想空白的陆亘从陷阱中拯救出来。据说陆亘摆脱了相对条件的束缚,他开解了。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当年四祖道信向他的老师求得解缚之法时僧璨所说的话:束缚你的,原本是你自己,而非他人,因而解脱自己的仍是自己,正所谓解铃仍需系铃人。
普愿在他长达八十六年的人生中不仅创建了南泉禅院(道场),从而让中国的农禅制度得以扩大和升华,在其一生的弘法中,更是创作了一系列语录(公案),使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宋《高僧传》收录了他的传记,《景德传灯录》、《碧岩录》、《从容录》、《无门关》、《五灯会元》、《葛藤录》等各种禅宗典籍都分别收录了他的传记和语录。感谢这些不立文字的文字,因为它毕竟让我们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一千多年前一位杰出禅师的人格魅力。
大热天去日本京都金阁寺看50余年前重建的金阁,立即让人联想到那场金阁寺的大火。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中,金阁寺对主人公是一种异己的存在,执着地崇拜着金阁寺,它却使人遗忘了更广大的存在,这种“美的倒错”让人难以进入真正的人生。所以让那位烧毁金阁寺的和尚想起了《碧岩录》中南泉和尚斩猫的故事,并真的把金阁寺一把火烧了!南泉斩猫与台山婆子
南泉斩猫说的是池州南泉普愿禅师,因为东西两堂为了争一只猫,南泉禅师就对大家说:“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结果是没人回答,于是他真的.把猫斩了!而刚从外面回来的赵州和尚的回答却是:“脱履安头上而出。”赵州和尚是知道南泉的用意的,但南泉看似是为了让人开悟,不执着于是否用了犯了杀戒的方法,但仍然是以一种执着去破另一种执着,而且有本末倒置之嫌。
还有一则“台山婆子”的故事。五台山上有个婆子,凡有僧人向她问路,她都告诉他们:“骞直去!”等僧人一走,她又嘲讽他们:“好个阿师,又恁么去?”这当然不是回答别人问路,而是禅的机锋,赵州和尚勘破了她的意思,无非是说,台山就在你心中,骞直去,直归本心就是台山佛法。但所谓“枯龟丧命因图像,良驷追风累缠牵”,台山婆子的“骞直去!”和赵州和尚的勘破,也都是以自己对佛性的理解为标准,仍然是以一种执着去破另一种执着,所以明朝少林寺的契斌和尚说,在这个问题上,连赵州和尚也陷入了“荆棘陷阱”之中。
《庄子.知北游》中有东郭子问于庄子:所谓的道在哪里?庄子的回答是:“无所不在。”这与“佛法遍在”的理论是一致的,然后庄子又说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赵州和尚则说:狗子有佛性,湛然说:草木、瓦砾都有佛性。云门和尚说:佛是干屎撅。道与佛是如此的相通!《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佛则说:我所说法如爪上尘,所未说法如大地。所以任何用一种执着去破另一种执着的方法,都不是正确的办法,发现自己发生了“美的倒错”,就去摧毁倒错了的美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如何做到心无挂碍的无执,从而在玄之又玄的未知之法中,甚至在佛的“未说之法”中有所发现,才是较高的境界。
》》》
地藏经讲义 第十六卷
净空老法师讲述
请掀开《地藏经科注》卷中第四面,第二行的经文:
【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
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这里面的意思甚深甚广,详细说实在是说不尽。可是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造成地狱?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受这些苦报?这一点非常重要。《地藏十轮经》上说五逆罪为最极恶,五逆后面还会详细说明。这是杀父、杀母,父母恩德太大,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观察,父母照顾婴儿小心谨慎无微不至,从出生大概到三岁,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伤害性命。而父亲,现在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不及古人,古人做父亲的不但是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所以父母恩德之大,在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不知道恩德,不知道报恩,还要加以杀害,这罪极重,堕极无间、堕大阿鼻。
第二种罪业是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证果的圣人,人天师范,世间真正的福田,他所在的地方为一切众生种福。你杀阿罗汉,就是把众生种福的福田毁掉了,这一方人都没有福报,所以罪就重了。所以杀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不是对他结罪,是对这一个地方众生来结罪,这罪就重了。现在世间有没有阿罗汉?应真的罗汉我们相信一定有。佛菩萨化身在世间都很多,哪里说没有阿罗汉?但是我们凡夫不认识,你想找阿罗汉来杀也找不到。可是有等流的罪,等流是跟他相等的罪,相等的罪是谁?善知识。在这个地方上有德行、有学问,又能慈悲教化一方众生,杀害这种人等于杀阿罗汉,这罪就很重。不但不可以杀害,连毁谤的罪都不轻,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可是世间有一些无知之人,对于善知识有意无意产生一些毁谤,无意是无知,有意那是别有用心;别有用心里面嫉妒是占一大部分。现在还有一些人有些策略,如何在社会大众提高自己的身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什么方法?哪个地方很有名、得大众景仰的,把他批判、把他驳倒,他就上来了,这是别有用心,造作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阿鼻罪业。这是心里面怀极重的邪恶,他不怕因果报应,为了眼前的名利,眼前一点的利益,敢造这一种重大的罪业,这是无间地狱的业因。
第三种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有等流之罪,就是以恶心破坏佛的形像,无论是泥塑的、木雕的,或者是金属铸造的,或者是彩画的,画的这些佛菩萨形像,是以嗔恨的心把他破坏,这罪就是五逆罪。如果说无意的?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那很轻,是无意的,忏悔行,通忏悔;恶意的是不通忏悔。
末后一条破和合僧,就是破坏僧团。和合僧僧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见到,这里头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破坏别人的愿心,破坏别人的修学,等于破和合僧的罪,这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我们不能不知道。这里头也有有意跟无意,都必须要拣别,有意是恶意,无意是对于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了解。譬如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自己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任意毁谤,也是这一类的罪业。现在在世间许多处所我们听到,这一些造作罪业的人,造作罪业之事。我们必须要了解,佛菩萨说法是应机而说,所以佛法没有定法。《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无法可说;甚至于说到极处,如果有人说佛说法,就是谤佛。
说到这个地方,佛这一些开示我们要细心深入去体会,然后你就不会造谤法之罪,你就不会造了。因为他是应机施教,我的根性跟你的根性不尽相同,就是同修净土法门,同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相同。怎么说?我喜欢追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接一个,他喜欢慢慢的念,阿弥陀佛,这两个人就不一样,两个人都能往生。这个人说我这个念法正确,你那个决定错误,那不是打架吗?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同样是害病得感冒,医生给你处方,当然药大同小异,也有不一样,你吃这个药吃好了;看到你那个药方上有一两味不对,错了,你就批评他,他的体质跟你体质不相同。同样是一个处方,同样是一个医生,给我的分量、给你的分量不一样,给我用三钱,给你用四钱,那你两个还要打架?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体质不一样。佛讲经说法度众生就像这种情形一样,所以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你就谤佛、谤法、谤僧。为什么?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著这部经批评那部经,拿那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依照经论修行证果的人,这是僧。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造这个罪,这都是愚昧无知。我们要明了。
祖师大德们,我们看到他们注疏里面有批评,我们敢不敢学?不敢学,他批评是有对象,应机而说的。你们听过宗门的公案,南泉斩猫,你能学吗?你能看到猫杀掉它,看到狗也杀掉它,你可以干吗?丹霞可以把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你也可以干吗?他为什么那个作法,他有当机者,他这个举动能令那个人开悟作佛,所以他不犯罪。我们要把佛像劈开来烧火,我们是犯破佛身血的重罪,他不犯。他是何等人物,我们怎么敢干这种事情?所以这是一定要懂得。过去学佛有师承,等于说我们学佛有了保障,就好像婴儿、两三岁的小孩有父母照顾。现在学佛没人照顾,两、三岁的孩童造些什么事情,死活他都不知道,遇到危险、丢掉性命他自己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就像这种情形,你说多可怕!
佛了解末法众生的状况,知道末法众生的苦难,所以慈悲到了极处,对末法众生有特别的开导,《大集经》里面教给我们,末法众生净成就,这是一个重大的开示。我们生在末法时代,我们学佛选择哪个法门,佛讲的净成就,我们选择净土法门,这是尊佛的遗教。佛又有四依法垂训后人,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没有善友照顾,我们遵守四依法决不会走错路。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经是佛说的。
第二个教给我们,‘依义不依语’,这一句非常重要,为什么?避免后人对经典的争论。佛知道经典会流通全世界,一定要依靠翻译,同样是一部经,同样是一个梵文原本,翻译的人不一样,里面的字句意思当然就有出入。譬如我们现在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