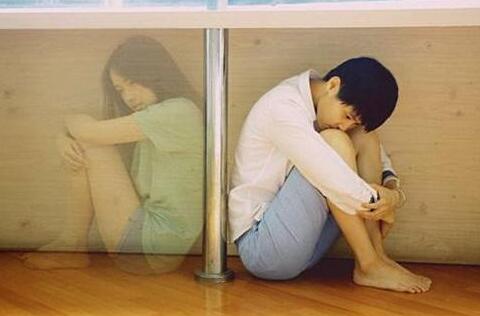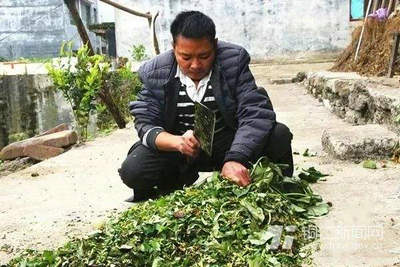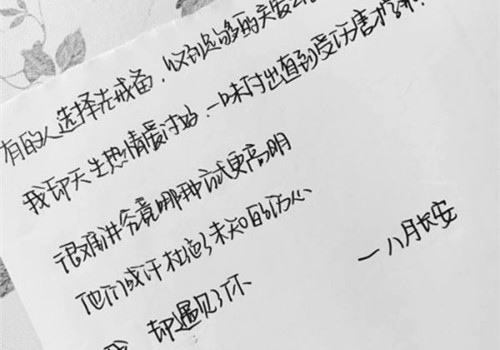
一、《琵琶行》中关于琵琶的演奏技巧
唐代诗人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的《琵琶行》是一首
《琵琶行》中用“轻拢慢
至于句中的“抹”与“挑”,则是指右手的两种指法。“抹”就是今天所说的弹,即用右手食指自右向左弹弦;“挑”和今天的说法一致,是用右手大指自左向右挑弦。弹和挑是琵琶演奏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指法,是基础。因为琵琶的右手演奏指法约有50多种,其中包括基本指法、派生指法与组合指法。正因为有了如此多的指法,所以才有琵琶丰富的表现形式。那么,为什么称弹挑是右手最基础的指法呢?因为右手的50多种指法中有90%的指法是由弹或挑派生的,或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所以,弹和挑质量的高低,对琵琶演奏的.右手技法如“滚指”、“轮指”、“
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对琵琶女的高超技艺和扎实的基本功,仅用一句“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描述就跃然纸上。“转轴拨弦”是正式演奏前的调弦试音,这准备工作只在“三两声”中便已完成,并且这“三两声”已经溶入并酝酿出了演奏者的感情。拧轴拨弦,弹奏几声,曲调未成就充溢着感情;一声声低沉缓慢,充满沉思,好像在倾诉身世的不幸。在整个演奏过程中,描写琵琶女弹奏技巧的文字也只有“轻拢慢
除了上述的演奏技巧描写,还有“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的句子,这是一种右手指法,相当于现在琵琶演奏中的“扫弦”。既右手食指用力急速地从缠弦到子弦一划而过,四条弦霹雳一声发出强烈的和声效果,在这里表达琵琶女对命运的不平之感与愤怒之情,是乐曲结束时常用的技法。不过,《琵琶行》中的“扫弦”是用工具,即诗中所说的“拨”,而不像今人用手指。前文中提到的“抹”与“挑”,也是用拨子,拨子可以是木质、牛角或象牙的。不过,也就是在唐代,已经开始有人用手指代替了拨子,乃至最终完全放弃了拨子。
二、琵琶的由来
琵琶,是由历史上的直项琵琶及曲项琵琶演变而来。历史上的所谓琵琶,并不指具有梨形共鸣箱的曲项琵琶,而是多种弹拨乐器,形状类似,大小有别,像现在的柳琴、月琴、阮等。其名“琵”、“琶”是根据演奏这些乐器的右手技法而来的。琵琶原是在马上演奏的胡乐,秦、汉之前的“琵琶”,又称为“批把”,最早见于史载的是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中有“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的记载,意即批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出称做批,向后挑进称做把,以此可见是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批把”。在古代,敲、击、弹、奏都称为鼓,当时的游牧人骑在马上好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大约在魏晋时期,正式称为“琵琶”。同时代的应勋在《风俗通》中也说:“以手批把,谓之琵琶”。由此可知,它是以演奏手法来命名的乐器,其形制,秦代为直柄,园形音箱,竖抱演奏,又称“直项琵琶”。据史料记载,直项琵琶在我国出现的较早。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进行文化交流,曲项琵琶由波斯经新疆、甘肃一带传入我国。曲项琵琶为四弦、四相(无柱)梨形,横抱用拨子弹奏。它盛行于北朝,并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传到南方长江流域一带。在隋唐九部乐、十部乐中,曲项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这在敦煌壁画和龙门石窟的浮雕中十分多见。唐宋以来,在这两种琵琶的基础中不断改进,逐渐形成现今半梨形音箱,以薄桐木为面,琴颈向后弯曲的形制,颈与面板上设“相”和“品”,张四弦,按四、五度关系定弦。近代通行的琵琶,为四相十三品,以后又经过逐步的改革,增至六相二十三(四)品,因而能演奏出所有半音,是许多乐器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当今的琵琶,是“融贯中西”的结果,当不为过。古代琵琶的视觉形象,在敦煌莫高窟的诸多壁画中,有极为生动的描绘;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古物库)中,还藏有多面唐代彩绘琵琶的实物。
三、中国民族乐器之王
琵琶是一种古老的民族乐器,被称为“民乐之王”,它的音域宽广,半音完备,技法丰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极强,被广泛应用于民族乐队和多种地方戏曲、曲艺伴奏。它不仅可以演奏传统乐曲,而且可以演奏西洋和现代作品,还可以与交响乐队合作,既能表现气势
再如琵琶文曲《夕阳萧鼓》, 乐曲通过委婉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细腻的技法,丝丝入扣的演奏,形象地描绘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尽情赞颂江南水乡的风姿异态。全曲就像一幅工笔精细、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第一段“江楼钟鼓”描绘出夕阳映江面、熏风拂涟漪的景色。第二三段,表现了“月上东山”和“风回曲水”的意境。接着如见江风习习,花草摇曳,水中倒影,层迭恍惚。进入第五段“水深云际”,那种“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壮阔景色油然而生。犹如白帆点点,遥闻渔歌,由远而近,逐歌四起的画面。第七段,琵琶用扫轮弹奏,恰似渔舟破水,掀起波涛拍岸的动态。全曲的高潮是第九段“乃归舟”,表现归舟破水,浪花飞溅,橹声“乃”,由远而近的意境。归舟远去,万籁皆寂,春江显得更加宁静,全曲在悠扬徐缓的旋律中结束,使人回味无穷。
《夕阳萧鼓》是一首著名的琵琶传统大套文曲,明清就早已流传了,乐谱最早见于鞠士林(1820年前)与吴
琵琶的许多名曲如《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昭君出塞》、《阳春古曲》、《高山流水》、《月儿高》、《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产生了无数的文化瑰宝,渊源流传,为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储蓄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素有单个民族乐器之王美称的琵琶,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中的精品。在其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实际上是一个吸纳、综合、取舍、
在唐代,琵琶是重要乐器,描写琵琶乐的诗歌也很多,而将琵琶描写得最出神入化的首推白居易。
一、关于琵琶
琵琶属于拨弦乐器,其形状因时而异,我们今天所见的琵琶,乃自唐宋以来,在圆形直颈琵和半梨形曲项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而来。隋唐年间,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等多种形制。琵琶,又称“批把”,武帝时,为了让远嫁之女能解思乡之情,便命人制作一种能在马背上弹奏的乐器,此乐器即为琵琶,东汉刘熙《释名》说:“批把,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可见琵琶的名称是基于演奏的手法而定。琵琶其音域十分宽敞,可以表现轻细和顺的抒情曲调,也可诠释雄浑激昂的热烈曲调。琵琶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形制、姿势、指法都有明显的变化。唐代时候,琵琶是件重要乐器,宫廷里、市井里,求风祈雨,争艳斗丽都有琵琶相伴。琵琶或加入合奏、或用于独奏,而且在演奏大曲时作为主奏乐器,位于领衔。唐代的琵琶名手如云,如曹妙达、段善本、曹钢等等。白居易有诗云“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听曹钢琵琶兼示重莲》)“四弦谱出是新声,珠颗泪沾金杆拨。”(《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这几句诗都是与曹钢有关联的。当时流行的琵琶有三种:一种是直项琵琶,又称秦琵琶、软咸、秦汉子;一种叫做曲项琵琶;另一种叫做五弦琵琶。《乐府杂录》上说直项琵琶传入较早,而曲项琵琶则是南北朝时期才传入。曲项琵琶外形曲项、半梨形音箱,长约三尺五寸、四弦四柱。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即是曲项琵琶。
二、“此时无声胜有声”
对于琵琶乐的文学描绘,在汉代已有零星的作品。不过当时的琵琶只是在“相和歌”中担任伴奏的角色,地位并不显著。《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琵琶是逐渐发展的乐器,到了唐代,已经取得了乐队中的霸主地位。唐代诗歌中琵琶乐诗约有一百三十首。如刘长卿“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顾况的“乐府只传横吹好,琵琶写出关山道。”王昌�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而将琵琶描写得最出神入化的首推白居易,白居易五六岁开始学作诗,八九岁便懂得声韵。其《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云:“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蕤宾掩抑娇多怨,散水玲珑峭更清。” 蕤宾、散水都是新调名,说明他对当时的音乐非常熟悉。白居易善于描写琵琶乐曲,如《听李士良琵琶》:“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第一句说琵琶的颤音如胡人卷舌音。又如《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珍珠细憾铃。”写出了琵琶的弦和弹奏的手指、听觉的美好联想。在众多的白居易的琵琶乐诗中,《琵琶行》被认为是“千古第一音乐诗”。孙绍振教授认为:《琵琶行》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1、以图画的变幻表现了乐曲的持续和突发的变幻之美。2、正面表现乐曲的无声、停顿、情绪的延续深化,使无声之美胜于有声。这是《琵琶行》达到的最高艺术境界(孙绍振《月迷津渡》。
琵琶可用于独奏和协奏,《琵琶行》是以精巧的诗歌语言来表现琵琶女子高超绝妙的琵琶独奏技艺。其诗:“……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诗中的“掩抑”是一种演奏的手法,以微弱的弹奏力度,表现一种沉重的风格,这是弹奏琵琶的独特技巧。“嘈嘈”是急雨骤下的宏大急促之声;“切切”指耳语般轻微细柔的声音。从琵琶女子手指间流出的月声,忽而如疾风骤雨,忽而似切切私语的'密谈。“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冰泉冷涩弦凝绝”形容音乐在行进过程中一种渐慢渐弱的表现,“凝绝不通”是声音渐渐停息的境界。从音乐来说是停顿,是音符的空白。诗人从旋律的空白中发现了音乐的美,外部声音的细微、停歇转化为内部自我体验和感悟――“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接着“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在无声中突然出现强烈的破裂性的响声,随即又停止,这是第二次的休止停顿,这种强烈的声音对比反差给人强烈的感染力,也因此“此时无声胜有声”成了千古佳句。有人说:“如果说,德国的贝多芬是世界上第一位懂得音乐强弱对比的美学价值的音乐家,那么白居易就是世界上第一位懂得音乐休止美学价值的音乐家兼诗人。”《琵琶行》还留下许多千古传诵的佳句,它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在诗歌史和音乐史上的地位正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所说:“《琵琶行》……后来作者,未易超越也。”
三、“人情重今多贱古”
五弦琵琶在唐代极为流行,据《唐书・乐志》记载:“其状稍小,北国所出。”公元五、六世纪盛行于北魏,唐代的“九部乐”和“十部乐”中几乎都离不开琵琶,且以五弦琵琶用得最多。五弦琵琶也称五弦琴,其形与四弦曲项相近,项直而音箱较小,筒体有精美的螺钿花纹。五弦琵琶的流行,与乐曲的优美、演奏水平的精湛密切相关。韦应物的《五弦行》:“美人为我弹五弦,尘埃忽静心悄然。古刀幽磐初相触,千珠贯断落寒玉。”白居易的《五弦》:“赵叟抱五弦,婉转当胸抚,大声粗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以生动的比喻写了著名五弦演奏家赵壁的高超技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五弦弹》对乐曲的哀怨愁绝之声有更生动的描绘:“五弦弹、五弦弹,听者倾耳心廖廖。……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风拂松,疏韵落。第三第四弦冷冷,夜鹤忆子笼中鸣。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远方士,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更从赵壁艺成来,二十五弦不如五。”这是一首讽喻诗,诗的前部分,诗人以一连串生动的比喻,铿锵的语言,描绘了赵壁弹奏五弦的绝技。但接着笔锋一转,指出五弦弹并非“正始之音”,因为“正始之音”是疏越清淡,听之使人心气平和,不像赵壁五弦弹那样凄切悲惨。诗以慨叹结束,从而完成了“恶郑之夺雅”的讽喻性主题。白居易受儒家传统音乐思想影响,在理论上推崇古乐,这在他的许多诗里都有体现,如“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等,他认为古乐才是“正音”。
四、结语
白居易认为“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琵琶行》和《五弦弹》的艺术魅力也许不仅仅在于对琵琶声的生动描写,恐怕还在于“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吧!
导语:白居易对音乐的描摹和对琵琶女演奏技艺的描绘是《琵琶行》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诗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琵琶女身世的同情和对自身遭遇的愤慨,将精湛绝伦的音乐与绵延无尽的深情完美演绎,呈现出精美丰富的艺术色彩。
诗歌和音乐,自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如此,古代诗人不但使诗歌具有音乐般的韵律美,而且喜欢以音乐为题材,或者在诗词歌赋中,间以音乐美的描写。但是要想对无形的音乐加以形容难度很大。宋代著名词人张孝祥有这么一句词:“悠然兴会,妙处难与君说。”意思是很多好的作品在欣赏完之后,有很多的好处很难说出来,尤其是对音乐的描写和刻画,因为太抽象太空洞。但是,历史上不是没有这种贤人能士。翻开我国古代诗史,多少描写器乐演奏的名篇佳句,集然入目,伶然盈耳:马融《长笛赋》中“状似流水,又象飞鸿”般的悠扬的笛声;韩愈《听师颖弹琴》中“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般的雄健的琴声;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优美的琵琶声;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中“石破天惊逗秋雨”般的箜篌声;苏轼《赤壁赋》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幽怨的洞箫声;刘鹗《老残游记》中的白妞说书一段等等都非常精彩。但若就对乐曲描写的细腻完整、形象生动、精美绝伦,而且还能从乐曲中挖掘出女主人公的形象,并透射出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令人一唱三叹的,就得算唐代白居易的《琵琶行》。他在描写音乐方面的成功使历史上其他的文章都难以望其项背,恰如清代张维屏《琵琶行》所说:“枫叶荻花何处寻?江州城外柳阴阴。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说到今。”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赞美白居易《琵琶行》描写音乐的完美时说:“这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比起同时代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等名作来,以其描写细腻真切、自然流畅和情感的潜流暗转、突放突收而独具特色。”
《琵琶行》作于作者白居易被贬江州的第二年(816),作品通过描写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巧和她凄凉的身世,抒发了作者自己政治上受打击、遭小人排挤的抑郁悲凉之情。在文章里,诗人把一个琵琶女视为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亦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那么文章是通过什么样的音乐描写把读者带入这样的一种境界呢?
一、对音乐的侧面描写
(一)题诗
《琵琶行》中有很多地方并没有直接描写音乐,但是同样起着勾画渲染音乐的作用,有的时候甚至比直接描写音乐更能表达音乐的内涵。例如:我们先暂且把《琵琶行》看作是一首琵琶曲,那么前面的第一句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无疑就是乐曲的前言,或者叫做题诗。在这样的夜色中,在这样萧瑟的秋风中送别客人,别有一番离愁涌上心头。这就为下面即将出现的乐曲烙上了一层悲情的基调。这也使我们想起了西方的音乐,例如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四季》作于1876年,共有十二首小曲,而且这十二首小曲与十二首诗篇相呼应。例如 :第四首《四月――松雪草》(“April――Snow Drop”)前面的题诗:
淡青、鲜嫩的松雪草啊!
初春的残雪偎在你身旁……
往昔的忧愁苦恼,
只剩下最后几滴泪珠儿还在流淌,
来日的幸福,将给你带来新颖的幻想……
而后面出现的音乐则是节奏自在、情绪柔和,表现初春的憧憬和梦,这和题诗的情绪是相互吻合的,这说明我们伟大的诗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在乐曲的前面加题诗来说明乐曲的基本内容,不能不叫人拍案称绝。
(二)对音乐效果的描写
对音乐效果的描写是《琵琶行》中的另一个亮点。诗中有多处是对音乐效果的描写,如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刚校弦正音,演奏者已经进入了抒情的艺术境界。感情先行,“未成曲调先有情”,这是音乐创作或演奏成功的关键。诚然,一切艺术创造都必须“先有情”,艺术思维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感情相伴随,但是,音乐的形象和思维更需要感情领先。这一点,也是白居易自己演奏的切身经验。他在《琴》中写道:“置琴曲几上,慵坐但含情。”在《夜调琴忆崔少卿》中写道:“今夜调琴忽有情,欲弹惆怅忆崔卿。”充分的感情酝酿,丰富的联想孕育,情在声先,曲居情后,演奏就一定十分动人。这些诗句可以作为“未成曲调先有情”的注脚。“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在感情引路之后,演奏开始,琵琶女也是寓情于声,以声传情。她通过拢、捻、抹、挑、掩、抑的手法,把满腔的情思化作一声声的“琵琶语”,用富有表现力的音乐语言,来诉说平生的心事。关于化情为声,白居易曾这样描写过一位弹筝的女艺人,他在《筝》中写道:“移愁来手底,送恨入弦中。”这是绝妙的音乐美学警句。琵琶女也正是这样,把自己的愁恨情思传到手底,送入弦中。这样的演奏,就不是纯技巧的卖弄,这样的音乐,就不是空洞无物的一堆音响,而是有了灵魂,有了生命,表达了琵琶女掩抑在内心深处的思绪,反映了她的坎坷生活,这“不得意”的生活又是她弹奏低沉曲调的沃土。又如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人写出了拨动不同的弦所发出的不同乐音效果,写得形象生动,对比鲜明,富于概括性。而“错杂”二字,正道出了音乐形式美的'真谛:寓于统一的杂多。正因为 “错杂”,琵琶音乐才曲折多变,才能产生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和谐之乐。“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这是从另一角度写音乐的意境。段玉裁《与阮芸台书》认为,“水下滩”应作 “冰下难”,泉流冰下,莺语花底,“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这是很有见地的。“幽咽泉流冰下难”的涩境,在白居易、元稹的诗中曾一再出现。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以无声衬有声,把听众带入曲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白居易描写音乐,多次涉及无声之美。如《夜筝》:“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又如《筝》:“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珠联千拍碎,刀截一声终。……歇时情不断,休去思无穷。”这无声之声的好处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弦凝指咽声停处”、“凝绝不通声暂歇”,既指出无声之美存在于有声之乐中,无声之美依赖声音的存在、运动与间隙而显见,又指出无声之美的短暂性,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但也需借助于无声的手段,其有声是长久的,无声则是短暂的。第二,“歇时情不断,休去思无穷”,指出音乐是艺术,不为有声而有声,也不为无声而无声,有声与无声、进行与休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它们都是表情的手段,都为表情而存在。第三, “别有深情一万重”,“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既指出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之所以需要无声,是因为无声具有特殊功能,能表现有声所难以表现的 “幽愁”、“暗恨”、“深情”,因而能胜有声;又指出只能“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能时时无声胜有声。无声能否胜有声,取决于它能否表现“幽愁”、“暗恨”,因而无声的运用必须恰到好处。白居易对无声之美的描述与阐发,道前人所未道。《琵琶曲》弹奏至此,满以为已经结束了。谁知那“幽愁暗恨”在“声渐歇”的过程中积聚了无穷的力量,无法压抑,终于“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这段音乐情绪高涨起来,绝非柳暗花明,重见天日,而是以刚劲急促、震撼人心的节奏,表达琵琶女对命运的不平之感与愤懑之情。这时她的幽愁怨恨一下子如破瓶而出的水浆滚滚而出,宣泄了她的幽愁暗恨。琵琶女受伤的心灵本渴望爱情的抚慰,但薄情的丈夫“重利轻离别”,让她时常空船独守,这现实更使她痛不欲生,悔恨交加,故而音乐之声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高亢激越的旋律正是她对世人重色轻才和丈夫重利寡情的愤怒控诉。“四弦一声如裂帛”,如裂帛,这是琵琶女的心的碎裂,也是诗人被贬九江之后,伟大抱负被撕裂的愤激的哀号。
总之,诗人不但写出了琵琶女音乐技艺的高超,而且通过乐曲的变化,表达出演奏者内心情感的起伏,让人如闻其声,如感其情。正如诗人所云:“我闻琵琶已叹息。”悲愤的曲调,令普天下伤心人闻声一哭!这一段,白居易和琵琶女,一个笔下写忧怨,一个弦上弹忧怨,他们都有一样的愁怨,诗人用湿漉漉的诗行写出了用湿漉漉的眼泪浸泡的湿漉漉的心。一曲虽终,而回肠荡气、惊心动魄的音乐魅力,却并没有消失。诗人又用“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环境描写给我们营造了一种视觉和听觉的美感:琵琶女的演奏停息了,东船西舫悄然无声,这是美妙绝伦的琵琶声引人入胜,引发了每一个人内心的郁闷和苦痛的结果;在茫茫的江水上,江面微波荡漾,落花慢慢漂流,只看到倒映在水中的明月,它盛满忧愁,弥漫着凉意,将人们引入一个凄清和悲凉的意境。它渲染了当时凄清的气氛,又衬托出琵琶女弹奏的高超技艺,给人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诗人不但写音乐演奏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把环境和人的情感,而且是把不同的人的情感压缩到这四句诗里去了。而且由于特殊的季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再加上弹奏者高超的技艺,弹奏者以及江州司马共同的处境,所以青衫湿遍则是必然的结果了,可见琵琶乐曲的感人。
二、对音乐的正面描写
白居易对音乐的描摹和对琵琶女演奏技艺的描绘是《琵琶行》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诗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琵琶女身世的同情和对自身遭遇的愤慨,将精湛绝伦的音乐与绵延无尽的深情完美演绎,呈现出精美丰富的艺术色彩。
白居易是喜欢音乐的,有诗为证:“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对音乐的喜爱,所以深厚的文学功底加上对音乐的痴迷成就了这千古绝唱的《琵琶行》。且看白居易是怎样地信手拈来。
(一)琵琶曲总论
诗中开始写音乐是从“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开始,继而是“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这一段诗先从调音开始写起,因为弦乐器是容易跑音的,所以一般都要在演奏之前先调试一下音,这是弹琵琶之前的必须动作。虽然作者白居易是简单地一带而过地描写,但是从简单的调音中,已经是“未成曲调先有情”,由此可以看出琵琶女的才情不浅,技艺高超。然后又交代了所演奏的曲目,这是对乐曲总的一个描写。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白居易的《琵琶行》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初为《霓裳》后《六幺》。”其中《霓裳》即《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大曲中的法曲精品,是唐代歌舞的集大成之作,而《六幺》同样是当时的一首著名的歌舞大曲,只有技艺高超的人才能驾驭得了,这也为后面的“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做了铺垫,更为能够弹出让“满座重闻皆掩泣”的音乐做了很好的预告。
(二)在比喻和对比中描写音乐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和其他描写音乐的作品一样,诗人在描写音乐时也运用了大量贴切的比喻,这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描写音乐的最经典的段落之一。用文字来再现音乐往往是很苍白的,因为它那飘忽不定的音响很难被准确地捕捉和表现。那么,白居易又是怎样写好琵琶女声情并茂的弹奏及其创造的美妙境界呢?
首先,他用人们熟悉的声音作比喻,以唤起读者的共鸣。如“急雨”、“莺语”、“刀枪”等声响,在妙喻联翩中赋予抽象的音乐以具体的形象,使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如大弦的嘈杂,小弦的窃窃私语,大珠小珠的清脆滚落,鸟声的婉转,冰下流水的呜咽……许许多多的声音,让人应接不暇;声音有很多种,仔细听来,这一声和那一声有明显的音色、音量上的区别,复杂中又有不可混同的地方。通过这种对比表现音乐的抑扬顿挫,例如大弦小弦,大珠小珠,而且在弹奏的过程中,莺语泉流。这些既包括音色的对比,又包括音量的对比。另外,还通过“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表现一种音乐音量的减弱。而“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则是音乐的完全停止。然而,音乐并没有结束,短暂的停止之后,积蓄了更大的力量,并在一瞬间爆发成“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完成了从舒缓流畅――逐渐呜咽――间歇停顿――激越雄壮的过渡,写得多么精彩绝伦啊。刘熙载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用日常生活中所见、所感之物进行音乐的描摹比喻,生动而不晦涩,浅显而不平俗,描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无言之美。
(三)弹奏方法的描写
白居易对诗中弹奏者的弹奏动作、弹奏状态也进行了形象的描写,通过这一描写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弹奏者的技巧、情感。这种方法,在其他写音乐的作品中就很少见到了。因为很多人在乐器的弹奏方面都是外行,对乐器的弹奏很难去把握。但是白居易却是一位行家,他诗中交代了多种弹奏方法例如:拢、捻、抹、挑,这些都是琵琶弹奏者常用的技巧方法。“转轴拨弦”是琵琶弹奏前一般的惯用动作,而“低眉信手续续弹”则是弹奏开始时的表情和神态。“拢、捻、抹、挑”和“收拨、划”是在弹奏中和弹奏结束时的常用动作和手法。“沉吟放拨插弦中”又是弹奏结束后的神情和动作。从拢、捻、抹、挑这些手法可以看出琵琶弹奏技巧的复杂性。“转轴拨弦”和“放拨插弦中”,虽然是弹奏者共有的动作,但绝不是一个琵琶弹奏门外汉的动作,这里写出一个“大家”来。更需注意的是“低眉信手续续弹”这一句,这里的弹奏神态是“低眉信手”,突出了演奏者的慵懒和自信,这不是一个消极的写法,而是通过这些不经意的随便的动作表现出一个大家从容不迫的风范。当然,这种懒惰的情绪不会一直如此,随着曲调的进展,弹者的精神也逐步振奋起来,到“曲终收拨当心画”,她已经聚精会神地以熟练的手法完全控制了听者的注意力。整个弹奏过程中,或低回掩饰,如泣如诉;或流美圆润,如莺歌玉转;或高昂明快,如铁骑交锋,无不生动地传达出弹奏者内心深处浪涛般起伏不平的感情。诗人用丰富的笔触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令人动容的、哀愁感伤的艺术境界。金人王若虚指出:“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如此赞语,洵不为过也。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对琵琶女演奏技艺的精湛刻画和形象生动的音声描摹令人叹服,对复杂的琵琶声音描绘得气韵生动,含情带意,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