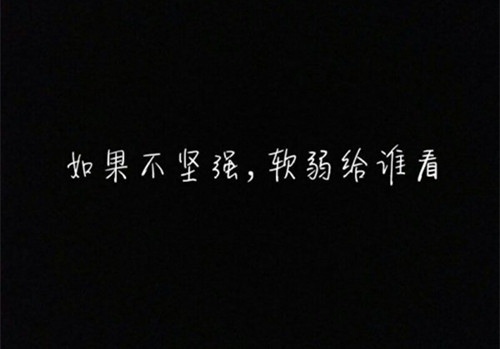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一)
白水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有趣的人。他能在谈天的时候,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这回听勉子说,日本某杂志上有《女?》一文,是几个文人以"女"为题的桌话的记录。他说,"这倒有趣,我们何不也来一下?"我们说,"你先来!"他搔了搔头发道:"好!就是我先来;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我们知道他照例是开口不能自休的。果然,一番话费了这多时候,以致别人只有补充的工夫,没有自叙的余裕。那时我被指定为临时书记,曾将桌上所说,拉杂写下。现在整理出来,便是以下一文。因为十之八是白水的意见,便用了第一人称,作为他自述的模样;我想,白水大概不至于不承认吧?
-------------------朱自清《女人》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来看我了。他说和P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东人;这回来上海,是要上美国去的。我问起哥仑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杂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杂志。但他说里面往往一年没有一篇好文章,没有什么意思。他说近来各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了一个会,有几个人的话有味。他又用铅笔随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后面,写了《哲学的科学》一个书名与其出版处,说是新书,可以看看。他说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馆里。见他床上摊着一本《人生与地理》,随便拿过来翻着。他说这本小书很著名,很好的。我们在晕黄的电灯光下,默然相对了一会,又问答了几句简单的话;我就走了。直到现在,还不曾见过他。
他到美国去后,初时还写了些文字,后来就没有了。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远处的云烟了。我倒还记着他。两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学日报》上见到他一篇诗,是写一种清趣的。我只念过他这一篇诗。他的小说我却念过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篇《雨夜》,是写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的。W是学科学的人,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却又很热很热的。
这就是W了。
-------------朱自清《飘零》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三)
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只是随意挼弄着,随意丢弃了。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
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
---------------朱自清《看花》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四)
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
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正可借来作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诗。这是两年前初到北京,在一个村店里,喝了两杯"莲花白"以后,信笔涂出来的。于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于诗中所说的,那更是遥遥乎远哉了,但是事情是这样凑巧:今天吃了午饭,偶然抽一本旧杂志来消遣,却翻着了三年前给S的一封信。信里说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宁波之南的台。这真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于想不出,这却指引我一条路,虽然只是"一条"路而已。
---------------朱自清《一封信》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五)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载自《匆匆》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六)
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只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利涉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载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七)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载自《背影》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 八)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载自《荷塘月色》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九)
莫愁湖在华严庵里。湖不大,又不能泛舟,夏天却有荷花荷叶,临湖一带屋子,凭栏眺望,也颇有远情。莫愁小像,在胜棋楼下,不知谁画的,大约不很古吧;但脸子开得秀逸之至,衣褶也柔活之至,大有"挥袖凌虚翔"的意思;若让我题,我将毫不踌躇地写上"仙乎仙乎"四字。另有石刻的画像,也在这里,想来许是那一幅画所从出;但生气反而差得多。这里虽也临湖,因为屋子深,显得阴暗些;可是古色古香,阴暗得好。诗文联语当然多,只记得王湘绮的半联云:"莫轻他北地胭脂,看艇子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气概很不错。所谓胜棋楼,相传是明太祖与徐达下棋,徐达胜了,太祖便赐给他这一所屋子。太祖那样人,居然也会做出这种雅事来了。左手临湖的小阁却敞亮得多,也敞亮得好。有曾国藩画像,忘记是谁横题着"江天小阁坐人豪"一句。我喜欢这个题句,"江天"与"坐人豪",景象阔大,使得这屋子更加开朗起来。
--载自《南京》
朱自清散文集摘抄(十)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有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蒙蒙的雨,园里没了秾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朱自清《歌声》
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
这座“萱瑞堂”被认为是曹雪芹所撰《红楼梦》中“荣禧堂”的原型。康熙皇帝六次南巡,除第一次驻跸在江宁将军署,其余五次均驻跸于江宁织造署,其中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及以后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都由曹寅承办接驾大典。此外,曹寅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亲王为妃。
曹玺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寅是他的祖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曹寅病逝,在江宁织造任职二十二年,驻江宁二十年。曹寅的儿子们——也就是曹雪芹的伯父曹颙、曹子承父业,继任江宁织造近六十年。在历史上,南京的丝织业一直负有盛名,三国东吴、东晋、南朝时期,都曾在建康(今南京市)设立锦署(织造署)。在清朝,江宁的丝织业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江宁织造署的丝绸产品——金陵云锦只供皇帝和亲王大臣使用,高度垄断了当时的服装奢侈品市场。江宁织造署规模弘大,共有三个工场:一在西华门,一在常府街桥边,一在北安门的靼鞑城(即明皇城)。江宁织造署拥有织机三万多台,男女织工逾五万,关联产业解决当地民众就业二十多万人,历年的产值都超过一千万两白银。江宁织造署里的金陵云锦生产规模和工艺创新也在康熙年间达到顶峰。金陵云锦因其灿若云霞、美若绮云而得名,是我国丝织工艺中具有优秀艺术传统、鲜明地方特色和独特艺术风格的织锦。金陵丝织生产的开端,最早追溯到南朝,而“云锦”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在元、明、清三代。金陵云锦集历代织绵之大成,在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品。
江宁织造署不仅是清代举足轻重的轻工业部门,还是江南重要的政治部门,可直接向清政府报告江南地区的各种情报,因此只有清帝的亲信及内务府大臣才可担任,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所以权势显赫。不仅如此,曹寅与妻兄李煦轮流兼任设在扬州的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曹家还曾兼理江南的制铜部门,在上述领域握有垄断的特权。六十年间,曹家势力逐渐扩张,成为江南举足轻重的豪族。雍正二年(1724年),曹雪芹诞生在江宁织造署内,自幼生活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环境中,他的童年记忆充满了这个家族鼎盛时期奢华生活一个又一个缤纷多彩的场景,这一切根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化作成年以后凄美绝伦的梦幻,同时也表现在《红楼梦》中花团锦簇的贵族生活场景。但是,江宁织造署并不确定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据一些红学家的考证,大观园可能来自曹氏家族位于南京小仓山的随园,或来自位于北京柳荫街的恭王府。由于北京恭亲王府至今遗迹尚存,所以倾向于此的红学家有更多的证据。然而,江宁织造署是曹雪芹生活多年的地方,它对曹雪芹必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乾隆皇帝南巡时,显赫的曹氏家族已经衰落。乾隆十六年(1751年),两江总督尹继善为迎接乾隆皇帝南巡,在江宁织造署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将其改造为乾隆行宫,现在南京“大行宫”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整个行宫内假山围绕,清溪穿流,花木葱茏,流水潺潺,楼榭亭阁布处其间,有绿静榭、听瀑轩、判春室、钟中亭、塔影楼、彩虹桥、钓yu台等胜景。大行宫后不幸毁于火灾。太平军占据南京时,在原基址上建天王府。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天王府又被焚毁。清朝末年,大行宫一带辟为马路。现在的南京市大行宫街区就是清代江宁织造署的所在地,但行宫本身却已无迹可寻。
乾隆皇帝驻跸过江宁织造署所改建的行宫,但他的身世之谜与曹家并无干系,而汹涌的俗文化与四平八稳的正史却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关于乾隆生母的各种传说中,最为荒谬的说法来自某些红学爱好者们,他们“考证”出,曹雪芹有个深深相爱的女朋友,该女友不慎怀了曹雪芹的孩子,但很快被选入雍亲王府,得到雍正的宠爱,生下乾隆。鉴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向被视为曹雪芹满怀深情所刻画的女友,那么这种说法即认为乾隆的母亲是林黛玉。诚然,这种说法是极具颠覆性的,它不仅颠覆了清史和文学史,而且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那么,乾隆的身世为何在江南引起如此大的波澜?他究竟出生在何地?《清史稿》中的孝圣宪皇后(雍正即位后封为熹贵妃,乾隆即位后加尊号为崇庆皇太后,去世后谥为孝圣宪皇后)究竟是不是乾隆皇帝的生母?有关乾隆生母的传说中有三种与热河避暑山庄有关,而且始终围绕着丫鬟或宫女展开:
①清末历史学者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中的《列女传》部分讲道:乾隆的母亲是热河民间女子,家道平常,没有仆人。她十三四岁时到北京入选了秀女,到雍王府做丫鬟。雍正有一段时间生了重病,她对雍正悉心照料,于是日久生情,女子怀孕,后来产下男孩,取名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②热河都统幕僚冒鹤亭、作家周黎庵、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台湾小说家高阳等人认为:乾隆的母亲是热河行宫的一个宫女李佳氏,名叫李金桂。雍正还是皇子时,随父皇至避暑山庄,与山庄内一位丑陋的李姓宫女相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姓宫女已怀上了“龙种”。康熙大为震怒,问道:“种玉者何人?”经追问,雍正承认是自己干的好事。此时这位宫女就要临产,康熙怕家丑外扬,让人将她带入草棚马厩,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
③民国国务院总理熊希龄与老宫役闲谈中得知:乾隆的母亲是江南女子“傻大姐”,她来到热河后做了雍正的丫鬟。雍正还是皇子时,随父皇至避暑山庄,与“傻大姐”相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姓宫女已怀上了“龙种”。康熙大为震怒,问道:“种玉者何人?”经追问,雍正承认是自己干的好事。此时“傻大姐”就要临产,康熙怕家丑外扬,让人将她带入草棚马厩,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最后这个传说流传很广,是因为熊希龄把这个传闻告诉了胡适,胡适又把这件趣闻记在日记里,通过《胡适之日记》公开,这个传说又经过口口相传,被添加了许多想象的内容,与李佳氏的传说混淆在一起,从而变得街知巷闻了。
王闿运、冒鹤亭、熊希龄、胡适等人都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人物,因而他们所说的话较寻常传言更为人所深信。那么,乾隆是否出生在避暑山庄呢?乾隆在位时期,民间就已经对他的出生地众说纷纭,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他出生在热河行宫的一座皇家园林,这座园林因为背靠一座形如狮子的山峰而得名“狮子园”。诸皇子每年随康熙到热河避暑,雍亲王也不例外,狮子园便是雍亲王(后来的雍正皇帝)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朝有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进士,后在军机处当值,做到了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的掌故。管世铭经常随乾隆去承德避暑山庄、参加木兰秋狝典礼,他曾写下《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该诗后面附有管世铭的原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个注脚的意思是:乾隆皇帝出生在狮子园,所以他常在先帝雍正的忌日到这里住上几日,以示纪念。
如果认为管世铭的诗作只是阐明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的旁证,那么嘉庆的两首诗就可作为直接证据了。乾隆退位后的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嘉庆跟随乾隆帝到避暑山庄庆贺他的八十六岁寿辰,并写下一首《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中有这样两句:“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诗后附有嘉庆帝的原注:“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一年之后,又逢乾隆寿辰,嘉庆再写《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祝寿:“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但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帝为父亲纂修《实录》和《圣训》时,发现两部典籍中,皇父乾隆的出生地皆为雍和宫。嘉庆命文华殿大学士刘凤诰仔细调查,刘凤诰考证了乾隆的《御制诗集》,这些诗作和注脚中,乾隆凡是讲到自己出生地点的几处,都清楚地表明是雍和宫。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春,乾隆作《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有一句“到斯每忆我生初”。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春,乾隆作《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中有一句:“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斋阁东厢”指的是雍和宫东书院如意室、平安居、太和斋一带。由此诗可见,乾隆本人不仅承认自己诞生于雍和宫,而且还暗示了自己出生在雍和宫的具体位置。有鉴于此,嘉庆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的说法。这样,《实录》和《圣训》中记载乾隆出生的文字就成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综合所有的正史、野史与传闻,乾隆的身世有如下几种说法:
①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熹妃钮钴禄氏,父亲是雍正皇帝。
②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热河民间女子,父亲是雍正皇帝。
③乾隆生于避暑山庄。母亲是热河行宫宫女李佳氏,父亲是雍正皇帝。
④乾隆生于避暑山庄。母亲是江南女子“傻大姐”,父亲是雍正皇帝。
⑤乾隆生于海宁陈家。母亲是陈夫人,父亲是陈世倌。
⑥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林黛玉,父亲是曹雪芹。
为了生下乾隆,雍正皇帝、陈世倌、曹雪芹和满汉女子各色人等着实忙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第一条是正史,第六条是笑话。第二、三、四条无法证实也无需证伪,只能永远作为民间流言存在。第五条流传最广,但也已经被史学家以确凿的证据推翻,不再值得研究了。那么,除了相信正史,就已别无选择。
乾隆的身世之迷的传播历时已久,它是清朝最有趣、传闻最多的历史疑案。朝野上下,京城内外,官方文献,御制诗文均被搬出来考证,而在清末民初排满情绪的推波助澜下,野史笔记、民间故事、戏曲小说,都在尽情地演绎这段故事。在一切传闻和野史都被证伪之后,穿过层层的历史迷雾,绕过热河女子、李佳氏、傻大姐、陈夫人等各形各色的女人,唯一的真相只能锁定在——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熹妃钮钴禄氏。于是,乾隆真正的母亲终于和世人见面了:熹妃,钮钴禄氏,崇庆皇太后,满洲贵族血统。
自此,好像这所有纷繁的传闻都被考证推翻,真相被正史揭开了。其实不然,翻开有关于这位熹妃的档案,乾隆真正的身世之谜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萧奭的《永宪录》卷二记载: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丁卯。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年)记载: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记载:
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前两条档案是完全吻合的:“封……钱氏为熹妃”、“钱氏封为熹妃”。而第三条档案则显示:“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三条历史档案中存在着矛盾,但可是肯定的是:“熹妃钱氏”和“熹妃钮祜禄氏”在同一天奉皇太后的懿旨受封,她们必然是同一个人。按照清宫的规制,册封皇妃不能有重名,不仅同一天不会有,整个清王朝都不可能有两个熹妃。萧奭的《永宪录》与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互为证据,不可能同时出错,更不可能错误相同。这两条档案是最有力的证据,它所提供的信息比任何传闻都更具颠覆性,因为它昭示出的是如下事实:乾隆的母亲姓钱,钱姓起源于中国南方,清朝满族人不可能姓钱,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乾隆是满汉混血儿。但是,钱氏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为什么成为了钮祜禄氏呢?钱氏家族的后人钱治冰经过考证认为: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册封熹妃钱氏的时候,这个时候雍正还没有秘密立储,也就是说,弘历(乾隆)这时候作为普通皇子其母亲钱氏和其他普通皇子的母亲一样都是可以保留汉姓的。而到了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正式设立秘密立储制,才指定弘历为皇太子。也就是说,熹妃钱氏变成熹妃钮祜禄氏就是在雍正秘密立储之时或之后的事了。在这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皇太子的母亲需要有一个高贵的满族出身,因此必须要将熹妃姓氏篡改为满族贵姓。而钮祜禄氏是满族最高贵的姓氏之一,其先祖巴图鲁额亦都曾帮助努尔哈赤以十三兵甲起家,是奠定清代开国基业的第一功臣。于是熹妃钱氏便拜巴图鲁额亦都之后四品典仪凌柱为义父,从而便改汉姓钱氏为满姓钮祜禄氏了。(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于是,在乾隆朝修订的《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钱氏就成为了钮祜禄氏,清代皇室的《玉牒》(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也更详细地表明:世宗宪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纯皇帝(乾隆),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
如果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原本姓钱。那么,钱氏是谁?根据钱治冰的最新考证:“乾隆之母钱氏(1692-1777年)是浙江嘉兴钱纶光与其妻书画家陈书(1660-1736年)之幼女,是刑部尚书钱陈群(1686-1774年)的妹妹”。钱陈群“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得乾隆帝的尊宠,倚为股肱儒臣,二人之间除君臣之谊,又是文字知己,乾隆称之为‘故人’。钱陈群每有诗作进呈,乾隆必亲笔题诗回赠。他退休后,仍屡次升迁,加尚书衔、太子太保。乾隆帝赐之以‘食全俸’,常寄自己的诗作,请钱陈群和作。他数次去北京,为皇太后和乾隆帝祝寿,并同乾隆帝到塞外围场行猎,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十六年(1751年)钱陈群首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并随驾钱王祠陪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钱陈群二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再次随驾钱王祠,乾隆赐御诗褒扬钱氏先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高宗第三次南巡时,钱陈群已告归在籍,即赴常州恭迎圣驾,并扈从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地,再次随驾钱王祠,并携台州族孙钱选,以传世唐赐铁卷晋呈御览,乾隆赐御制铁卷歌一首。”此外,“钱陈群的学生阿桂、刘墉、纪昀等备受乾隆重用……钱陈群的子孙世代包括女婿、族人均为朝廷重臣,可见钱陈群与乾隆母子的关系非同寻常,恐怕一般亲戚关系是无法做到这一步的。”(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
同时,前文提到的乾隆极其关心钱塘江海塘工程,这可能与他的真正身世有关。“公元前910年8月,吴越王钱镠为了保护海岸,使其免受海潮侵蚀,命人采山阳的竹子,又令矢人造箭三千只,募强弩五百人以射涛头,使‘潮回钱塘,东趋西陵’。……乾隆继位后,开始重修钱氏海塘。乾隆二十五年,浙江潮信告警。乾隆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四次亲临海边,检查海塘工程。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乾隆到杭州的第二天,即亲临海边,亲试打桩,他见石桩必须内移数十丈方能固定,必然会损毁百姓的田庐,是‘欲卫民而先殃民’,决定先建柴塘,待接涨沙坚,再改筑石塘。到乾隆晚期,凭借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浙江境内已建成自金山到杭县长达二百四十八里的鱼鳞石塘,钱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自宝山至金山长达二百四十二里的块石篓塘。石塘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仍然起着挡潮防患的作用。乾隆继钱镠之后大力修筑浙江海塘,有力地保护了富庶的吴越地区,此举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而钱陈群,这个可能是乾隆舅舅的人,正是在远古时代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吴越王钱镠的直系子孙。
在《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被写成是乾隆的一母同胞,陈家洛在并不知情的时候,与乾隆在钱塘江边畅谈。书中第八回这样描述,“陈家洛道:‘当年钱王以三千铁弩强射海潮,海潮何曾有丝毫降低?可见自然之势,是强逆不来的。’……乾隆说道:‘潮水如此冲刷,海塘若不牢加修筑,百姓田庐坟墓不免都被潮水卷去。我必拨发官帑,命有司大筑海塘,以护生灵。’陈家洛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道:‘这是爱民大业,江南百姓感激不尽。”
自古以来,兴修水利始终是帝王的职责。但乾隆六下江南、四赴海宁,住在偏远小镇中的陈家府邸,事无巨细皆亲历亲为,事隔两千多年,乾隆与钱镠为何热衷于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情?当然,钱治冰的推论仍需更多史料甚至考古成果的辅助研究,但他几乎已经指出了一条研究的路径。这个“钱氏”同时出现在萧奭的《永宪录》与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必定隐藏着历史的重大秘密,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揭示历史的重大发现。历史上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疑案,俗文化的演绎让这些疑案浸满了流言蜚语和野史趣闻,各种故事满足各种人的兴趣。而考证只能还原历史的真相,考证是无意识的,它可能让一段传奇变得索然无味,也可能让事实振聋发聩。乾隆的身世之谜最终从热河避暑山庄那一大堆丫鬟和宫女的传说以及红学爱好者的狂想中走出来,渐渐显露出本来的样貌。这些传闻和闹剧不仅是娱乐的产物,它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狭隘、脆弱和肤浅,人类总是把虚幻的血统看作荣耀。然而,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历史真相毕竟与任何民族主义无关,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这和康熙的祖母是蒙古人一样无需避讳。天嘏的《满清外史》中曾经提到: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洲人,因此经常在宫中身着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个汉人。虽然这本书中“乾隆生于陈家”的说法是错误的,但这个“身着汉服”细节并非杜撰,乾隆的确喜欢穿前朝明代的服饰,并且经常请画师为他作身穿汉服的画像,这些画像至今仍保存着。
如果乾隆的母亲钱氏确是汉人,并且确是远古吴越王钱镠的后代,那么乾隆喜爱汉服,并且把身穿汉服作为一种荣耀,便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些画像只能作为旁证,乾隆对汉服的情有独钟未必与他的血统有关,就如同雍正皇帝虽然喜欢穿西装,但不能以此判断他是欧罗巴白种人。
然而,乾隆的母亲究竟是谁,并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乾隆皇帝这个人,也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清代的历史。毕竟乾隆是一个汉族人还是半个满洲人有什么关系呢?华夷之争来自于狭隘和封闭的心灵,大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然而他们的籍贯何曾影响他们伟大的光辉?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因文化母体而统一的文明古国。战争、融合、同化的漫长历史都决定了这个文明的特质,决定了传承的阴暗与光明、奴性与理性、沉沦与觉醒。历史是被偶然性与必然性推动的,乾隆的血统是偶然的,但乾隆朝的历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必然的。作为皇帝,作为统治康雍乾盛世顶峰的君主,乾隆皇帝固然荣耀之极。他登基后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减免捐纳,平定叛乱、统一新疆、治理西藏、兴建河务、编修文化典籍……然而,他在现代人的眼中并非一个无可指摘、圣德贤明的统治者。乾隆皇帝一生好大喜功,发动战争、修建园林、重用和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致使国库空虚,康雍乾盛世在他死后戛然而止,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一生都在为挽救帝国的衰落而奔波劳碌。乾隆皇帝是个古人,做不到现代意义上的高瞻远瞩,他有功亦有过,并非十足的明君。然而,乾隆无论是什么血统,都曾是中国的皇帝。乾隆无论身体里是否流着吴越王钱镠的热血,都曾同样为百姓兴修水利。这已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