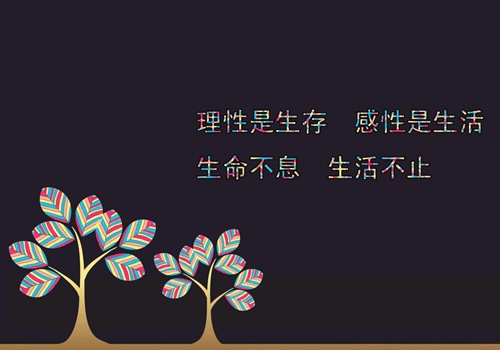一
太阳终于出来了,尽管是在下午,小区对面的楼房依旧镀了层柠檬色的光。生命是华贵的,那一刻,砖瓦都是饱满的。
生了病,很漫长的病,记忆里从没病得如此之久之重之疲劳,恋着床,恋着睡眠。窗外风声、雨声、市声混沌着。雨下得缠绵,没完没了,早春模糊,像我的睡意。躺在床上,想着新鲜的玉兰是否开了,湖边的柳是否垂了线,大自然那么鲜嫩,干净得像个孩子,该来的终会来。
昨夜,还听到窗外马路上,一个小男生撕心裂肺地在哭,不知受了啥委屈,用了那么大的气力。须臾,又听到一个大人急吼吼的声音,想着成长真不易。醒来却是安静的,朝暾初上,白白的一个世界,仿若什么都不曾发生,倒像是自个的一个梦。
病情反反复复,期间听了一场课,赴了两场友人的邀约,以为无碍,却愈发重了。听朋友的话,用深桶子泡了腿,发了汗,煮了红糖姜茶,买了温度计。没输液,是懒得上医院,走到半路都折了回来。那样的嘈杂,费时费力,让人着实难耐,一味的依赖抗生素也不好。
日子就这样慢慢挨下去,一天天,竟有点恐慌,像一朵花的香气,说没就没了。好久没打字了,日子都薄了。有时候,甚至想还会不会再写下去,净是些废话,自己都不愿意听,又说给谁。什么时候能站在时间之外,写一个故事,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有关生命美学和低微内心的。那样的吐纳,像瑜伽,再自然不过。是自己收藏的一条河流,从这端到那端,白茫茫一眼无尽。而不是花朵,这是两个概念,就像美和艺术从来都不一样。美是天下的,而艺术注定是自己的,有“我”的介入,方为真趣。
花是美的,但不是艺术的,只有进入人的感情领域,窑变成自己的色泽,再一次呈现时,方是艺术。所以那个画家死在了异乡,他的画多不成比例,变异孤独,那是他的眼睛,深藏纸中,后面的属性和标签才是大众的。艺术是缓慢的,精神上的教养,上帝解渴的声音,那么微弱,要说关乎别人,也是别人的艺术艺术了你。就像这个春天一定还幽居在某个路口,不打扰人,也不被打扰,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
二
长时间囿于病榻,忽然怀念起那些健康的日子,活蹦乱跳的该有多好。
秋其来信了,这是她好久后的讯息。那一刻,有泪滑过,我知道她也病了,病的不是身,而是心,比我重。
她居山里,那么寂静,像另外的一个我。那个尖顶铁皮瓦的木屋,我曾在纸上见过,似一个红色的童话,幽暗在一棵棵古杉里。不远处是一座天主教堂几何样的塔尖,很多个夜晚,秋其下晚自习独自从那走过,寂静的山路,只有她皮鞋的回声。那幢木屋,起初是位传教士的寓所,后来住了个武汉人,再后来成了她婆婆的婆婆的家。
老婆婆一百多岁了,经常坐在券廊的竹藤椅上和猫咪一起晒太阳。精神好时,会把猫咪塞进大围裙兜里,和秋其的孩子叮当一起抚摸梳理猫毛,听猫咪喵喵地叫。光阴的细纹落在那,秋其在老婆婆的身边摘菜,晾晒衣物。四周安静,只有墙壁的闹钟滴答滴答轻响。
老房子就这么老着,和老婆婆和那些日久年深的木纹,窗前挽起的藤蔓,以及有着新鲜生命的叮当。没人知道它确切的历史,老婆婆老了,有些事记不得了,秋其整理文献时,也未曾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秋其说这只是一个生命的巢穴,尘世的庇护所,无论作为有着怎样历史记忆的老别墅,还是简陋的木板房,现在只是一幢普通山民的住宅,一幢保护和关怀她们简单生命的房屋。狭窄的木门,锁眼,窗棂,有火,有烟在屋顶上嬉戏。
院子是安详的,晒着一簸箕一簸箕从山里摘的野茶,竹竿上挑着各种被太阳晒干了的野蘑菇;鸢尾、含笑,洁白香浓的栀子,细细森森开了一院,和这座山中万千植物样,都是秋其深爱的。冬天来时,她把它们挪进屋,和家人一起取暖。
背包客也会误入这条小径,举着相机,询问些植物的名称或有关这座老别墅的身世。秋其会含笑告诉他,他摄下的那朵花叫含笑。他们不知道这个清秀美丽,长头发的女子是谁,不知道她叫秋其,不知道大山予以她纯良温净的性格,以及丰厚的内涵。她的心思,是座博物馆,里面盛满了山川、河流、时间、人物、图案、青草般的气息。她是自然的,她的思绪像曲折的山道,柔韧的山风,绵长而悠远。
秋其也在廊檐下扫落叶,收拾孩子的玩具,用笔记本记下一些零散的思维。那些朴素柔和充满恩泽的文字可以激发我的灵感、表述,以及对生命的另一种体验。所以她柔美的灵魂不单单只属于自己,那是山顶流下的清泉,每一个路过她湖泊的人,都会照见自己。
她说下雨时,那些雨点打在铁皮瓦上,以三级跳的形式再跌落在一楼地板上;她说晴天,是从窗帘被染红的那刻开始的,她搂着叮当,那些美丽的线条穿过松软的棉絮进入叮当的身体,孩子熟睡着,小手掌里还安静地握着一片,而大山早已被唤醒。
她在她的书房里给我写信,那些小信像蓝色的雪片飘入我的窗口。搬家时,我曾卖掉过书。她说:想哭!每一本书,都是静静围绕自己膝头的孩子,也都是我们转过身去的昨天……”那一刻,四壁的纸张是温柔的,时间静静流淌在每个细节里,她用眼睛深情地抚摸着,它们都是她的孩子,她给它们以安全的臂弯,引领着到达一个光辉的所在。那些哲人都是我们回身的亲人!
就像在一座大山面前,她是那么庄严,是女儿也是母亲!
她在信里说:“真正爱山敬畏山的,是山林的土著和她的山民。守山的山民走了,商人多了,山热闹了。今天散步走过戴笠别墅和西哈努克亲王别墅,天下起毛毛雨,在那庭院里站了一会儿,不知为何泪流满面。显然不是为了来去匆匆的著名政客和领袖。”
合上小信,我呆呆地望着窗外香樟还没来得及换掉的叶子。知道她心疼什么,为何落泪。我们迷恋的时间走了,生命里的根须轻而易举地就被折断。那座山不再是过去的那座山,没有等我,美好的影像只留存在曾经的纸上,秋其的文字里。那座木屋也没有等我,都将不复存在,这也是她半年来纠结低落的原因。她深爱着它们,每一片叶子,每一条溪水。
她说她收到了我的新书,带了一本放在办公桌上。左边是普里什文的《鸟儿不惊的地方》、苏子《东坡志林》,右边是林文月《京都一年》、阿姜查《森林里的一棵树》。她说我会喜欢这些邻居的,她把我和一切美好的事物放在一起,不管我是否惭愧。
她说里面的文字她都熟悉,现在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忽觉隆重。我题写的几个毛笔字也让她感动,写字是日课,一笔一画且行且珍重。“隆重”多好呀!但那不是纸给的,是秋其。就像她一直想给一座大山以隆重和祝福,但办不到。人都是轻的,尘世间的一根羽毛。
先生在朋友圈看到我生病的消息,发来秘方,嘱我坚持泡腿,喝生姜红糖水。先生还给我画了画像,我生平里的第一张画像。那么像我,五观神态及散发出来的气息。油画是漫长的,需一遍遍上色,干了方能继续。我不知道先生用了多久的时间,一个月还是半个月,总之,从这个冬天开始,就在酝酿。雪一直在下,天气极寒,白白的一片,十多年没有过的场景。只要稍停,先生就去画室,打开电暖气,安静作画。
?先生是位老人,每天看书,习字,挤公交,烧三餐饭,有时还拉着米袋子上楼,中间往往歇上几歇。先生简朴,一身布衣,隐匿在这座小城。我不想用任何形容词来形容他,那些东西都很脆弱空洞,他身上的仙气是漫长而严肃的岁月给的,也是艺术的转换。我曾开玩笑说,先生即便掉到灰堆里,都有出尘之美。的确如此,有些东西是遮不住的,哪怕再大的苦难与疼痛。
先生轻盈,心里只有艺术,画着画着就忘记了时间,那种状态真好,松针落地,一片寂静。“给内心世界以自由,打开一切闸门,你会大吃一惊的发现,在你的意识里,关着远远多于思想情感和诗的力量。”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是人世间留给这个古城最美的礼物。而画像,是我病中,以致一生收到的最美最珍贵的礼物。
我从不未向先生索过画,更别提画画像。就像我不喜欢别人向我索文样,每个人的劳动都应是喜悦的,那是内心的光芒,不被浮云遮蔽。我更喜欢距离,那是对他人的尊重和自我固守的自尊。先生用了稳重的咖啡色调,大公报做底,衣服的领子高而贴服。照我照片画的,只是置换了年代,像一张老旧底片的翻拍,那是唤不回的记忆,对美和一个时代的追忆。
先生从来不运作自己的画,他学生画作的价格已然不菲。先生是安静的,很多东西打动不了他。还艺术以初心,他一直这样做,就像他十几岁时捡烟头,那时的烟头没过滤嘴,烟丝烧不尽,拾得多了,可换分分钱,好久才能买一本美术方面的书籍和文学上的著作。《金蔷薇》就是这样来的.,如老沙梅样,他打首饰,先生买书。他们都在淘金,都很纯粹,现在依旧是,所以我敬爱这种人生。
四
前几天我出去买菜,天是阴的,风摇动着香樟的树梢,并不觉得冷。是春天的风,恹恹的,绿是老绿,并没些许新意。梧叶还没掉光,焦脆地挂在光秃的树杆上,风一吹,哗哗作响,似干花。这样的寂寞真好,如贴上去的简笔,只是一个轮廓,没太多的意象和心事,离冬不远,离春也不近,就那么清寂着。
一棵树总是美的,春天时鲜嫩,毛茸茸,有粉的声音一层层发生,耳膜是鼓的。纱帘外新煮了茶,白软软的,洗透了的香。春就是这样,飘忽着,一片叶子往往比一朵花更温和,更长久,更像春天。即便到了秋,通体黄透,一大片一大片往下掉,也是别致的。在路上,被风簌簌地刮过来又刮过去,那么惆怅。每晚散步,卷到脚边,俯身拾起一片,带回去放在飘窗上,夜便殷实起来。
季节,只不过是随手拧亮的一盏灯,时光是矮的,笼着伏案的人,那层暗桔色,柔和而考究。安静里,多少人睡去,又有多少人安静地醒着。
风扬起大衣的摆,慢慢地走着,并不急着到菜场。身边的门面都熟悉,生意并不好,冷冷清清。没戴眼镜,世界是模糊的,看不清任何人,这样倒好,仿若路上只有自己,街道也就变成了一个人的街道,那么空旷,如在旷野。
很羡慕那些不知疲倦的车,没有归期似地一直往前开。心里想着要是不买菜就好了,便可节省下时间做些喜爱之事。
菜场里没人等,熙熙攘攘净是些陌生的面孔,只有一次看见自己的爹妈提着袋子站在那选菜,袋子里装有香葱,绿绿的。我抱了一枝梅,夹了叠宣纸,远远望过去,老太太穿了件鲜亮的袄子,戴了顶帽子,半指手套,低着头,很干净的样子。帽子是我买的,一眼的喜气,安稳得像年画。生命奇妙,俗人俗事的光环,亲切到到哪都能碰见。
还有一个卖鳝鱼的,脸上有条疤,红赤赤的,是个女人,四十来岁,也卖螃蟹、黄颡和财鱼。我每次去都找她买。她没门面,只在路口进去不远处就地摆个摊,两个盆子,一块板子便是全部的家当。她麻利,笑得也轻盈,一边低头做事,一边应答着,偶尔抬头,也是明媚的。她收拾鱼,回身从摩托车龙头上扯下袋子,撩起旁边盆子里的水洗手,在围裙上擦一把,接钱数钱找钱,动作像流水。阳光暖暖的,照着简陋的菜场和她的脸,那么好。她不丑,挺好看的。
关键是她对我好,鳝鱼卖别人35元一斤,卖我28。28是我还下来的价格,也就成了惯例,不管年节,她就这么卖着。即便饭馆成盆成盆的要,也比我的贵。她不关秤,高高的,还价也不反感,嘴里笑着说卖不起,却一如既往收着老价钱。她卖的是野鳝,真正的黄鳝,个头肥大,炒出来鲜嫩,肉翘翘的。
有一次,我买了她的螃蟹,是公子,又跑到里面称泥鳅。贩子问多少钱,咋不买她的,也是个女的。我询了价,她说58,我说我买的价格你卖不起,她问多少,我报了价。她说下次来,我也这个价给你,可知菜场的水有多深。一个男人过来,并不还价,提着便走,这点女人总是显得琐碎小气。
每次去,依旧寻巷口的女人,有时候走过去,又倒回来,重新找一遍。她若不在,便很失落,向旁边摊位打听,卖花的告诉我,她家里最近有事。能有什么事呢?心里不免嘀咕起来,是不是儿子要结婚了?这一想,自己倒笑了,纯属杜撰,于她知之甚少,有没有儿子,真不知道。也会想她是不是病了,水那么深,天那么冷,那双手泡得那么白。又想她脸上的伤咋来的,年轻时是否有过噩梦,现在过得好不好,爱人待她若何,一连串的问题。
总之。我开始惦记她,在这个菜场,从没这样惦记一个人,就像这个午后,我在键盘上想她,并写下有关她的文字。有一次,等了她一个月,要还她十元钱。见时,竟有点小兴奋。她说,不急的,你,我还不放心!
有个买芋头的老太太也好,七十多岁,胖胖的,低头坐在一个小木凳上修芋头,那么专心,花白的头发搭在前额。市场闹哄哄的,独她静,像尊佛。她修的速度赶不上卖的速度,五元一斤,恒温,年节不变。只要碰见,也准会买。回家改刀,放点葱姜蒜粒,伴点红辣酱,上笼一蒸,白白的一盘。有时只稍许点点盐,清淡着,像刚长出样
五
昨天短信提醒,云柜里有快递,过十分钟又提醒超时或出现异常已被派送员取出。停下手里的笔,跑到门房找了找,无果;又冒雨去云柜输了密码,提示这个号没待取件。遂疑惑起来,越发想知道是个什么物件,给快递公司打了电话,折腾几个来回。快递小哥说还在云柜里,拿出来,又放了进去,云柜最近总有点小问题,实在不行,明天他过来取。
没想到深夜十一时许,刚熄灯,有电话进来。拿起“喂”了一声,对方竟踟蹰起来,说是不是睡了。我问是谁,他报了身份,说把件取了出来,在楼下等。望了一眼窗外,枝摇叶颤,雨点噼啪,忙穿着睡裤跳下床,打着赤脚,想找件袄子穿。一想还病着,凉不得,遂向客厅捂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爱人喊,烦他下去一趟。
想着,这个小哥真有意思,这么晚了,又是风又是雨的,还记挂着。
另一个快递小哥也有意思。前几天,买了一条手绘的裙子,打开一看,远不是那么回事,质量草率得要命。没上楼,转身直接塞给他,烦他帮忙寄回去。快递小哥说,那你得和对方说好,我说不会,才学网购。他说那也得打个电话。一摸没带,他把自己的递给我,沟通后,我把手机还他,另给了十元钱。小哥回去,给我发来短信,说,他已原单寄回,不用快递费,把钱退我。
用平板看了几部电影,日本老片子,过去式场景,局促的小站,暴风雪的夜晚。小人物小故事,罪犯警察,人情人性,那么纯洁安宁,又那么温和动人,一点都不躁。女人安稳,如雪夜里的小店,不需要太明亮,却是暖暖的。不禁叹息,日本的女人真不错,心里安详,植了香气,有教养,没被打劫过。
每天坚持临两篇字,给老师交作业,老师在那边等着呢。
写到这,忽然觉得老南门外的樱花是不是要开了,若开了多好,雪一样一层层落下,纷纷扬扬的,整个春天就下下来了,巷子里也就染上淡淡的香。
一道风景线,镶嵌在乡村的房前屋后,没有花红柳绿,却很温馨,令很多人陶醉。
一种文化现象,伴随过无数个朝代,任云卷云舒,看花开花落,如今还在延续。
在东北的农村里,每年到了挂锄农闲时节,或者冬天“猫冬”的日子里,农民们就闲了下来。偏僻一隅,没有百货商场可逛,没有娱乐场所可玩,特别是中老年人,他们活动的范围就更小,就前街后道的左左右右几百米的地方。人不怕累,就怕没有人唠嗑说话,所以,大家就开始找个夏天背荫,冬天阳光足的大墙根下聚堆,东扯葫芦西扯瓢,千年谷子万年糠唠了起来,姿势千态百中,有站,有坐,有蹲,大家管这种现象叫“蹲墙根”,够形象化的吧!
我小的时候,听见过祖父那辈人蹲墙根讲张作霖大帅和吴佩孚的传奇演义,稍大一点以后,听父亲那辈人讲杨子荣抓座山雕、蝴蝶迷的故事。后来,工作在城里,偶回到家乡原来小村子的路拓宽了,房子也实现了砖瓦化,大家的穿戴也时髦一些,般大般的年轻人头发白了,老年人拄上了拐棍。可是,蹲墙根的风俗习惯一点没有变化,他们还是有的坐在马扎上,有的偎在石头墩上,或者闲聊,或者抽烟,或者起哄,悠然自得,无拘无束地比比划划,扯东聊西,聊得没完没了,生活得仍然是那样地滋有味,那样地甜蜜滋润,真叫人羡慕。每次看见他们,感觉家乡还是那样纯朴,那样和谐,那样地可亲。
蹲墙根的地方,一般都是在大街面上,比较高岗的院门外,地点相对也不固定,随着一年四季的天气情况而转移着。春天和冬天,北方比较冷,大家就选择在落太阳光面积大的地方。夏天和秋天两季,会选择在阴凉处,或者老榆树下,以此轮回,充分享受着阳光给墙根带来变化的舒逸。
蹲墙根是没有人组织的自由活动,但却有相对固定的队伍,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左邻右舍的邻居,以中老年人为主。开始是几个个老年人闲来无事,随意找块暖阳处或者荫凉的地方坐下聊天,而后又有其他中老年人加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慢慢地队伍逐步壮大,并相对趋于稳定。说趋于稳定,实际上也是动态的,因为蹲墙根的人从来就没有组织观念,也没有纪律约束,愿来就来,愿走就走。也没有考勤之说,没有规定固定到岗和回家时间。有人不来,其他人也不会为此牵肠挂肚,只是偶尔可能问及。有人中途退场,也没有人极力挽留。大家都习惯了,闲的'时候,茶余饭后,不去蹲一会,睡觉都感觉不踏实,总觉得心里缺少什么东西似的。岁月更迭,生老病死,大浪淘沙,蹲墙根的人员年年发生变化,老的走了,年轻的变老了,一茬接一茬步入了这个行列,蹲墙根的队伍也后继有人,就这样永远延续着。
蹲墙根大家议论的话题也是不固定的,谁也不必事先准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也不必负啥责任。虽然有时候,为了一个问题争论面红耳赤,起誓发怨的,但是,谁也不往心里去,扯完就拉倒。蹲墙根的人一见面,如果是刚吃完饭,往往都是口头语:“吃了没有?”。然后,消息灵通的人开始口若悬河地传达一些村里村外的新闻趣事,交换一些对世事的评论,或深或浅,或中庸或偏激。也有的人,没有多少文化,硬是装文化人:“昨天我看报纸了,报上说,柬埔寨内乱了,‘诺罗敦和西哈努克亲王打起来了’……”。旁边的人不服:“你懂啥啊,诺罗敦和西哈努克亲王是哥俩,怎么能掐起来……”。正在看下棋的“大眼镜”把棋子一划了:“你们两个都是不懂装懂,诺罗敦和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个人,人家叫诺罗敦.西哈努克”。大家哄堂大笑,把院子里的鸡鸭惊得“哏嘎”乱叫。
老母猪拱酱栏子,家雀扑楞房檐子……,不管大事小事,真真假假,能不能对上岔口,顺口开河,大家伙图得就是乐呵。
你给我一支烟,我和你对个火,一个香瓜在裤子上擦几下,掰开几掰,大家抢着吃,讲一下“荤段子”,甩几句歇后语,开开玩笑,你乐我乐大家都乐,痛快淋漓。
在墙根下,大家开玩笑基本都是围绕“老婆”逗趣,谁的老婆漂亮,年轻,同他开玩笑的人就越多。言轻言重都无所谓,不动真格的就不急眼。发言也随意,没有领导,不用考虑年尊长幼,处处透露着和谐。蹲墙根虽没有主持,但是,一些阅历丰富,有文化的年轻人,大多是中心发言人。因为他们经常出门在外,经历多,见识广,说的都是新鲜事,青年人也都有表现欲,老年人都愿意听。我回老家的时候,就经常去蹲墙根处和原来的发小唠唠嗑,听他们讲奇闻异事,国内外大事小情,有些人比我还关心国家大事,分析的问题比我还深刻,思想比我还进步。
是啊,时代变化了,中国农民的思想也变化了,俺东北父老乡亲再也不是反穿皮袄喝大碗酒时代了,他们也在奔小康的路上竞风流。
蹲墙根人,不光是消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心存一种期盼。特别是现在,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是分家单住,在这里等候,眼望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孙女从眼前走过去,不管是背影还是听见声音,心里就满足,就是一种幸福。
蹲墙根,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一般不掺和,现在不同了,除了大部分青年人出村打工外,村里留下来青年人农活也少了,农田基本都是机械化作业,不用人铲马趟,消闲的时间也多了,他们也参加了这个行列。他们谈论最多的是电脑,微信和科学方面的问题。老年人则在一旁抽自己卷的旱烟,一边唠他们的古老话题。纯朴的乡下人,生活就是这样自由自在,享受着冬日暖阳,夏天的荫凉,过着这样闲散的日子。这不也是人生里的一种幸福吗?一种享受吗?一种社会和谐最现实的反映吗!
幸福是什么,是天天不愁吃穿的玩乐?是多年的梦想终获得成功?是身边拥有年轻貌丽的红颜知己?是在人生灾难中的重生?是平凡生活中突中大奖的幸运?是仕途上升官发财……?我问过很多人,答案都不同。我冒然问了我的一位农民朋友,他回答叫我目定口呆:幸福就是在晚饭后,老哥们几个在门前墙根下唠嗑,看火烧云……
我明白了,蹲墙根这道风景,为什么能够这样地靓丽,花开不衰!
我小的时候父母就喜欢花,喜欢的如痴如醉……
大概是1972年,柬埔寨国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访沈阳,为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沈阳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仪式,男孩穿上了白衣服,蓝裤子,女孩子也穿上了花衣裳,在那个摧残人性的年代,好久没有看到女孩穿花衣裳了。人们的生活逐步走向正轨,虽然戏匣子还是只唱着那几段样板戏,但大胆的人们也开始在平淡枯燥的生活中寻求美了,在自家的窗台上摆上几盆花,这在那个年代真是有点不同凡响。
我的老姨夫会养花,老姨家里住平房院子也不大,可家的前后院养满了花,让童年的我好不羡慕。那时外祖母还健在,外祖母常住咱家,偶尔也住我姨家,我也时常去我姨家去看外祖母。正值盛夏,灯笼花开得正旺,煞是好看,(灯笼花生长的花总是整齐、对称的而且很像灯笼,就像贴在灯笼上的剪纸。贴在宫灯、纱灯、笼式灯上的灯花一样具有对称性。而灯笼在中国代表的是吉祥、安宁)。
外祖母见我也喜欢灯笼花,就偷偷地剪下一个杈,让我回家压在花盆里,可过了半个多月,灯笼花还是蔫蔫的没活,我有点失望。母亲看看蔫蔫的灯笼花长长地叹息一声。父亲安慰我们娘俩说:这是盛夏,花是不爱活,春天栽花花,爱活!春天,我期盼春天!
第二年的春天,老姨把栽活的灯笼花苗送给我家,灯笼花是木本植物,喜欢太阳,喜欢风吹雨淋,室内养活,花也不开,苗也不爱长,我小的时候家住在铁西区工人村的.一栋苏式楼房的一楼,家里没有阳台养花,而室内养的花大都不爱开花,即使开花也不艳丽。父亲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决定在窗顶上用木头钉上了木架,这样可以摆上几盆花,本来可以弄个铁的,铁的结实,可父亲从来不爱占公家一分钱便宜,更不愿因自己家的事麻烦别人。父亲不是木匠出身,做这样的活有点难为父亲,父亲一边钉花架,母亲在一边帮忙,见父亲累得满头是汗母亲赶紧为父亲擦汗,花架钉得不漂亮,但终于有了自己家的花架母亲高兴。母亲理解父亲,理解父亲,不占国家一分钱的品格
四月的天,天气说暖就暖和起来了,父母决定把花苗挪到花架上,外边的阳光足,再加上浇些发酵的豆饼子水,花苗长得快,二十几天就长出了花蕾,让父母喜之不尽。一天,细心的我发现灯笼花开了,我把这件事第一个告诉母亲:是吗?母亲半信半疑,赶紧拉着我的手去窗外看,可不灯笼花已经开出了好几个花了,在夕阳的映衬下格外美丽典雅。母亲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让我去告诉正在忙碌晚饭的父亲。栽种的希望终于开出了美丽的花蕾,父母喜之不尽。
灯笼花不仅花开得艳,开得多,而且花期长。到了伏天雨水大,风也大,母亲让我把灯笼花花挪到屋里,可第二天花蕾就会脱落。让母亲心疼!于是还是把灯笼花放到窗外。任凭风吹雨打,经过风吹雨打的灯笼花更健壮,更挺拔……
到了深秋,父亲会把灯笼花挪到屋里,长得高大的也被剪枝,灯笼花会在室内越冬这时的灯笼花也不会开花,会长出小杈,到了来年的春天,父亲依旧会栽上灯笼花花苗,热心肠的父母还把花苗送给邻里同事也让大家一起感受灯笼花的美,夏天依旧会看到美丽的灯笼花,就这样,年年如此,父母年年栽种美丽的灯笼花,栽种美好,栽种希望!
可爱的灯笼花,陪伴我们一家走过了那艰辛的年代,也让年少的我觉得即使在那样清苦、平淡、枯燥的年代,照样生活中也有美好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