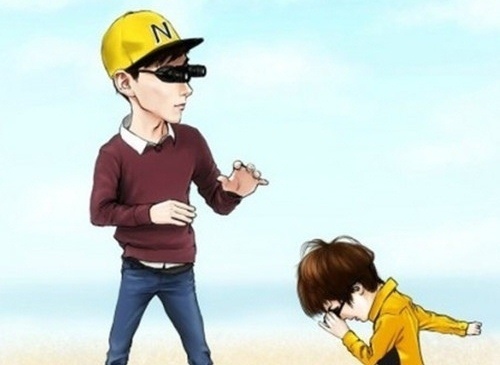笼子里的鸟现代散文
我不知道当初人们在制造鸟笼时,真正的目的和用意是什么。但根据其用途而看,是用来装鸟儿的。那么,为什么要将鸟儿拘束在笼子中?也许是鸟儿羽毛艳丽,体态轻盈,叫声婉转而动听。为了将这种美保留下来,故而如此的吧。这也许就是鸟笼制造者的根本用意。
可是把鸟儿关起来,就当真能得到其真正意义上的美吗?就像是采摘花瓣,不久便会枯萎,是得不到花儿之美的。凡有生命之物,都有求生的意志,也有渴望依其本性而存在的愿望。那么,鸟儿的本性是什么?是自由采食,嬉戏,飞翔与繁殖。关在笼子里的鸟儿,已失去了大自然所赋予它的灵气。它不会叫出婉转动听的歌声,也不会挥动轻盈的翅膀。
鸟儿起初被关在笼子里,会不停扑腾、嘶叫,想要摆脱笼子里的束缚。可是它柔弱身躯是无法冲破那坚固的囚笼的。待得知一切挣扎只是徒劳时它便会停止反抗,静静待在里面。也许鸟笼设置着的目的,就是让鸟儿进去后不能再出来,并且希望鸟儿自己因不能出来而最后不想出来。有时候,当鸟儿被关太久时,即使打开笼门,鸟儿也不会飞出来。这其实是人类的悲哀,也是鸟儿的悲哀与不幸。
制造鸟笼的`人,用笼子关鸟儿的人。都是拥有可怕的自私,有极强的占有欲。其实我们喜欢和爱一件物事,难道就非要占有它吗?如果对物本身没有什么负面影响,那倒也还罢了。而如果因占有而使这件物事有所损耗,我们又于心何忍?难道又能算是对其有根本性意义上的喜欢与爱吗?将鸟儿关在笼子里,得到的是什么,是自私的占有欲以及自欺欺人的本质,此外别无其它。而且此举,也大大显示了占有者本性的卑鄙与可恶。
其实处在笼子束缚里的鸟儿,得不到自由。可是它被关着,当有一天失去了对自由的渴望,失去了飞翔的雄心,失去了对牢笼的反抗。那么这样,才是最可悲的。被关在笼子里出不去,是外界因素强加的,没有办法。而如果自己束缚自己、囚笼自己,毫无飞出笼子的意愿和想法,而甘于忍受一切时。那当真就能算是无药可救,极为可悲了。
春天里现代散文
一
植物随春出新,动物随春出蛰。惊蛰,被惊醒了的不仅有植物、动物,还有人。钱钟书有文章说,春从窗户进来,人坐不住,就从房门出去了。
这真是“满园关不住春色”的时候,重楼铁门也关不住猫冬的人们了。人一定要出去看春,窗户映进来的是平面的,有限的,出去,到街区、公园、山水间去看,可以旋转着身子,360度空间立体看。抬头看天,低头看水,六合之中处处春意盎然,缤纷得如万花筒。杨树“狗”先长出来了,一只一只,毛茸茸的,滴里嘟噜挂了满树,树上小小的叶子半卷着,浅浅的绿色。如果真的嫌这绿色太浅了,那么,就去看柳树,这时正是“远看笼烟,近看滴翠”的状态。路旁的柳枝极为热情地在人们头上搔首弄姿,时不时地随风低下来抚一抚你的脸,一幅可人之态。而江边的柳,老干如虬,细枝长软,在风中轻轻摇弋,受了诱惑般地逗波戏浪,一幅顽皮之态。
这个时候,看庭院里的树上的花,小小单单,连翘满树,黄雀衔枝,又多又密,闪闪发光,给颜色尚未浓烈的春平添了几分闹意。之后,杏花、桃花、榆叶梅、梨花、丁香花纷纷大闹起来,让人目不遐接。山野间最火爆的是达子香,学名杜鹃,这小灌木是成片而生的,开花时,艳紫色如云落坡,灿烂无比。
在赏春的时候,我总会顺便关注农事,这大概和我是农垦人有关,退休多年仍不自觉地关心农垦农事,是习惯成自然,积习难改。在岗时,春天里我去过许多个农场,每个农场的春景不尽相同,但春忙是一致的。从中,能看到农垦不断向前的步伐。还记得那年五一,我在宁安农场采访结束回牡丹江,汽车沿着大道一路向岗下驶去,就要驶出场界时,留恋地回头一望,视觉远处,垅直田方,一林新柳笼烟浮雾,丛丛怒放的小桃,红云蒸霞蔚,地里红牛拖着绿机在欢跑,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盛春图。这景色不正是农场前景的图绘么,岂一个“美”字了得!
二
说起拍春,在今天相机几乎普及,有拍照功能的`手机几乎人手有之,拍摄工具爆炸,功能更全,我不是专业摄影者,也无先进的摄影工具,更无专业水平。我的那些照片,不是摄影艺术,是留存,是留下春的足迹。看着城里的风景,向往田野的风景,特别喜欢看北大荒老新闻工作者QQ群,那里经常发农场的风景,自然的、人文的,新鲜漂亮。
我把拍春的片子都一一整理存盘,在非春时节打开重新欣赏。尤其是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酷冷猫冬,百无聊赖之时,欣赏春的画面,权当一次愉快的春的卧游。
拍春花,看上去万紫千红、热热闹闹,但仔细想想有些常识并不是很清楚。拍花记下日期,可以掌握规律,掌握它们美貌的最佳时候,而有些花种曾比较模糊,我一直不知道杏花还有白色的,一查资料,才恍然大悟。
最让我惊喜的是,我从中发现春植的萌发是最自由浪漫的。有开花后出叶的,有先出叶后开花的,有出叶同时开花的,真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没有统一步伐,没有统一行动,自由散漫极了。这样回头一想,春的肚量这么大,心底这么宽宏,天底下再无它物可比了。我赞美春天,赞美它的烂漫缤纷、生机勃勃之外,更赞美它鼓励各行其是、争先恐后的热情。
拍春花,更能具体感知当年气候与往年的不同。以连翘为例,近两年都是三月二十七日前后明显吐黄,去年春寒暖缓,四月二十四日才开,今年四月四日就开了,相差二十天之长。传统习俗中有春季祭风神的活动,以此请风神息怒宽怀,将小风微吹,让花开得好些,时间长些。我想对掌握气温的大神也须一祭,让她乐呵,天也就暖得早些、快些,花也开得早些、多些。
三
赏花拍花,引出许多爱春、赏春、惜春之情。光赏春是不够完整的,还要纵情咏春,当然这不是我的发明,古人的春诗给古代的春增添了多少锦秀,那不是刻意之为,那是愉悦心情的流淌。今古景色一样美,今古赏春心情一样激荡,今古一样有许多写春心、春怀、春景的词句,砌出了春的美妙诗章。
整理咏春的诗词,发现我寻春的脚步是从立春开始的。立春的节气,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大冬天呢,但“立春”这两字却很有温度,立马让我有着一股迎接春的冲动。眼前景物如旧,心中春风吹拂。在这种情绪的鼓励中,诗咏的句子无奈中掺着热情,企盼中杂着急迫。之后,一个节气一首诗,一个节气,增一分欣喜,翻着日历,读着农谚,和着诗歌的节拍,眼前不断幻化着天气物候的变化:惊蛰时节,看到了蝴蝶飞、小虫跳;清明之后,杏花就开在我眼前了。
等到春来园中山野上的时候,就赏着实物、写着歌咏了。春序一个接着一个,春程一程接着一程,一路走下来,一路咏下来,花草从初到盛,农事从备到动。初春,盛春,晚春,如一幕歌剧,从序曲,到高潮,在这之中,我满天洒笑,满地寻诗,赏春,咏春。
是春草、春花、春树、春云、春雨构成了一个自然的春季,有了赏春、读春、写春、咏春,才构成了一个人文的春天!
棉衣里的母爱现代散文
现在每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大家到会穿上羽绒服,来防寒保暖,几乎每个人都一样。那种用纯棉花手工做的棉衣,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小时候,每到冬天,我和妹妹都能穿上母亲做的棉衣,棉衣里的棉花是母亲亲手栽的,从小苗开始,施肥,除草,打农药,修剪棉花,直到开花结果。收获的季节,母亲就带着我去棉花地里,摘到篮子里收到家里,晒干后把棉花弹好,给我们兄妹做棉衣,棉鞋,从来没有让我和妹妹冻着。
记得小时候,缝纫机在农村还没有普遍,母亲还很年轻,做棉衣服很在行。母亲做衣服的动作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母亲喜欢戴上顶针,一手拿针,一手熟练的穿线,还不时地用针在头发上抿一下。做到厚的地方,用针扎不动,母亲就用戴在手上的顶针轻轻一顶,针线就出来了。针线活看着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啊,因为不小心还会扎住手。母亲用一双粗糙的手努力地改变着家的贫穷,全家人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这也给家里节约不少开支,更主要的是穿着舒服,穿着暖和。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偷偷拿出来穿,出去让小朋友们看,他们都会不住的赞叹,也会投来羡慕的眼光,那时心里别听有多高兴了,感觉很过瘾,棉衣上因为玩耍总会沾上灰尘,母亲也会责备我几句,不过自己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多少年过去了,母亲也慢慢的老了,眼睛也变得模糊,看东西非常吃力,而我却像母亲哺育幼苗的棉花一样渐渐长大,开花结果,娶妻生子。母亲做棉衣也力不从心了,羽绒服代替了母亲的棉衣,个人的衣服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母亲就显得有些孤单。也许穿棉袄干活有些笨,手脚也不灵活,羽绒服相对来说干活利索一些,也暖和,对我来讲,母亲的棉衣就有些显得多余了。
很多时候,我几乎遗忘了母亲做的棉衣的存在,身上穿的羽绒服里有没有棉花也无所谓,反正不冷就行了。去年春节前,记得妻子给母亲买了一件羽绒服,母亲不很喜欢,母亲还是穿着自己缝的棉袄。今年冬天来临的时候,母亲还在电话里还嘱咐我把棉袄穿上,她说就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我急匆匆的打开行李箱,那件深蓝色的棉袄呈现在我的眼前,泪水不禁迷糊了我的双眼。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不惑之年,才深深地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一阵难过涌上心头,我用责备的心理悔恨自己。母亲的关心我从未真正放在心上,对母亲的关心我也做得很少。“儿行千里母担忧”,看着行李箱里的那件深蓝色的棉袄,想起母亲的棉衣带给我和妹妹的快乐,总感觉愧欠母亲的不只是那份亲情,还有母亲对我无私的爱。因为母亲知道她大半辈子的操劳也不知道最终能收获多少,但在她的内心里,在她的笑容中,总能寻找到平凡的满足,简单的衣物只能看到她外表的穿着,而永远也看不到她咽到嘴里有多少苦涩的野菜。
几多往事,几多辛酸,我感到自己为母亲做的远远不够,而母亲却给与我温暖的亲情。一件棉衣,一件棉鞋,包含了母亲对儿女的期盼,折射了母亲的伟大胸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今天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远在他乡的游子,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母亲,祝福家乡的母亲健康长寿。
冬天里的农家人现代散文
当家家户户用拧好的稻草绳,把菜地里的大白菜,捆扎严实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农家人的冬天就要到了。
江汉平原的冬天,江河湖面吹起的阵阵寒风,刮在人们的脸上,吹进人们的家里,显得有些阴凉。
早晨起来,太阳照射在大地上。晶莹剔透的霜花,粘附着嫩绿的麦苗、油菜、路边的枯草。好像给整个村庄釉了一层浓浓的乳白。荷塘里,昔日绿莹莹的荷叶,根根枯管,片片残叶。荷塘边的杨柳只剩下光溜溜的枝干。一头老水牛悠闲地嚼着喂给的草料。
江汉平原的冬季,“干湖底”的日子,晴朗的天气较多。人们总会盼望下雪,哪怕只下一场,也会冻死不少的害虫,疏松一下土壤,期盼来年有一个好收成。
冬季是农闲的季节,田活收掇完毕,五谷归仓。壮年男女外出打工,春节才能回家过年。在家的妇女们,看护着上学的孩子,照料着老人。也日夜想念着城里打工的男人。
早饭也比农忙时晚了许多。暖洋洋的太阳,把呀呀学语的孩童和老人叫了出来,嘻闹玩耍,在吸着旱烟的老人面前晃来晃去。
原来的冬季,妇女们会趁天晴,去准备一些过年时“熬糖打豆腐”所要用的原辅材料。用大麦把麦芽生出来后晒干,把黄豆簸得籽粒干净,也会买些石膏块放在家里。最令人难忘的,是做炒米的糯米饭,用木甄蒸出来的,吃起来又香又甜。
现在到处都是超市,什么都能买到,省掉了很多。
但每年的腊货是少不了的。冬至数九,过了冬至,腌鱼、腌肉、鸡鸭、香肠……晾晒在屋檐下。当你走进村庄,腊味飘香,太阳下泛着油亮的光泽。
这些腊味,翻年后,外出打工的总要带走一部分。留下来的腊味,在家里的'人,一直可吃到来年的麦子黄。
农闲的冬日,如在元旦节,腊月逢八的这一天,都是农家人吃酒的好日子。年轻人带着孩童吃完喜酒回来,总要带一些“狮子头”丸子、金黄的油炸鱼给年迈的老人。时而还会听到阵阵鞭炮声和地方花鼓戏的演唱。喜庆的空气,便在整个村庄弥散开来。
冬天里的乡村,曾经是我生活过的地方,令我思念。我追忆,却无奈——“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