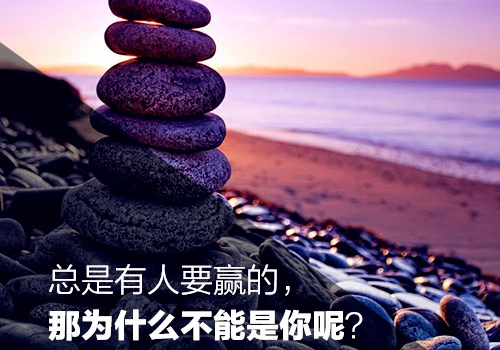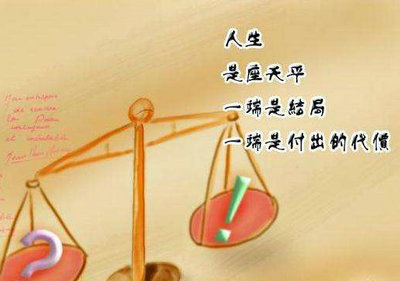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生活中有各种隐喻,比方说手上的掌纹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甚至一条隐隐约约的艺术线,都仿佛是一种对人一生的隐喻。所以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生活在存在之初,早已在生命之路上铺好了各种青石泥板,而这些你我走过却又不经意的瞬间,恰似一部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
以前不懂电影,还以为蒙太奇是哪个外国潮人的名字,随着观影量的增加和专业知识的深入,才觉得,品一部电影就如同在亲临一段人生。大部分人都会忽略导演在拍摄剪辑时的某一个特写或者移动镜头,而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拴在了剧情的链条上,至于那些曾经让导演、演员、灯光、道具等等工作人员呕心沥血、作用较大却并不很吸引人的场景往往需要观众的再次甚至多次回味才尝得出其中咸淡,感受到其中冷暖。
同样,生活中也常会有被忽略的场景。譬如我第一次坐公交车回家,作为一个资深路盲,因为没有找到我家附近的标志性建筑,故而错过多走了两站,无奈徒步返回。这当然只是小事难做正论,但如果是人生的转折处遭遇了诸如此类的情况,可就后悔莫及了。
所以电影又不似人生,影片喜欢可以看很多遍,不喜欢可以随时走开或者随手删掉,但人生只有一次,你想再次回味之时想必已是风烛残年之际。故而,自命不凡之我拥有年轻这最宝贵的资本,便更应该相信生活的隐喻,注重观察、主动回味。
事实上,生活要叫你该往哪儿走哪儿才会有天山的雪莲能起死回生,哪儿才会有昆仑山的紫金葫芦能装天地,有时候全凭一种悟性巧合。正如捕鱼为业的武陵人缘溪行会钻进若有光的山中小口,然后发现桃花源;也正如苹果砸到牛顿的头也砸开了人类的小宇宙。你感觉好奇,才会有奇迹。
所以我的每一天都像初恋似的,过得格外认真与细心,生怕错过了哪一个或许能让我成为伟人的机遇。我一直坚持地相信生活就是一部电影,我们所见的都不会平白无故的来,又平白无故的去,换言之,存在即是有用的。就像电影里如果给了某一件物品(如玉佩、手镯等)的特写,那就一定会围绕这件物品发展出很多故事。到了生活中也处处可见,就好比我今天上午在班主任的课上睡觉,她临下课给了我一个颇为温暖慈祥又险恶犀利的眼神,这就暗示了我下午要么会被叫去谈话,要么就会写
对于电影与人生的辩证关系,我常常企图用一句话来概括,但仿佛是决然不可,可我仍然把这样的思考时不时地提在唇上,唇齿一分一合,让我在朋友圈里变得独树一帜,我自此明白:有些有道理的话,说的越模糊越有效果。记得我有一次和一个损友去看《阿凡达》,巨贵的影票让我俩当日山穷水尽,我们趁着余晖正要散落桥头,弱弱地坐在已经褪了漆、连边角都磨圆了的广场休闲椅上。忽然他用仿佛还在潘多拉星球与人类战斗的纠结表情对我说:其实这就是人与人的对抗!我觉醒了!
我对你的崇敬已经达到了理智与人性分离的高度了。你在那三个小时里把所有伪先进的思想都剔除了?你现在这么说是不是觉得你就是阿凡达?你要为自然与正义而战?我极忍笑抽的面部肌肉回问道。
没错,一切都被颠倒了,仿佛那里才是真实的世界,那里才是梦他故作回味地说完,我便觉得有些离奇,又忽然觉得非常合理,这些虽然是想象,但同时也是一种隐喻,它隐喻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任何一个群体因没有正义的举动都可能会遭到自身的背叛,总会有人作出和杰克萨利一样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背叛意味着善与爱。
这种观影的感受使我尝试在每一部影片看罢之余,再细细思考一下其中的深层次暗语,以至于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观察家,洞悉一切。然而实在的说,对待生活的`态度有时候还真应该像看电影一样,不能只顺水推舟地过,而应回味又期待地活。所以常看电影,除了眼镜越戴越厚,还真是没什么坏处。
正如前苏联戏剧理论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言:戏剧艺术的感受应该从外而内,然后从内而外地表达出来。受益于此,常常无所事事宅在家里的我,就在不断地寻求将外部的感觉转化为思考,再沉淀成内心的情感,最后才去真正表达。这有些像王阳明向内探求的心学,但也并不排斥格物致知的传统的
谈及光影的变换可以援引阿尔贝冈斯之语:构成影片的不是画面,而是画面的灵魂。同样之于人生,构成生活的不是一段又一段经历,而是在经历之中不断锤炼的灵魂,锤炼可以是来自外部的磨砺,也可以是来自自身的感悟。画面之所以有灵魂,是因为画面之中存在隐喻,使得影片文艺而富有底蕴;经历之所以锤炼灵魂,是因为经历之后体现生活的隐喻,指引人生凌风绝顶!
能够经常地获得生活的灵感实在是难能可贵,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常保持捕捉灵感的意识。于是,除却看电影,我也喜欢探索新的领域比如,我也打篮球但我也练习双截棍;我也有一本一本的漫画书可我也要围棋比赛的段位证书;我也去公园广场KTV,可我还尝试着敲敲键盘做个金牌编剧......虽然最终我也许不会成为李小龙、吴清源或是严歌苓,但这个过程让我感到快乐,就像看电影一样充实。
记得学校里每周六都会组织连场电影,我就仿佛是那个和它签了合同永远不会违约的合作者,就算是课程紧锣密鼓、作业铺天盖地的高三,我也从不错过。凭借文化课较好的基础优势,我肆无忌惮地把那些电影看了又想,想了又看。还有我每一次都会在同一地点遇到也爱看电影的前排女生,有一回我问她每次都来?
她点点头。
每部都看?
她又点点头。
可是有的电影不好看耶。
哪有完全不好看的电影呀?她明朗地一笑。
就这一句话,我对她肃然起敬,之后我看电影也不总是去挑影片的毛病,而是多多的发现其中的闪光点。我幽幽地改变着心态,那种喜悦就好像孙悟空救活了人参果树,唐三藏看到了雷音寺一般。
于是我觉得我青春的起飞阶段并不只是枯燥地挥着汗水,我还有哭笑不得,还有彻夜难眠,还有安静遐想。我回想刚刚走过的青葱岁月,就好像是靠在山旁傍在水边,一叶红蝶并没有过早地在起风时飘落了,精致得像陈逸飞的电影。那些原本支离如碎镜的求学片段,在心中经过巧妙地蒙太奇处理,忽然反射出也喷薄着绚丽的光芒。
生活,电影,其实就像拼七巧板、搭积木、转魔方一样,好多好多的瞬间,好多好多的镜头,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我们既可以平稳地叙事、冷静地讲述,去发现许鞍华的功力;也可以把岁月修缮的影影绰绰、神神秘秘,去
一、 对比:《伊利亚特》叙事方式和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
经典好莱坞的叙事系统(Classic Hollywood Narrative System),又被尼尔巴奇(Noel Burch)在《实用电影理论》(Theory of Film Practice)一书中称为“表达的程序性格式”(The Institutional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MR)。
著名电影人安德烈巴赞说:“理解影片表达什么,最好先懂得它是怎么表达的。”赫曼G温伯格则说,叙述故事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伊利亚特》是一部较为古老的西方文学经典,美国好莱坞电影则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代表之一,但是二者在叙事方面却有着某种惊人的一致性。莎士比亚说:“阳光下面无新事。”这是否又是一次对经典的回归呢?
1、在经典叙事结构中,故事中的事件是围绕着谜和解谜的基本结构来组织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意外的事件打破了虚构的业已存在的世界的平静与和谐。现在,叙事的任务就是要着手对付失衡的世界,并重新找回世界的平静与和谐。
《伊利亚特》虽然叙述的是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个片断,却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由团结到分裂,再到团结的故事,或者说是由愤怒到愤怒消解的故事。《伊》开篇,希腊联军已经和特洛伊及其盟友对峙九年,“阿尔戈斯人并不松懈,只是因为特洛亚人养精蓄锐,对于他们很少攻击,所以他们转而侵略特洛亚城附近的地区”。这是一种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但是,阿基琉斯的愤怒打破了这种平衡。状况一,希腊联军内部分裂,失去了阿基琉斯,实力的天平开始向特洛亚倾斜。失去了维持平衡的支点,特洛亚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当然不会轻易放过。状况二,为给阿基琉斯复仇机会,宙斯诱惑阿伽门农,希腊联军贸然出动,使秩序更加混乱。随后《伊》叙事的任务就是解决矛盾,使阿基琉斯回到战场,战争又回到两军对垒的正常秩序。
2、经典叙事将会采取不同的手法来解决发生的问题,重建虚构世界的秩序。但重要的是叙事的过程(从初始事件爆发到最后问题解决的一切事件)都有一定的秩序安排,故事中的事件按照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这样,叙事事件之间就有了逻辑的联系。经典叙事按照大致的线性架构逐次展开,直至到达最后那显然是理所应当的结局。
帕里斯把“给最美者”的苹果判给了爱神,这一事件引出两件大事:一,阿弗洛狄特为了实现诺言,帮助帕里斯诱拐了海伦;二、金苹果事件引起赫拉和雅典娜对特洛伊的仇恨。海伦事件是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而赫拉和雅典娜的仇恨更是时时影响着战争的发展方向。从文本来看,《伊》中,祭司事件的结果是阿基琉斯愤而退出战争;阿基琉斯的退出导致阿尔戈斯人的溃败;为了挽救同伴,阿基琉斯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替阿基琉斯出战;帕特洛克罗斯的死亡,使阿基琉斯再战赫克托尔。在《伊》中,架构起故事的线性叙事有两种,特洛伊战争的演变和神灵的行动。因果关系是整部史诗的逻辑联系。
3、经典叙事的世界由真实性,或者说是记录片风格的写实主义统领,叙事确认首先建立一个接受对象(读者或观众)理解和相信的虚构世界,真实性通过叙事事件的空间场景和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得以体现,时空的结合是经典叙事因果逻辑关系事件的实在前提。
就真实性而言,《伊》故事中,首先是大量战争场面的描写都是采用细节描写,对阵的两位英雄的动作、容貌、话语、出身等有较为具体的介绍。其二,在神仙叙事的线索中,描写饮宴场景,赫拉魅惑宙斯等,都充满了现实凡人生活的影子,给人接近日常生活的亲切感。第三,叙述语言中多采用乡间牧童似的话语,例如把涌向特洛亚城的希腊联军比喻为成熟的涌动的秋天的稻浪。
4、在经典叙事中,故事的发展靠虚构的人物个性来推动,经典叙事中的主角是一个带有性格特征、动机和欲望的丰满个性。这样一来,构成故事的连环事件就受到这个人物行动动机的控制,这个人物就成为经典叙事的“英雄”,并有他的行动来最终决定矛盾的解决,而他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取决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阿基琉斯的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正在于他的丰满个性。他勇敢善战,敢于并执着于自己的利益,即使面对的是队伍的统帅――阿伽门农。正是因为这种个性,所以当阿伽门农掠夺了他的光荣礼物时,他会愤而退出战争,甚至不顾其他阿尔戈斯人的灾难。也是因为他的高傲,阿伽门农第一次求和被拒绝。最后矛盾解决,同样是阿基琉斯的个性使然:他要为最好的朋友报仇。可见,在阿基琉斯的观念里,跟本没有忠君报效的思想,他战争是为了给自己争取荣誉,个人荣誉超过了一切。
5、最后,大团圆结局作为叙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故事叙述中扮演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大团圆结局具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循环型或封闭型故事结构(The Circular or Closed Story Form),其二是达到成功和完美的幸福结局(Achievement of Perfection or Happy Ending)。
循环型或封闭型故事结构要求叙事在最后回到它的起点。在这一结构模式的结尾,主人公将完成自己的圆型旅程回归他(她)的出发地,这一回归也许是通过影像象征或对话暗示来完成,其目的在于使故事完整。《伊》故事在老祭司的祈祷中开始,又在赫克托尔的葬礼中结束,二者都是伴随着战争的重要场合,但又确实是暂时停止战争的`较为平静和谐的场合,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回归。更深层的则是希腊联军内部由团结被破坏到重新团结的回归,即阿基琉斯由愤而退出英雄事业到回归其事业的过程。
二、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特征主要有三点:戏剧化的故事结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和连续性剪辑。
解析[戏剧冲突] :
经典好莱坞叙事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戏剧化的故事结构。
《伊利亚特》叙事的绝对“英雄”是阿基琉斯,他正是“一个带有性格特征、
动机和欲望的丰满个性”。他的愤怒导致了《伊利亚特》故事的发生,他和阿伽门农和解决定了矛盾的最终解决,正是他的鲜明的个性决定了事态的发展。而具体的戏剧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希腊联军和特洛伊之间的矛盾及双方队伍内部的矛盾斗争是史诗叙述的重要
内容。
第一卷,开篇就是希腊联军中,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的矛盾冲突;第二卷,长老议事团的计谋造成希腊联军“去与留”的矛盾;第三卷有“帕里斯和墨涅拉奥斯的对决”;第四卷,潘达罗斯引起双方队伍的激战;第九卷,阿伽门农向阿基琉斯求和遭拒,这是第一卷矛盾的直接延续;第十卷,“夜探敌营”的行为是双方的,也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第十六卷,宙斯的儿子萨尔佩冬和阿基琉斯的伴侣帕特罗克洛斯的激烈对决;第十七卷双方战士围绕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展开的争夺斗争;第二十四卷,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潜入希腊联军营地,向阿基琉斯赎取赫克托尔的尸体,孤身犯险的老王和仇恨特洛伊的希腊联军构成矛盾冲突,同时对于阿基琉斯,“还尸体”还是“抓国王”也构成了矛盾。
2、神仙也疯狂。天神之间的矛盾是《伊利亚特》叙事的另一重点。
第一卷,宙斯和赫拉出场就积怨甚深;第四卷,宙斯和赫拉的争吵引发人间的仇视,雅典娜和阿波罗正式投入战斗的双方;第五卷,爱神阿弗洛狄特、战神阿瑞斯、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都参加了战斗;第十三卷,波塞冬挑战宙斯,不顾宙斯的禁令,加入战争;第十四卷,赫拉用美色迷惑宙斯,引起宙斯的愤怒;第二十卷、二十一卷直接描写众神的战争。
3、作为两条线索的交叉,人与神的冲突也有所表现。
第二卷,宙斯用梦诱惑阿伽门农,众神之父以诡计陷害凡人,“入人于罪”,或者说是为了实现命运的安排;第三卷,爱神在战乱中,救出了帕里斯,并和海伦产生冲突;第五卷,狄奥墨得斯在雅典娜的挑唆下刺伤美神,还出言不逊;第二十一卷,“阿基琉斯力战克珊托斯河神”,凡人不但对神没有了敬畏,而且对神也拿起了武器,敢于正面对抗。
解析[类型化的人物形象]:
在戏剧化的故事情节模式确定之后,好莱坞经典叙事的人物形象构成也自然呈现类型化的倾向。根据戏剧冲突的原则,人物形象被确立为正反两个阵营,正面人物包括主人公、导师或盟友和信使,反面人物则由坏蛋和帮凶组成。在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中间往往会出现一个灰色的中间地带,那就是中间人物看门人和变色龙。(《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教程》)
《伊利亚特》特殊之处在于叙事视角的偏袒性。(《弓弦和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美]伯纳德特 著,华夏出版社)在《伊》中交战的双方没有善恶之分,只有主次之别。阿基琉斯是无可争议的主人公,他侮辱赫克托尔的尸体、他杀死无数战士,但是他的残暴源于他的愤怒,所以只能使人痛心,而不会使人憎恨;赫克托尔为了城邦,为了家人而战斗,最后面对阿基琉斯,他因为恐惧绕城而逃,这是一个人面对比他强大的对手时正常的反应,但是他敢于一个人
战斗在城门之外,而且最终,明知道被神背叛,还是要为荣誉而战,他同样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主次之别,只要体现在重点描绘希腊联军方面的英雄,而特洛伊方面的英雄相比逊色。
《伊》故事中,人物类型没有截然的“正反”之分,但是整个故事框架中,人物形象仍是以两个对立阵营的形式出现的。里面所有的人物都可以分为希腊联军和特洛亚盟军两个阵营,神亦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伊》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表明的,是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又一次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