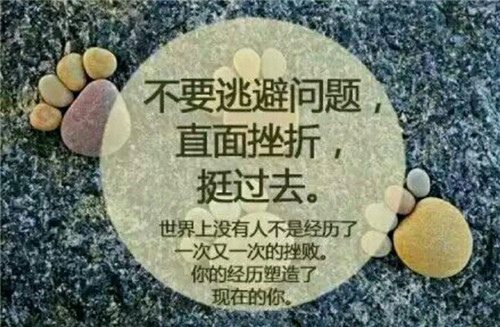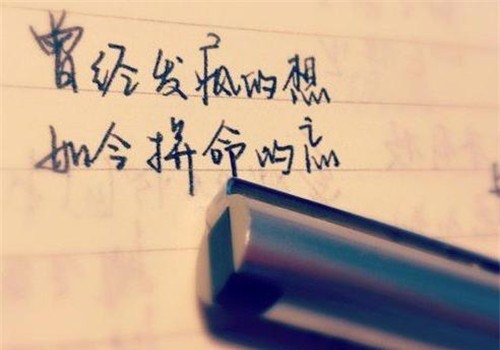
引导语:人生不需要完美,不然有什么意思,完美的想象,不完美的才是生活。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这是季羡林在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就像颁奖词中所说,季羡林对自己的定位也始终是“一介布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季老一生受人尊重,被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对此,季羡林却力辞这三顶“桂冠”:“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是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曾经说过:影响我一生的.四句话,分别是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所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也留下了很多影响我们的话:
谈人生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燥;对人可以互相谅解。
谈勤奋
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一个人干什么事都要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没有这个劲,我看是一事无成。
谈孤独
父母也好,爱人也罢,朋友同事,所有的人,他们在时,都是恩赐,是上苍给你的礼物,所以要加倍珍惜和感激;而一旦离开,也别太伤感。你要明白,离开是正常的,孤独才是生命之常态。
谈真、忍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谈关系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谈态度
世人无不想走运,而决不想倒霉。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谈恐惧
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正常的;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是英雄;不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孱头。我们都要锻炼自己,对什么事情都不要惊慌失措,而要处变不惊。
谈友情
人类是社会动物。一个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没有朋友。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如果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
谈爱情
如果一个人不想终身独身的话,他必须谈恋爱以至结婚。这是“人间正道”。但是千万别浪费过多的时间,终日卿卿我我,闹得神魂颠倒,处心积虑,不时闹点小别扭,学习不好,工作难成,最终还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觉得,两个人必须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不必过长,短则半年,多则一年。
“我的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 “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季羡林
“我数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
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摘下外界冠以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称谓,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本真面目。先生风风雨雨的近百年人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真实写照。透过老人平易近人的絮语,人们仿佛随着他翻阅人生书本中生动的一页页。
幼无大志,幸运垂青
季羡林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到了季羡林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
六岁以前,季羡林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忘了他究竟教了季羡林些什么,大概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从那时起,季羡林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季羡林在新育小学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季羡林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季羡林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季羡林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他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季羡林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不管怎样,幼无大志,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季羡林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题目是汉译英。季羡林翻出来了,结果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季羡林也并不努力,成绩属于上中水平。他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季羡林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季羡林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季羡林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羡林身上。他严而慈,对季羡林影响极大。季羡林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根据他的要求,季羡林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季羡林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现在回想起来,他今天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季羡林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季羡林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季羡林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季羡林也阅读。这些书对季羡林有什么影响,季羡林说不出,反正他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得遇良师,锋芒初露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玉先生,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对季羡林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季羡林意料,这篇作文受到老师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季羡林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季羡林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季羡林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季羡林。这当然更出季羡林意料。季羡林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季羡林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里有几位国文方面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季羡林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即普罗文学。季羡林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季羡林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 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反动派通缉,不久遇难。季羡林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随后, 接胡先生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季羡林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季羡林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给了季羡林极大的鼓励。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季羡林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
缘定清华,多面受益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季羡林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季羡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季羡林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因为,季羡林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季羡林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英文、德文、法文。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 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等等。
季羡林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授课。尽管季羡林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季羡林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季羡林只能看书,不能听和说。
所有的课程中,季羡林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的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佛经翻译文学”的旁听课。这两门课对季羡林影响至今。季羡林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顺便说一句,季羡林在大学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季羡林可万万没有想到,那几篇散文竟给带来了好处。1934年,季羡林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季羡林那几篇散文就把季羡林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季羡林可是在心里直打鼓: 季羡林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季羡林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季羡林,季羡林就敢去!季羡林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成了国文教员。季羡林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季羡林只有23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季羡林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季羡林实在是如履薄冰。
留德十载,情钟外语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季羡林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季羡林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留学生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季羡林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修了不少的课。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季羡林忍受了空前的饥饿,天上还有飞机轰炸。尽管十分怀念祖国和家庭,却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季羡林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他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岁月,最使季羡林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对于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季羡林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授的对象也几乎就是季羡林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传给季羡林。他给季羡林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等。作为吐火罗文的最高权威,Sieg 教授坚持把这门天书般的语言传授给季羡林。季羡林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季羡林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从1937年起,季羡林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该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季羡林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季羡林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季羡林在这方面的知识面。季羡林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 1945年秋冬之交,季羡林离开这里到瑞士,住了将近半年。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季羡林的留学生活, 也可以说是季羡林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季羡林35岁。
任教北大,治学半生
1946年秋天,季羡林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要感谢陈寅恪先生,是他把季羡林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也许是季羡林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季羡林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季羡林,季羡林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42年,季羡林一直没有离开过北大。期间季羡林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季羡林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季羡林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季羡林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季羡林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也都属于鲁迅所言的“勤捉”之类。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而且立竿见影。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然而又一点也没有八十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
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我的父母都没有活过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计划是活到五十。这样已经超过了父母,很不错了。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我活到了五十岁。那里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流年不利,颇挨了一阵子饿。但是,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正在德国,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像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我们那一点灾害,同德国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我从而顺利地渡过了那一场灾害,而且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于不知不觉中冲破了我原定的年龄计划,渡过了五十岁大关。
五十一过,又仿佛一场春梦似地,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蹰。其间跨越了一个十年内乱。我当然是在劫难逃,被送进牛棚。我现在不知道应当感谢哪一路神灵:佛祖、上帝、安拉;由于一个万分偶然的机缘,我没有走上绝路,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不但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反而时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来了,也许还是有点好处的。我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原因并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和时间。在浩劫期间,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来不打不骂了,我却变成了“不可接触者”。在很长时间内,我被分配挖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然而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
又仿佛是一场缥缈的春梦,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这个在寿命上胸无大志的人,偶尔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况:手拄拐杖,白须飘胸,步履维艰,老态龙钟。自谓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这个年龄了。今天是新年元旦,从夜里零时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青霭入看无”,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周围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
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我相信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话:“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梦着楼前的白杨重新长出了浓密的绿叶;我梦着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绿的大叶子;我梦着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八十”这个数目字竟有这样大的威力,一种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经八十岁了!”我吃惊地暗自思忖。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又回头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的一团,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长。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罢。
而回头看呢,则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回头看既然这样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我上面已经说到,向前看,路不是很长,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现在正像鲁迅的散文诗《过客》中的一个过客。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终于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讨了点水喝。老翁看他已经疲惫不堪,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况且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边,西边是什么地方呢?老人说:“前面,是坟。”小女孩说:“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我理解这个过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个过客,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声音催着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到西边的坟那里,这是一切人的归宿。我记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也讲了这个意思。我并不怕坟,只是在走了这么长的路以后,我真想停下来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自我安慰的是,我同那个老翁还不一样,有的地方颇像那个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坟,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蔷薇。
我面前还有多少路呢?我说不出,也没有仔细想过。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没有大志的人,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大志了。
我从前对穷通寿夭也是颇有一些想法的。十年内乱以后,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他的一首诗,我很欣赏: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决不想成为行尸走肉。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
1991年1月1日
读季羡林八十述怀有感
近来读到一本好书《人一生要读的经典大全集》,其中对著名大师季羡林①的`“八十述怀”一文,很有感触。“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得年龄在内。我的父母都没能活过五十”。“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我活到了五十岁”。文章一开头就充满了一个老人对岁月匆匆,光阴似箭的感叹。继而回忆了他五十岁时 ,经历了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挨过一阵子饿,特别是二十多岁在德国留学期间,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生存的艰难,经受了至今都难于想像的饥饿的考验,精神面貌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
“五十一过只彷佛一场春梦似地,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蹰。期间跨越了一个十年内乱。我当然是在劫难逃,被送进牛棚”。“由于一个万分偶然的机会,我没有走上绝路,活了下来”。“活下来,也许还是有点好处的。这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原因并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和时间。在浩劫期间,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来不打不骂了,我变成了‘不可接触者’。在很长时间内,我被分配挖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说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然而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人”。这一段叙述一气呵成,感人至深,是全文的一个高潮所在。季羡林大师在人生的极端逆境中不甘沉沦,不自暴自弃,把十年内乱的“噩梦”转变为“春梦”,利用充裕的时间,刻苦做学问,利用自己留德时通晓的东亚古文字特长,用很少有人懂得的印度古语梵文,翻译了印度史诗巨著,成就了一代大师的辉煌事业和千古英名。
“又仿佛是一场缥缈的春梦,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这个在寿命上胸无大志的人,偶尔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况:手拄拐杖,白须飘胸,步履维艰,老态龙钟。自谓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所以想的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这个年龄了”。“然而,我看不到什么老景。自己的身体,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周围的环境,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这里跨越时空的想象,与一般老人的形象作对比,说明八十岁的季老,心态平和,宠辱不惊,感觉身体还象年轻人一样很健康。
“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我相信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话: ‘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梦着楼前的白杨重新长出了浓密的绿叶;我梦着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绿的大叶子,我梦着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季老已经感觉到高龄带来的今后生活的压力,却并不悲观失望。在文中几次交替使用“宛如一场春梦”似的等类似的句子,使这篇文章充满青春的气息,并且使全文紧密相扣,错落有致。表明了他年轻的心态,乐观的态度,过人的精力。
接着他说道,“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八十’这个数目字竟有这样大的威力,一种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经八十岁了!”。“我吃惊地暗自思忖。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又回头看一看。向前看,灰濛濛的一团,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长,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罢”。“而回头看呢,则在灰濛濛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步地走过来的”。人到八十的时候,一种自然的力量和神秘威力,逼迫他思考总结,回顾了过去。他看到了他的出生地山东清平县的官庄,看到了母亲等亲人,看到了求学路上,泉城的大明湖、水木清华,德国小城哥廷根及母亲似度女房东、祖父似的老教授,又看到了从不远万里折回到神州大地,回国后的北大红楼燕园,还看到了人生低谷时的牛棚和牢头禁子的那一副面孔。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直入;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久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这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回忆过去,道路是漫长曲折的,经历是坎坷沉重的。即使是数十载戎马磨砺,功成名就,桂冠无数,也要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前途依然是光明的。季老对过去的人生之路作了高度的哲理性、艺术性的概括,这是本文的精华所在。
“回头看,既然这样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尽管向前看,路不是很长,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 ”峰回路转,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时间仿佛也不多,季老固然觉得惋惜、伤感,但并不消沉。对于未来,季老化用鲁迅散文诗《过客》一文中的内容,说自己“我理解这个过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个过客”, “我并不怕坟,只是在走了这么长的路后,我真想停下来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自我安慰的是,我同那个老翁还不一样,有的地方颇像那个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坟,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蔷薇。”表明了自己一个八十岁老人的豁达的生死观,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勤思进取的学术观。真挚地表达了他对大自然的憧憬,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赞美,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充分肯定:百年以后,自己绝不会寂寞的。
接近文章的末尾,季老又一次谦虚的说道:“我前面还有多少路呢?我说不出,也没有仔细想过。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与米?相期以茶’。 ‘米’是八十八岁, ‘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 ‘相期以米’。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没有大志的人,我觉得这已经是大志了”。表达了季老淡泊人生的思想态度,承认生命的客观规律性。文章开头也讲到的“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这正是中国人对待事物的精髓之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包含了很深刻的哲学思想。绝不主观臆测地去追求什么长寿、超自然,尽人事而顺天意。这里季老还欣赏引用了陶渊明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思想,淡泊明志,豁达开朗。
最后,季老说 ,“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决不想成为行尸走肉。我知道,未来的路也绝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表明了他乐观面对未来,只要身体允许,决心活到老学到老,笔耕不缀,做一个对别人有益的人。这恰恰也是季老既能成就事业,又能长寿健康的人生感言和经验 。
细细品读完季老这篇写于1991年1月1日的“八十述怀”全文,一个平和、豁达而又坚强、自信的学者,一个具有高尚思想品德的老师,一个有些衰老还很健康的老人,已经跃然纸外了。和大师对话,总是感到那么地亲切自然,令人振奋,又像是在交心交底,促膝而谈;总是感到心灵的净化,精神境界的提升,满口余香,如沐春风;总是感到毫不隐讳,无拘无束,谦虚和蔼,实事求是的大家风范。我坚信,季老期望的将来在他筑坟的那边,永远有野百合、野蔷薇的摇曳飘香,自然流芳,一定会实现。季羡林曾被授予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颁奖辞: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季羡林活到了高寿,98岁(1911.8——2009.7),比他在“八十述怀”中说的“相期以米”,无意中整整多了十岁。他是真正的一代学术大师,将永远活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垂不朽。
①季羡林,男,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曾撰文三辞桂冠。2012年 8月2日,季羡林先生纪念园奠基仪式在泰安长安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