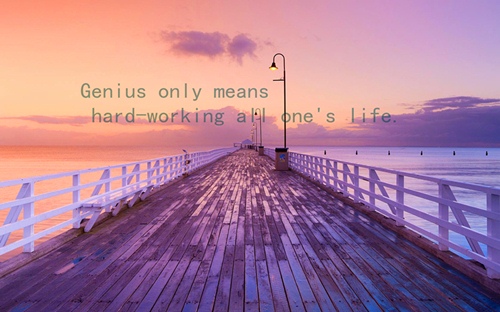家乡的名人作文(1)
说起名人,同学们一定会想到那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或是作家、画家、企业家、科学家,还有歌星、影星、球星等等。其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今天我要说的是我的奶奶。
奶奶六十来岁,个子不算高。脸上布满了皱纹,一笑起来皱纹就更深了。虽然奶奶长得并不出众,可她扎出的扫把却个个漂亮得很。
奶奶每年都要种扫把苗子用来扎扫把,因为每年总是有一些人找奶奶帮他(她)们扎。还有一些人也想学,奶奶就会毫不吝啬地教她,直到把她教会为止。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你奶奶这手艺是跟谁学的?”其实,奶奶的这个手艺并不是跟谁学的,而是她看别人扎,她自己也很好奇,回家自学的。后来慢慢就学会了。
其实,做扫把也不是很难。先把扫把苗子晒干,种子去掉,再把它的外皮剥掉,用锤子把杆子锤开,然后用绳子把它扎成扫把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一点,一定要扎紧,否则很容易散掉。
有一次,我跟奶奶在聊天。我突发奇想,问:“奶奶,你刚开始学扎扫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呀?”奶奶说:“有啊。”我说:“那你给我说说吧。”奶奶说:“好。有一天,我正在扎扫把,突然,用东西把杆子梳开的时候,那东西上面有一颗钉子松掉了。我一梳,把手都割破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不学了?”奶奶说:“这点小困难算什么?我跟本就没有想过。”我说:“哦。”突然之间,我真有些佩服奶奶呢。
这就是我的家乡的“名人”——奶奶。
家乡的名人作文(2)
说起名人,大家一定会想到那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或者作家、画家,企业家、科学家,还有歌星、影星等等。其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的家乡就有这样一位名人,她虽然不像那些大红大紫、家喻户晓的名人有名气,她却是我心中的偶像。她就是我的阿姨—许红莲。
阿姨是一位有名的“数学家”。阿姨从小就勤奋苦学,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她永不退缩,脑袋里装的几乎是知识,没有一点杂丝。所以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去请教阿姨。有一次,我有一道数学思考题不会做,就去请教阿姨。阿姨一看,在草稿纸上“挥”了几下,就大功告成了,然后把步骤慢慢地讲给我听,直到我听懂为止。我心想:阿姨真是“神机妙算”,只可惜没去当老师,却成了我的“家教”老师。
从那以后,我就很佩服阿姨,佩服她的“神机妙算”,佩服她的刻苦学习,佩服她讲解时的娓娓动听。
我应该学习阿姨坚持不懈的精神,经历每一件事都要做好。记得阿姨曾经说过:每一个人做一件事,就要坚持不懈,永不放弃。
家乡的名人作文(3)
我们村有一位“名人”,他就是我们村的“养猪大户”——李大叔。
李大叔养的猪个个肥头大耳,胖墩墩的,足有百十来斤重,活像一个个大肉球。
李大叔养猪十分有
每年年底,李大叔便把所有的大猪卖掉,留下小猪仔,让那些小猪仔长大后再卖。李大叔一年就因养猪就赚了七、八万元钱,没过几年,李大叔便发家致富了。
村里的人看到李大叔养猪能发家致富。便去请教李大叔,李大叔毫不犹豫地对大伙说:“只要对猪有无微不至的关照,那么猪也不会亏待我们的。”大伙听了,都知道了自己养猪不能发家致富的原因:没有给猪好吃的,没有为猪看病……现在,我们村里的人都改正了养猪的方法,全都发财了,现在,大家都感谢李大叔的提醒,让我们村的人都发家致富了,过上了小康生活。
我非常敬佩李大叔。
家乡的名人作文(4)
我家乡的名人有很多,但是,令我最最钦佩的.还是我们教英语的孟老师。
孟老师是教育局英教办公室的主任,也是我们补课的老师。孟老师说起英语来如关不住的水龙头,似乎怎么也说不完。“叮铃铃”,上课铃响了,我们陆陆续续回到了教室。孟老师来到了教室,先把我们的名字点了,然后进入了美妙的课堂!首先,孟老师先让我们不认识的单词用横线划出来,然后老师一一把不认识的单词用音标写出来让我们拼,“拦路虎”就这样被我们清除掉了。下来,就进入了学课文的阶段了,学完课文,就下课了。第二节课时,我们先把上一会学来的音标复习一遍,在学四个音标。音标学完后就开始对练习册。
这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名人——孟老师。
家乡的名人作文(5)
在我的家乡有一位捏泥人的老人,他就是——张爷爷。
他一身陈旧的中山装,一顶老式的鸭舌帽,一张黝黑而又饱经风霜的脸。
张爷爷经常坐在村子里的大柳树下,他的面前摆着一个大木箱子,上面摆着各色各样的泥人,什么“孙悟空”“机器猫”“樱桃小丸子”……个个活灵活现,,
在我观看“画眉”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一个“猪八戒”的半成品已经展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张爷爷一手举着“猪八戒”,一手托着下巴,似乎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儿,老人拿出一些红色的泥和一些黑色的泥,左揉右捏,就变成了一瓣“西瓜”,他又从箱子里取出一些黑色的泥,小心的给“西瓜”装上了瓜子,你别说,简直像极了。接着老人把精心设计的一瓣“西瓜”放在了“猪八戒”的手里,哈,“猪八戒吃西瓜”终于完成了,你瞧“猪八戒”那贪婪的馋样儿表现的淋沥尽致。围观的人不断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宝剑锋从墨砺出,梅华香从苦寒来”,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泥人背身后的故事呢?
一致是强有力的,而纷争易于被征服。 —— 《伊索寓言》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管子·牧民》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 陈辉
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应表现在漂亮的话上,而应该表现在为祖国谋福利的行动上。 —— 杜勃罗留波夫
资本主义故意jiaoyu人们彼此敌对,它害怕劳动者的团结。但是我们的党却jiaoyu人有深厚的的同志爱和友谊。人的巨大精神力量就在这里——-觉得自己是在友好的集体里面。 —— 《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因为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之中, 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 《我是匈牙利人》《裴多菲诗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唐.贺知章<<回乡偶书>>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谁若认为自己是圣人,是埋没了的天才,谁若与集体脱离,谁的命运就要悲哀。集体什么时候都能提高你,并且使你两脚站得稳。 —— 《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顾炎武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zg人才有真进步。 —— 《鲁迅全集》
位卑未敢忘忧国。 —— 陆游
我们法兰人,当国家遭到奴役的时候,是无权离开自己的祖国的。 —— 居里夫人
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 彭德怀
我无论做什么,始终在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我的话,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 —— 《巴甫罗夫选集》
我愿用我作部的生命,从事研究科学,来贡献给生育我栽培我的祖国和人民。 —— 巴甫罗夫
我赞美目前的.祖国,更要三倍地赞美它的将来。 — 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诗选》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 —— 马蒂
要永远觉得祖国的土地是稳固地在你的脚下,要与集体一起生活,要记住,是集体jiaoyu了你。哪一天你若和集体脱离,那便是末路的开始。 —— 《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
一般就在部分之中;谁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就不属于人类。 —— 别林斯基:《威克裴牧师传》
故乡的河流,静静地拥有她岁月的安谧,河边上的小林子,安稳地望着对面的小河。关于家乡的散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约会乡愁》
用情去感知这个世界,用爱去融入这个红尘……
--题记
路上的行人,渐渐稀少;路上的车子,莫名的拥挤。都市的霓虹灯,依然闪烁,只是跳跃的影子,减少了很多,很多。尽管,夜仍然是夜,酒仍然是酒。
身居繁华的喧嚣都市,心却奢望宁静如水的寂然小村。群山,青草,绵羊,牧童,还有绵延的云,朦胧的雾,更有生生不息的情,暖至灵魂的爱……
劳累了一天,紧绷的神经,终是要放松。或者,用情抚摸;或者,用爱温润;或者,用酒精麻醉;或者,用往事穿插……
有时,狂躁的自己,甚至用暴走释放心情的无助,谋求灵魂的归宿。当精疲力尽的身体,躺在草坪上,望着繁星闪烁的夜空,心总会莫名的疼:远方,应该也是星月灿烂吧!
是,夜?漆黑了谁的心,又敲碎了谁的梦幻?
只是,有些路,总要一个人走。或者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暗伤,不见太阳,不经雨露。只不过,这伤,或深,或浅,而已。
都说世相迷离,我们常在如烟世海中丢失了自己,而凡尘缭绕的烟火又总是呛得你我不敢自由呼吸。千帆过尽,回首往事,那份纯净的梦想早已渐行渐远,如今岁月留下的,只是满目荒凉。
林徽因如是感慨,是那个年代的因果吗?可是,一唱雄鸡天下白,岁月悠然走了将近一个世纪,红尘依然……
陌上花开,风在呢喃。谁,陪你聆听季节的呼唤?谁,陪你仰望星空的转换?
一个人,一杯酒,饮尽红尘的冷暖;一个人,一杯茶,品味岁月的酸甜;一个人,一本书,阅览浮世的清欢。一切,都只是云烟过眼,终会如风。
夜,深了,冬夜,更冷了。
独自坐在吧台上,一杯酒水,静静地陪着,说不上寂寞,也说不上狂欢后的孤独,就那样陪着夜,陪着这个城市,将故乡抛弃。
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你看,移动的舞步,闪烁的灯光,靓丽的身影,流淌的音乐,无不展现着迷人的风景。间或,激情的接吻;或者,浪漫的红玫;还有,高贵的紫罗兰……夜,总是撩人的。
谁说,熟悉的地方只有错过的人?你看,流动的大街小巷,匆匆的行人,遇见就是缘分,一个微笑,一次牵手,或许都会温暖异乡的寂寞。快速的列车,擦肩的你我,一声你好也会化解彼此的陌生。
是谁,在等你缓缓归?
那片荒芜的土地,那条曲折的泥路,那叶落寞的小船,那条清澈的淮河,还有儿时嘻戏的时光:田野中挖野菜的春日暖阳,麦田里捡拾麦穗的炎炎夏日,沙滩上流连忘返的秋水清凉,雪地里堆垒狮子的欢歌笑语。还有,倚门微笑的亲人……
是谁,在轻轻召唤:归来吧,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你,终究是这个城市的过客,也是这个红尘的过客。有些人,有些事,亦是如此,无需刻意,只要心安就好。
人说,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乡。其实,每个人都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安稳。既然我们都是过客,就该携一颗从容淡泊的心,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风尘起落的人间。
我们总是在埋怨着什么,在索取着什么,却总会忘记我们付出了多少。不是吗?
当我们埋怨城市的地铁,多么多么拥挤的时候,而我们的家乡却还是泥泞满地;当我们向这个城市索取更多的报酬时,可曾想过我们为这个城市增砖添瓦?当我们向父母羡慕别人的豪车名宅时,我们可曾理解父母的艰辛?
是的,都市的繁华也是多少人努力的结晶,相反我们又为自己的故土做了什么呢,或许最清楚的还是自己。
诚然,这个社会不乏贪婪者,利用手中仅有的一点点权势,坑民利己,践踏着法律的尊严,或许可以蒙得了一时,但他可以肆虐一世吗?
故乡,在呼唤;乡愁,在弥漫。我们,都在逃离着故土,却又在渴望着回归,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心理,谁又知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愫?
雪小禅说,每一个在乡村生活过的人都是幸福的,在漫长的人生中,那是丰沛厚实的滋养。
岁月,悄然从指尖划过,那没有结局的曾经,是碎了一地的梦。蓦然回首,已是无言,这满地碎片,叫我们如何拾起?
有些感受,只有凭着记忆慢慢寻找最初的味道,回忆已经很拥挤,却不见过路人,皆是匆匆过客。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只要,我们可以平静的呼吸,仔细的聆听,还有微笑着生活,足矣。
其实,有些东西一直就在,只是你以为它已经走远罢了。
一段路,一个人可以走,两个人可以走,多人可以陪你走。只是,沿途的风景,路过的行人,期许的情感,不同而已。这一程,或短,或长,有喜,有愁,有苦,有甜,享受获取是的欣喜,忧伤失去时的悲悯。若可以,不悲不喜,多好!
尽管世事繁杂,心依然,情怀依然;尽管颠簸流离,脚步依然,追求依然;尽管岁月沧桑,世界依然,生命依然。
我们一直,延续着生命,剔除着丑陋,传承着美好,这个世界何处不是春暖花开呢!于是,记忆的碎片,在一点一点的交织,一个人的浮世清欢,一个人的细水长流,都镌刻在岁月的风铃上,谱写一曲悦耳的音乐。
于是,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你是我的故事。
张抗抗《故乡在远方》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
几十年来,我漂泊不定、浪迹天涯。我走过田野、穿过城市,我到过许多许多地方。
我从哪里来?哪儿是我的故园我的家乡?
我不知道。
19岁那年我离开了杭州城。水光潋滟、山色空濛的西子湖畔是我的出生地。离杭州100里水路的江南小镇洛舍是我的外婆家。
然而,我只是杭州的一个过客,我的祖籍在广东新会。我长到30岁时,才同我的父母一起回过广东老家。老家有翡翠般的小河、密密的甘蔗林和神秘幽静的榕树岛,夕阳西下时,我看见大翅长脖的白鹳灰鹳急急盘旋回巢,巨大的榕树林上空遮天蔽日,鸟声盈盈。那就是闻名于世的小鸟天堂。新会县世为葵乡,小河碧绿的水波上,一串串细长的小船满载清香弥漫的葵叶,沉甸甸贴水而行,悠悠远去……
但老家于我,却已无故园的感觉。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也并不真正认识一个人。我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地道的家乡方言。我和我早年离家的父亲,犹如被放逐的弃儿,在陌生的乡音里,茫然寻找辨别着这块土地残留给自己的根性。
梦中常常出现的是江南的荷池莲塘,春天嫩绿的桑树地里透紫酸甜的桑椹儿,秋天金黄璀璨的柚子,冬天过年时挂满厅堂的酱肉粽子、鱼干,还有一锅喷香喷香的煮芋艿……
暑假寒假,坐小火轮去洛舍镇外婆家。镇东头有一座大石桥,夏天时许多光屁股的孩子从桥墩上往河里跳水,那小河连着烟波浩淼的洛舍洋,我曾经在桥下淘米,竹编的淘箩湿淋淋从水里拎起,珍珠般的白米上扑扑蹦跳着一条小鱼儿……
而外婆早已过世了。外婆走时就带走了故乡。其实外婆外公也不是地道的浙江人氏。听说外婆的祖上是江苏丹阳人,不知何年移来德清洛舍;又听说洛舍其名是早年此地曾有一支移民来自洛阳,洛阳人之舍,谓之洛舍。由此看来,外婆外公的祖籍也难以考证,我魂牵梦系的江南小镇,又何为我的故乡?
所以对于我从小出生长大的杭州城,便有了一种隐隐的隔膜和猜疑。自然,我喜欢西湖的柔和淡泊,喜欢植物园的绿草地和春天时香得醉人的含笑花,喜欢冬天时满山的翠竹和苍郁的香樟树……但它们只是我摇篮上的饰带和点缀,我欣赏它们赞美它们但它们不属于我。每次我回杭州探望父母,在嘈杂喧闹的街巷里,自己身上那种从遥远的异地带来的“生人味”,总使我觉得同这里的温馨和湿润格格不入……
我究竟来自何方?
更多的时候,我会凝神默想着那遥远的冰雪之地。想起笼罩在雾霭中的幽蓝色的小兴安岭群山。踏着没膝深的雪地进山去,灌木林里尚未封冻的山泉一路叮咚欢歌,偶有暖泉顺坡溢流,便把低洼地的塔头墩子水晶一般封存,可窥见冰层下碧玉般的青草。山里无风的日子,静谧的柞树林中轻轻慢慢地飘着小清雪,落在头巾上,不化,一会儿就亮晶晶地披了一肩,是雪女王送你的礼物。若闭上眼睛,能听见雪花亲吻着树叶的声音。那是我21岁的生命中,第一次发现原来落雪有声,如桑蚕啜叶,婴童吮乳,声声有情。
那时住帐篷,炉筒一夜夜燃着粗壮的大木棒,隆隆如森林火车如林场的牵引拖拉机轰响。时时还夹着山脚下传来的咔咔冰崩声……山林里的早晨宁静而妩媚,坡上的林梢一抹玫瑰红,淡紫色的炊烟缠绵缭绕,门前的白雪地上,又印上了夜里悄悄来过的不知名的小动物一条条丝带般的脚印儿,细细辨认,如梅花如柳梢亦如一个个问号,清晰又杂乱地蜿蜒于雪原,消失于密林深处……
那些神秘的森林居民给予我无比的亲切感,曾使我觉得自己也是否应该从此留在这里。
小小的脚印沉浮于无边的雪野之上,恰如我们飘泊动荡的青春年华。
我19岁便离开了我的出生地杭州城,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
那时我曾日夜思念我的西湖,我的故园在温暖的南方。
但现在我知道,我已没有了故乡。我们总是在走,一边走一边播撒着全世界都能生长的种子。我们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既来则定、四海为家。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流浪移民。也许我走过了太多的地方,我已有了太多的第二故乡。
然而在城市闷热窒息的夏日里,我仍时时想起北方的原野,那融进了我们青春血汗的土地。那里的一切粗犷而质朴。20年的日月就把我这样一个纤弱的江南女子,磨砺得柔韧而坚实起来。以后的日子,我也许还会继续流浪,在这极大又极小的世界上,寻觅着、创造着自己精神的家园。
《长治马路宽》
“长治马路宽,女人的裤脚宽……一共有三宽,第三宽记不清了,”还没望见长治的城墙,一位同行者就对我们说了。第三宽究竟是什么,我到城里就问过几次,说者不一,按下不表。女人的裤脚在冬天都扎上了带子,看不出宽得怎样了不得。马路倒确乎宽。从西门一进城,一见面前展出去的三株两株大树,三所两所商店的楼房峙立在两旁,由大车道夹着的大街,同伴中就有人说:“到了北平的西直门大街了。”
长治城也确乎不小,周围二十里,其大,在华北目前在我们这里的城市怕算得上第一了。城内并立在一起的钟鼓楼,上面钉着“风驰”、“云动”两块匾额,传说楼顶与伏在东边的太行山顶—样高。门里是地方法院,从前是府衙门。府衙门背后有“唐玄宗为潞州别驾时所建的德风亭故址。”今年春天日本一零八师团长下元在这里住过一个时期,最近八路军朱总司令也就在同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天。
府衙门前面的石板底下传说还埋着一位将军的盔甲。这位将军在金兵破城的时候,自刎而死,尸立不倒。一直等金兀术来拜了三拜。传说的故事是发生在四五百年前。在四五百年后,在1938年2月27日,长治城里又自杀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位四十七军的`旅长李克沅。从东阳关进来的敌军大部队已经到了城下,旅长带了一营兵在城里死守。北城的门楼被大炮打穿了,城破了,完了吗?不,还有巷战。兵士在被解决以前,把枪枝毁了,或投到井里。一场壮烈的战斗,博得了长治一带老百姓简单而可贵的一声:“四川军打得好。”长治老百姓异口同声的说出这一句话也算得不容易吧。要知道长治第一次失陷中老百姓被敌兵杀死了多少──三千!这三千人本来也有脚可走,就因为川军誓与城偕亡,封了城门,才没有出去。敌兵进来了以后,手指按着枪上的机关,“看见狗不顺眼就打狗,看见人不顺眼就打人,”一个理发匠对我说。城里老百姓当然还不止三千。其余的都在耶稣堂和天主堂里得了两个月的庇护。提起这件事情来,大家都不说一句怨言,却说了“四川军打得好”。
宋朝那位守城将军的儿子就是被金兀术养大了却起来抗金的《说岳传》的英雄陆文龙。现在那些四川将士的儿子是远在我们总后方的四川,当然还不会给敌人带去训练,可是也当然熟悉《说岳传》里的故事,多数正预备随一股向外的潮流而涌到前方来,也许一部分已经涌到前方来了,以后当然还要源源不绝的涌到前方来呢。
至于这里长治的老百姓呢,他们干脆把城墙拆了。
这里的房子倒没有什么大损毁,虽然老百姓在敌军退走以后,回到家里看见可以拿走的东西都拿光了。“连我们这里榻上铺的毡子都给拿走了,”一个澡堂的伙计还在埋怨着。澡堂外边一间房子里也许本来就没有煤气灯,他也把没有的原因归之于敌人的破坏。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可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当然得由敌人负责,老百姓反正已经把侵略者认定是坏蛋了。敌兵退走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件照例做的工作却没有做:没有烧房子。这里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被粉碎了。八路军和决死队已经兵临城下。烧房子得冒烟冒火焰,他们就暴露了退却的征象,会招致被追击的危险。下元师团长也并没有把地方法院的沙发搬走,反而把新加在窗口的细铁丝网留下来了。他溜走的时候听说是坐了飞机。
长治马路宽。街道上走来了许多穿灰色和黄绿色军装的年轻人。在北平,在上海分手的又在这里街上拉了手,带了意外的欢欣,相互看看身上穿的军衣。原先不认识的也总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你们从前不认识吗?”“哎……”被问者迟疑了。“他跟某某人很熟。”噢,我们好象见过面。”这么宽的大路展开在他们面前,等着他们走。对于他们只要感觉兴趣,就无路不可以走,只要走下去就无路不容易通。你没有走过吧,一边走一边学习下去就行了。在这里我遇见了杭州梁氏三妹弟。他们中姐姐在决死三纵队的军政干部学校当指导员,正预备当县长;妹妹也在深山里熬炼过,现在是一个记者;弟弟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里出来了,正要到河北打游击。
长治的三宝在街头重新露面了:潞酒、驴肉、小火烧。在华北广大的非敌区号称第一的长春园饭馆里又响出了铲刀敲锅子的声音。如今正是冬天,价廉的皮货站岗到大街两旁的铺门前。五毛钱一双的羊皮手套游动在街头预备温暖多少出门人的手指。南门外经常聚着许多挑担子的小贩,陈列了许多从铁路线的城市里运来的日本货。可是大多是我们需要的物品,煤油、洋烛、火柴、电池、油印机……
大街的中心搭起了戏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出来看本地戏。中国人容易抱太平观念,实在也是因为我们太爱和平的缘故。可是火星剧团也在这个台上演了抗战戏。戏台正中的上方横挂着一幅白布,上面是广告,简简单单的写着“请看战斗日报。”
观众背后的一条巷口也确乎有人看贴在街上的当天的《战斗日报》。
巷内转弯处就是战斗日报社。工人分四班不分昼夜的在那里操纵着六架石印机。
全社最初只有半块石头,以前则没有石头,因为报用油印,由现任社长的秦春风担任收电、撰稿、编辑,由另一人担任蜡纸,印刷,发行。那是已经在敌人退出去以后了。在敌人来以前,全城更只有一种由商人把无线电广播的新闻抄在纸上卖钱的东西。再以前,在战前,则类似这一套的玩意儿都没有了。现在全社工作的有五十人。报已扩充到八开式的四版,有社论,有战讯,有国外要闻,有地方通讯,有副刊。管理部的墙壁上挂了五张统计表,统计改用石印后,七月起至十一月止五个月内每日的开支。中间一张总表,两边四张统计印刷费、邮寄费、杂费、生活费,每一张表上耸立着以六十度斜势,一支高过一支的五支黑柱。报的销路已有三千,每份报的读者当然还不止三十个。地域当然限于晋东南。发行部的墙上贴了少数定阅单位的读者的地址与姓名。屯留一县中我看到了有这样不同的读者:
李高村转×宋村革命室
崔留村孙轼
郭村杨德堂
路村转栗村段权中
军电局赵慎斋
丰仪镇村箱柜交冯作新
新民村基督临时安息会鹿慧生
走到报社的民族革命室,你就仿佛进了缩小的晋东南,十几张的县图底下挂着三十多种报。这里现在已经办到每县至少有一种报了。它们中有油印的,有石印的,有一种用铅印的,就是《中国人报》,间日刊,已经发行了几个月,每期销一万五千份。
用石印翻版的《论持久战》,《抗战游击战的一般问题》,《人类的故事》,也到处被抢着看。成立不久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社长走在街时常被青年拉住了问他们又出了什么新书。出版社也就不息的翻印着,编印着种种小册子。他们编了一部小学战时读本,预备印八万册。他们知道抗战建国的大工程不能搁在空洞的基础上。
所以牺牲救国同盟会上党中心区办事处的王兴让同志,在和我们用左手(因为他断了右臂)握了手,和我们讲了多少年轻人都做了县长了,多少村子已经有了民选村长了,多少剧团已经到处演出了,多少自卫队甚至连回民义勇队已经组织起来了,多少救国会已经成立了以后,也要严肃的加上一句说:“现在这里什么都有了个框子,就等待充实。”
山西第五行政区戎胜伍专员的结论则是:“别处怕民众起来,我们这里就怕民众不起来。”
戎专员也不必怕,1938年12月l1日,就有陵川民众代表五十余到他面前来请愿撤换他们的县长师人风。民众的沉痛呼声把老实的戎专员感动得红了眼睛。“你们的痛苦我都知道,”他说,一边伸出了手,“看,我的也是农民的手呀。”
请愿的代表大多是农民。留在长治静候消息的三个代表(其中一个已经长了白胡子)就住在第五行政区农民救国会里。农民救国会里经常住五个常务委员。他们是从五个县的乡下来的道地庄稼人。武装部主任,从潞城来的,穿着黄铜葡萄式扣子斜襟的黑布棉袄而照军装规矩的束了一根皮带。他只在襄垣受过一星期的训练。到这里就什么都办得有条理了。另一个农民,担任秘书的,在12月20日第五行政区工人救国会成立会上,虽然是怯生生的,毕竟上台致词了。
参加这个成立会的各县工人救国会代表一共到了二百多人,其中十分之一光着头。十分之二用毛巾包头,十分之五戴瓜皮小帽,十分之一戴皮帽,十分之一戴军帽。可是一听说唱歌,老老少少,毫不忸怩,“工农商学兵……”大家合上来唱了。
长治县妇女救国会办事处的桌子上搁着黑布和针线,因为他们正在发动会员给青年救国会做二百双鞋子。
同一院子的长治儿童救国会的房间里则挂着几支电棒,一看就令人想起那些小英雄的光芒与威棱,两个十五岁的乡下孩子,一胖一瘦,都是委员了。胖的指瘦的对我们说:“他管组织部。”他自己呢?“锄奸部,”他回答。听到说“锄奸”,我们就立刻想起当地报纸上每隔若干日总可以读到的各地儿童团抓住汉奸的新闻。提起这些事来,锄奸部主任淡淡的解释了:“都是些小汉奸”。“都是和你一样小吗?”我们打趣说。“并不是人小呀,”他只微微的一笑。他们大多是下毒药的,贩白面金丹的。儿童团查路条最认真。为不给看路条,长子县儿童团扣过县长,陵川县儿童团扣过洋教士,平顺龙镇的儿童团中把自己的舅父都扣了。从他们充满了幼稚的字迹的“工作报告簿”上,我们可以随便翻出几条来看看他们办起事来那副认真的面孔:
四区报告,韩村村副不负责。须村儿童放哨不确实,教员不负责,自卫队黑夜不放哨,一个人借了一个通行证。南和没有学生放哨。
二区报告,苏店宣传队成立,每星期一下;侦察队成立,每星期上早操。晋寺宣传队成立,每半月宣传一回;募捐队已经成立,没有笔墨。
长治马路宽。长治城大,空地多,于是大家也就感到一点“不满”──不是“不满意”,而是“不满足”。精神上和实际上的空间老是填不满,而时间永远是那么短,尤其在目前,在冬天,一做工作,天就黑了。于是煤油灯,麻油灯,洋蜡都起来尽它们所能尽的绵力。民族革命中学的大礼堂里,经常有校外人来用五十张或八十张课桌,十二支或二十支洋蜡把两三个或五六个从别处到长治来的客人包围在核心,向他们发出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由他们回答──这叫做“座谈会”。座谈会很容易一下子就开到第一批洋蜡点完了,第二批洋蜡眼看又只剩一个头。
1938年12月13日,在民族革命中学的民族革命室里又开了一个特别长,意味也特别长的座谈会:士绅座谈会。
八路军朱总司令是座谈会中被包围的中心人物。他还是第—次到长治,在三天的滞留中,马不停蹄的到处走,带了今春府城战斗中亲自带一连人上第一线作战的作风,亲自出马干民众运动的工作,到处演讲,谈话。
座谈会的士绅中首先站起来说话的是一个穿黑马褂的前山西高等法院院长。他一边说一边微伛着上身,用右手在洋蜡上空绕了又绕。他是讲的战略:要保卫山西,得在河北打击敌人。不错。总司令只是和蔼的笑笑,点点头。还有一个穿皮大衣的胖绅士提出了“我们究竟要何年何月才可以打退日本兵?”很可笑。总司令又只是和蔼的笑笑,可是当然不点头。问题多得很,可是写在小纸条上了。总司令预备一块解答。
“今晚这个座谈会实在是一个恳亲会,”这是总司令站起来说的第一句话。不错,这个会到后半多少有点像恳亲会了。老老少少,一团和气不时发出来一阵阵笑声。总司令首先分析了国际局势,就不啻给听众看了一幅生动的漫画:看,法西斯实在还够不上做强盗,而是扒手。扒手还是怕挨打的。这几个法西斯穷国只有一把刀,就把刀拿出来东戳一戳,西晃一晃,吓一吓,弄一点便宜。“意大利有几只潜水艇,就用几只潜水艇去撞人家的船只兵船也好,商船也好,在地中海冒起来了又缩下去了。”像美国这种有钱绅士,在这种场合就对法西斯蒂说:”你还不起钱就不要还得了,别那么凶奄。”苏联呢,明知道法西斯蒂是空头,在打扑克里只是吓唬人,所以随时都预备说;“来吧,我看!”总司令用“就是这个道理”结束了许多话题的明白解释,叫大家听完了一想也觉得确乎就是这个道理。
总司令戴起眼镜来了,又摘下来了:一张纸条上的看完了。他抬起头来说了几句,在讲话的中间或者末尾不时的引起一片笑声。问题本身也颇有些怪好玩的。主要是共产问题,总司令说:“在实现三民主义这一点上,共产党很乐意和竞赛一下。”听众笑了。有人问;牺盟会和共产党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总司令把眼镜又摘下来了,接下去就是一个简单的答复:“到底怎么样?到底还是朋友关系奄。”听众又笑了。“合理负担是不是共产?”总司令回答说:“合理负担是阎司令长官提出来的,也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办法。阎司令长官在山西算得最有钱了吧,他还要共人家的产吗?”听众又笑了。不要笑得太多了,还是深省一下刚才总司令对于“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会不会实行共产?”这一个问题的答复吧:“什么都打得稀烂了,还有什么产可共,第一得先造产呵。”
长治马路宽。长治城垣拆了两次,已经快平了。快成了一条宽阔的环城大马路的基础了。
长治,12月22日(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