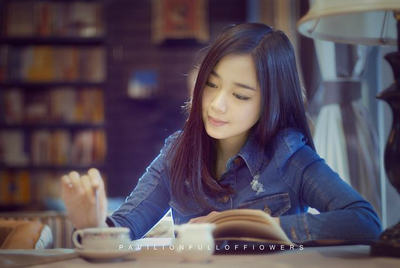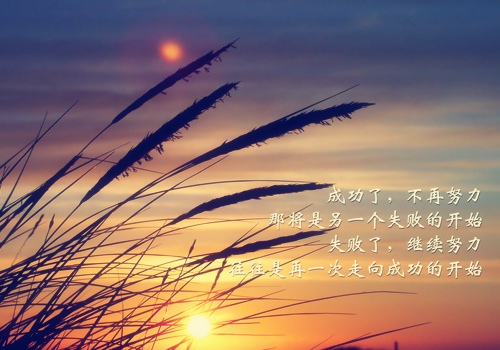
有一位朋友说:每当看到一篇好文章的时候,除了于心有戚戚焉之外,更会触动内心深层浓郁之情愫,那种感觉真的好棒!
然而他又接着表示:不过欣赏归欣赏,如果要尝试将那种感觉化作文字,有时候却又抓不住其精髓而无法下笔,因此只能够抱持着纯粹欣赏而已。
他的话真有道理,也许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感觉;记得有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被问到为何拥有源源不绝的写作题材时,他的回答蛮有意思。
他说:只要打开心灵之窗,用心感受美丽的娑婆世界,则处处都会有灵敏的感受,而四时皆有美妙的文章。
我们觉得他的话语并非故作矫情,而是累积自己亲身体验之后的'心得,所以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虽然人们都知道,从事任何一种创作的过程,都是很快乐的事,可是偶尔却会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情况发生,所以每个人的笔触都会有不一样的面貌。
不过笔触有差异的作品呈现出来之际,当然不会影响到创作过程之乐趣,因为那是每一位作者的精心成果,总是最宝贝的作品。
因此,亲爱的朋友,我很想告诉你,在每个夜晚心灵分享之际,我很愿意将许多故事当做题材,然后用愉悦的心情,写出一篇篇属于全然自己的札记。
当然还要告诉你,当每一篇文章完成的时候,不论是否为一篇佳作,除了可以享受写作之乐以外,其实对于个人而言,你永远都是不可或缺主角呢!
由于应石家庄市“当代文学函授学院”编辑部主任田浩先生之约,才写下这篇粗浅的文章。其实我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可谈,不过是与大家相互交流、共同学习。
2001年,我幸运地结识了缪斯这位高雅的朋友。从此与她不弃不离,共同走过九个年头。九年来,她就像一缕皎洁的月光,时刻照耀着我的思想;她又像一泓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灵。她使我的精神富有,使我的生命蓬勃,使我暗淡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由于对她的痴迷,就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
我写诗,靠得是生活与阅读,加上自己的一点悟性。再就是有幸得到了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屠岸先生和学院的田浩先生,以及远观、宋弘雅先生们的悉心指导——在他们的指导下,我追寻着古代和现代文人的足迹,慢慢前进。
古人写诗有“三不可”,即:“不可强作,不可徒作,不可苟作。强作则无意,徒作则无益,苟作则无功。”我一向作诗本着前者和后者。诗是心灵的自然流露,如果强作就会失去自然本色。写诗时,必须要对某种事物或某种情景着迷,从产生意念到激情迸发,并有强烈的创作冲动。那时写出的诗才会有真情,有意境,才能打动读者。相反,你若对某种事物和情景,见之无动于衷,甚至视而不见,而硬是将一些抽象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即使能写出诗来,也会毫无诗味,不过无病呻吟的那一类。
诗歌是崇高的艺术,它可以反映生活的阴暗面,或者是负面;还可以颂扬真善美,抨击假丑恶。诗人应该有先进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坦荡的胸怀,优雅的文采,并且有担当,有责任。因此,写诗绝不可苟写,要认认真真写,一丝不苟的写。其中包括反复推敲,认真修改,练字练句,更要练意。
对于写作,著名作家有高见:“不管你当不当作家,一定要有三个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表达能力……”当诗人更要有这三个能力。先生把“观察能力”放在首位,这说明它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观察能力,对于写作就等于无源之水。我们要以独特的视角,细心入微观察宇宙的客观事物,体贴物理情态,才可能有独特的发现,才能产生相应的审美效果,才能有所新的创造。
其次是“想象能力”,我认为想象应该是一只翱翔蓝天的鸟儿,也应该是一匹驰骋原野的千里马。
我在创作《春雪》一诗时,正是春雪飞舞的四月。我伫立院中,仰望着空中纷纷扬扬的雪花,轻盈地飘向大地。望着望着,我的想像就飞向了银河,飞向了月宫。我想:“人们传说中的仙女散花是不是这样的景象,这般的美丽。”那一刻,我不觉得诗意涌向心头。于是,我回屋写道:“轻轻的,盈盈的/带着银河的波光/带着月宫的桂香/旋起洁白的裙裾/是仙女在凌空撒满了梨花……”(这是第一节,共五节)。这节诗,虽说词浅意薄,只是写景咏物,但它无色而有色,有亮度,有味道,有动感,并且物中见人。此诗于2004年春天同在《黑河日报》、《日照日报》上发表。
另有2008年春,我去县里开会。会后一个人走在春光明媚的大街上,享受着浓浓的春意,感到十分惬意!走着走着,便突然想去江边玩玩,于是我就朝江边走去。还没等到走近江边,那热情奔放的风景扑面而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挤进我的眼帘——江边暖阳高挂,江面波光潋滟,岸上新绿拥着初红……在风光旖旎的江畔上,坐着一大排垂钓者。我情不自禁的走到他们的身边,看着他们反复地甩着鱼竿,鱼篓里的鱼却寥寥无几,只装着一篓篓习习的江风。但他们并不为钓不到鱼而焦急,反而悠闲自在。我看着那情景,就像看一副活的、诗意盎然而富有神韵的水墨画。那一刻,我心里的诗直往外拱,就随意口占了一首七绝《春日众人江边垂钓》。诗中写道:“春阳闲挂嫩江天,垂钓人儿一江边。鱼少人多醉翁意,竿长线细甩诗篇。”这首诗写在纸上只修改了两个字,一个是末句的第五字:“甩”字,原为“钓”字。因为改用“甩”字比用“钓”字更有动感,又避免了一个重字,也为此诗增添了点神韵。——七言诗的第五字正是诗家所谓的诗眼。另外一个字,是开头的“春”字,原为“暖”字,现在看来,还是不改为好,因为改后减少了诗的温度。
别看这首诗短小,却基本做到虚实相生,神形兼备,也符合古人所强调的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此诗2008年在上海一家诗报上发表。
以上谈的是前两个能力。最后的一个能力,就是“表达能力”,简单地说,即是把自己对事物的`所见所思,用精练的文字,将它们组合成诗。但是,说着容易写起来难。是因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要艺术结构的手法来表达。名家作诗都很讲究起、承、转、合,四个环节。在一首诗的结构领域中,占重要位置的莫若开头与结尾。一首诗的开头结尾(起、合)最难写。一首诗,如果有一个好的开头,会引人入胜,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开头若不好,反而会失去很多读者。
从写作意义上讲,开头可以开辟一个广阔的意境,引来思绪泉涌可以使思绪顺利展开,就能一气呵成的完成全诗。开头的方法很多,可以是开门见山,也可以是曲径通幽,可以是突兀高远,也可以是平淡亲近,但都要根据诗的内容和布局来定。虽然诗的开篇方式种类很多,但都要从立意出发,为立意服务。
我的一篇《秋天的田野》开篇是这样写的:“秋天的田野,挤满了成熟和希望/玉米包金,稻谷揣银/大豆又把铜铃摇响……”这个开头用的就是“开门见山”的手法,同时又用了“列锦”的艺术手法。这首诗一开始就把丰收的景象展现给读者,把读者的视线轻而易举的引进秋天的田野。这个开头,曾被名家称为生动之笔。
结尾也很重要!好的结尾,如嚼干果,似品香茗,令人回味无穷,给人留下美的想象空间。我们虽然不能像大家们一言九鼎,笔力千钧春雷动,掷地可作金石声。但总得做到一语贯全篇,笔有刀剑之利,掷地有雨打荷叶之音。比如我的一首《留守女孩的眼泪》一诗的结尾:“一个11岁的留守女孩/留下的两行眼泪/湿透了一个村庄。”这个结尾,不仅使意境更加丰满,而且突出了诗的立意,也合乎词浅意深的诗家之语,同时又给人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
如果起、合写得精妙新奇,承、转自然也不在话下(承,以为承接上面的开端,而予以发展;转,峰回路转的转折变化,其中包括矛盾冲突和情节行文的起伏跌宕)。
我写诗一向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无论是叙事、抒情、咏物、写景,或兼而有之,都要尽力做到叙事有情,咏物见人,即使通篇写景的诗也要做到,“一切景语皆情语”。其二,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客体,去认识感受事物的本质,甚至把自己变成草木、花朵、江海、湖泊……屠岸先生在《诗刊》卷首语《客体感受力》文中说:“物我合一,就能发现过去从来没发现的东西。”——把客体发现的新鲜的东西,用新鲜的语言恰到好处的表达出来,做到:意要称物,文要逮意。
今不揣浅薄,说了这些缭无秩序的话语,实属班门弄斧。文中不免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错误,敬请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多多指教!
郑成美2010年2月23日
从小听了不少故事,上小学又读了不少课外读物,因此对文字有了兴趣,所以,上初中时就有了创作欲望。
大约是1957年上初二时,一次
还有一次能称得上“创作”的是1958年的“七一”诗歌朗颂会。“七一”前夕,学校发出通知,为了庆祝建党37周年,学校决定在7月1日全校举办一场“庆‘七一’诗歌朗颂会”,要求师生踊跃参加。
通知发出后,各年级的班主任都召开了班务会,发动学生创作诗歌参赛,并把这次活动提到这是对党感恩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我们一级三班的班主任董瑞洲老师,还特地叮嘱我:要努力写出一首好诗,为班级增光。
那段时间,课余和早晚自习时,同学们都在苦思苦想搞创作,都想一展身手。当然我也不例外,同样陷入创作的思索中。写啥呢?
我想到:这年的6月,我们学校按大炼钢铁指挥部的指令,停课到南海淘过铁砂,运铁砂我又到过炼铁厂,那炉烟滚滚,人喊马叫的气象,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大开了眼界!
想到了这些,我决定用诗歌的形式把这段生活及感受抒发出来。经过几天的思考推敲,我终于创作出长篇叙事诗《吼叫吧,海啸!》。
朗颂会选在“七一”的晚上。那晚,月朗星稀,微风轻拂,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那时学校没有大礼堂,近千名师生坐在操场上,三盏汽灯照得操场瓦亮瓦亮。正式开场前,各班互相拉歌,你班唱过他班唱,会场已是一片热烈。“庆‘七一’诗歌朗颂会”正式开始后,被选中的近40名同学按顺序陆续登场,个个精神饱满激情昂扬,其诗文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与颂扬,博得了台下阵阵掌声。但其诗歌大都很短,只八句或十几句。也有较长的叙事诗,都是历数从党的诞生后率领全国人民经过的革命历程。但是这些诗歌,几乎是千篇一律,使人有抄袭感。只有我是把党的伟大与英明融进了南海淘铁砂与大炼钢铁场面的感受之中。年代已久,已记不清具体的诗句了,只记得每节开头都是:“吼叫吧,海啸!请你大声宣告——”,每节读完,都赢得一片掌声,当全诗朗颂完后,台下是掌声雷动,真如吼叫的海啸,经久不息!由此激动得我夜不能寐。
事后,我这首长诗还被学校板报组抄在黑板上,向全校展示了很长一段时间。使我的“作品”第一次有了不少读者。
真正开始创作是我到了北大荒当了渔工以后的1962年。一天,弟弟拿着一张《佳木斯日报》,把他写的一篇题为《徒工
那时,家庭经济又比较困难,我在修造厂当车工,上夜班。有了时间得上山搞副业,采中药、采猴头蘑菇、拣橡子;冬天摘冬青、拣烧柴,能抽出搞创作的时间实在不多。晚上搞创作,又受居住条件的限制。每当夜晚,一家六口躺满一炕,哪有个可供创作的清静地方?所以,那时我写稿子,大多是在被窝里趴在枕头上写的。
就是在被窝里搞创作也要受到限制。冬、春、秋问题不大,因为家人已养成了在灯光下照睡不误的习惯。但一到夏季就不行了,因为北大荒的蚊子小咬多,亮灯时间一长,讨厌的小咬会无孔不入,飞满一屋,搅得全家不得安生。所以,那时我最讨厌夏天。
记得1982年夏天,我构思了一篇小小说,“腹稿”都打好了,就是没有机会写下来。一天晚饭时,我把小说的内容对妻子讲了一遍,她听后说:“这篇东西挺有趣的,你应该写下来。”其实我等的就是她的这句话,便故意为难地说:“可进小咬怎么办?”她想了想说:“豁出今个晚上了,不过你得抓紧点。”
那天晚上我写到半夜时,抬头一看,我的天!雪白的天棚上爬满了黑压压的小咬。看看被小咬咬得不住滚动的孩子,我真有点过意不去了。妻子终于爬起来说:“快别写了,咬得人实在没法睡了。”我还有个结尾没有写完得坚持一下,便说:“听人家说,端盆水用笤帚一划拉,小咬就掉在盆里了。来,咱试试。”于是,我端着水盆,妻子就在天棚上划拉开了。一不小心,我把盆里的凉水,触到了炽热的灯泡上,只听“嘭”地一声!水花四溅,灯泡爆炸了!黑暗中,孩子哭,大人叫,乱作一团。好在没伤着人,只是虚惊一场。
妻子一个劲地叨咕:“不要再写了,咱又不是创作的料,再穷也不差那点稀汤寡水的稿费。”
我也扪心自问:已是半百之年了,遭这个罪,何苦呢?
多年来,我就是这样悔而不改,苦巴苦熬地坚持创作下去,在编辑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也发表了一些东西,也自觉好像摸到了点创作的门路,便鼓足劲儿想继续大干下去。
沉梦终于惊醒。
1990年初春,我刚刚放下手中起草的《场长工作报告》,便应邀参加《北大荒文学》编辑部在佳木斯市举办的笔会。参加这次笔会的作者中,属我年龄最大,因此倍受编辑们的优待,特地给我一间清静的办公室,让我潜心写作,出盘“好菜”。我也丝毫不敢怠慢,足不出户,整整把自己禁闭了三天。可三天后当我重新拿起苦思苦想创作的所谓小说时,我吃惊地发现,那完全是一堆语言垃圾。惶感、苦痛中,我终于大彻大悟了:艺术的圣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插足的,像我等之辈,在圣殿门前溜达的份儿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心情反而舒畅了,无忧无虑地逛了一天大街。
编辑老师听说我遇到了困难,过来劝我:写不下去不要硬写,硬写写不出好作品,先把素材放下,焖一焖,等成熟了再写。
心想:焖什么焖,我下定决心知难而退,从此洗手不干了。
可是,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只要你沾了它的边,苦也好喜也罢,你只能永远臣服于它。笔会归来,饭后茶余,我仍然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引着,走进己是今非昔比的办公室,创作着、痛苦着。当年那篇我写不下去的小说素材,我一“焖”就焖了9年,终于在1999年写成了4万字的中篇小说《西伯利亚风暴》,发在当年《北大荒文学》第四期上。
可更多的时间是,烟缸里的烟蒂小山似的堆集起来,面前的稿纸却是一尘不染。
苦恼中,有时偶然抬起头来,瞅瞅墙上那面题词:“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的悬镜,竹影婆娑间(镜中有竹的配景)显现出一个秃顶、满脸皱纹且一副受苦受难者的形象。
我真不敢相信,那就是我。
时至今日,已人到古稀,我仍在创作着,痛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