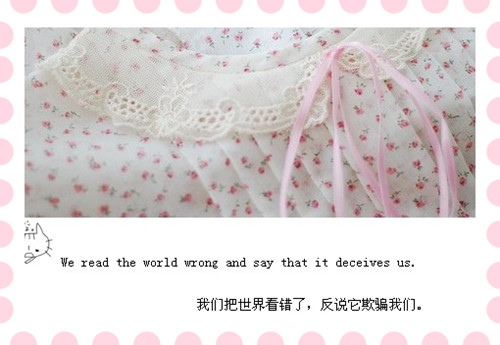
(一)封存记忆中的那只老风箱
每次在老家的锅屋炒菜,看着锅底那团旺旺的火光,便会想到小时候使用的那只风箱。置身老家,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与一个“老”字分不开,老人、老房、老井、老碾、老挂钟……每一种都渗透着时光的沉淀,伴随着成长的记忆,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现如今,在农村偶尔会遇到爆米花的老头儿,旁边放着一个老风箱。每当有人来爆米花时,老头儿就会把玉米或大米粒放进米花机里,然后扣紧盖子,放到炉子上,开始“唿哒唿哒”地拉风箱。这个熟悉的老风箱,对于现在的城里的孩子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鲜事物了,却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让我想起了当年拉风箱的难忘岁月。
风箱,也叫风掀、风匣,相当于今天的鼓风机,是过去农村家庭中普通但不可或缺的炊事用具。在沂蒙山老家的六七十年代,风箱立在各家各户锅屋的灶台边,风箱是一天三顿饭都离不开的物件。那时候,在每个清晨或傍晚的村头巷尾,总能听到风箱“唿哒唿哒”的声音,童年的梦总是在风箱声中醒来,它和着鸡鸣狗叫、伴着孩童笑闹的喧哗,大人们的脚步声、说话声,那动听的风箱声和袅袅升起的炊烟,绘就了一幅极具农村特色的风景画。
风箱的制作原理并不复杂,它用木头制成,长方体,内空,由一活塞和两根木条连接在手柄上。说句通俗一点的,风箱就是做饭时用的“鼓风机”,庄稼人生火做饭、烧水全靠这风箱催火,那风儿够大,吹的火够劲的烧儿。
我小的时候,哥哥姐姐每天放学回到家会帮着母亲做饭,他们就帮着拉风箱,我因为年龄小,只有站在一边看的份。再后来,当我有力气拉动风箱时,风箱已经不再受宠受了。现在想来,拉风箱用的是巧劲,长拉短放、快拉慢推,才能使火苗匀称而又不费柴。同时,要根据所做饭菜的不同,变化拉风箱的快慢和力度。炒菜需要急火,风箱就要快拉;熬饭或煮粥,开锅之前要用急火,开锅之后需要文火慢熬,拉风箱就要先快后慢;而最考验拉风箱功力的是烙大饼,要细拉慢拽,父母掌握的比较到位,想来这也是一道农村做饭的技术活。
母亲做饭时,我多半在一边玩耍,看到锅底的那团红红的火儿,心里有一种踏实和温馨的感觉。锅里的水哧哧作响,灶堂内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噼噼啪啪”的欢快声,燃料自然是庄稼秸秆,比如,麦秸、玉米秆、玉米瓤,豆秆、棉柴以及树叶等。不久,锅里的水沸腾了,整个锅屋里热气氤氲,如果是做一道可口的饭菜,那浓浓的香气随着缭绕的炊烟向外扩散。
说到风箱,还有一句民间歇后语:“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现如今的中小学生多半是不知道风箱的,多半会一脸的茫然,百思不得其解。如今的孩子,谁见过风箱?“老鼠钻到风箱里”的情况,我是亲眼见过的,小老鼠不小心钻到了风箱里,因为出不来,当推拉风箱时,老鼠在风箱里只有挨夹的份了。
光阴转瞬即逝,现在的农村已难觅风箱的踪影,父母在老家也早已用上了液化气,只是偶尔会使用一下地锅炒菜做饭,但是风箱已经再也找不到了踪迹。我想,多年后,怕是让人想也想不起来了。
风箱远离了人们,故乡暖暖的炊烟和亲切的风箱声却没有走远。当年我家的那只风箱已经封存在了我的记忆里,但是那只老风箱发出的“唿哒唿哒”的声音,仿佛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在我的心底回响,弹拨着我的记忆之弦,伴我铿锵前行。
(二)不老的挂钟
圣诞节的钟声似乎马上要在耳边响起,这让我不由地想起老家的那座老钟。每次回老家,正屋北墙上挂着的老挂钟总能发出清脆的声音,准确的告诉我整点和半点的到来,作为我的老朋友,又像在和我打招呼。
说起老家的这座老挂钟,不由得让我会想到那久远的岁月。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是没有钟表的,手表更是遥不可及的物件,平时的生活时间是靠经验来掌握的,对于我来说,只有看太阳的高度和天气的变化来揣摩了,不得不说这是当时农村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
我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没有钟表,自然只好估计时候提前出门,每天早上经过同村表弟家时,都是结伴而行,表弟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家就在学校附近,我们每次都是早早的到校。表叔在县城上班,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家里已经有了一座漂亮的挂钟,悬挂在白色的墙壁上,尤为好看,尤其是听到那响亮的“当当”的打点钟声,我是羡慕极了,当时心想,什么时候我家也能买一座呢?
我家终于拥有钟表,应该得益于我小学一年级的一段经历。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不到三个月,天气就已经入冬了,应该和现在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农村的冬天显然比城市寒冷一点。有一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认为快到上学的时间了,就起床上学,父母也拿不准时间,只好由着我。去喊表弟上学时得知还早,他们让我回家再睡会。生怕晚点的我,自然不会回家,而是选择了一个人站在未开校门的大门口等待。学校门前有一条宽广的河,校门口并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风吹得特别来劲。一个人在凌晨的寒风中耐心守候了足有一个小时,可想而之,我当时在原地哆嗦的.样子,尤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手脚是耐不住寒的,这一段往事一直时常浮现。穷人家的孩子受磨练,或许正是小时候的经历和诸多考验,让我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努力。
当时我心里一直纳闷,我的家庭境况在村里虽不富裕但并不贫困,为何一直没有买起钟表呢。后来我才得知其中的原因。我的母亲是姥姥家8个孩子中的大姐,几个舅舅当时有的要上学,有的要盖房子,有的要结婚,责任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我母亲的身上。我的父母亲把亲情看得很重,尽可能地把家里的收入贴补给了几个舅舅。
有了我这一段起早挨冻的深刻经历,父母亲就商量买一个挂座,解决我上学遇到的时间问题。本村是买不到挂钟的,父亲分别探询多个商店才得知,老家乡镇驻地的挂钟品种并不多,最多样式的是隔壁村庄的大吴皇路村供销社。买挂钟的时候,母亲专门带上我,母亲选了一个浅红色木质外壳的机械挂钟,挂钟有一扇门,上面有块方形玻璃,能看见里面的钟摆。母亲试着上了弦,钟摆自然摇摆,每摆一次,秒针的齿轮就发出“咔嗒”一声响,不亚于现在的流行音乐好听。这样一个挂钟价值58元钱,母亲即高兴也心疼,58元钱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当时不少于三个月的家庭收入,买了这个大件,带回家的时候,我心底的喜悦比现在拥有一辆漂亮的汽车更加鲜明。
母亲说,红色外表的挂钟喜庆,有好运。母亲有时会讲我抽红签的故事,我一岁的时候遇到一位到村里抽签算命的先生,我抽到了红签,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长大了会有出息,现在母亲每每提到抽签的事,我都不会反驳,因为我分明看到母亲沧桑的脸上显露出一份对儿子成长的自豪和对现在生活的满足。
有了挂钟的相伴,每天清晨它洪亮的钟声伴我起床上学,夜晚它有节奏的滴答声伴我静静的入眠。清脆声的挂钟一周就得上一次弦,不然它就会停滞不前。挂钟陪伴我顺利的度过了小学,走过一段段人生的路途,让我成为“时间”的主人。光阴似箭,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一起上小学的表弟早已在北京安家生子,我们每每提及此事都会满足于现在的幸福生活。
现在挂钟的样子已经有了变化,有些地方已经退色和生锈,我们全家却从未有过让它退休的念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还是那样坚强的生活,生命力愈发的旺盛,指针运行依然很准,整点报时的钟声更是清脆悦耳,还会有一阵阵回音,好听极了。且看着那一针针的走动,时光随着一点点消逝,好像它的生命里蕴含着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让我们珍惜时间、珍爱生命。
我想,没有了压力和动力,挂钟也会失去前进的劲头。这就是如同人生,只要我们心中充满希望,积极进取,坚定正确的方向,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就会感悟到生活的美丽和生命的真谛。
庄子云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不老挂钟的三个指针重复转动不断印证着人生的轨迹。我想,尊重时间,应该把温暖和关爱充盈家里的每个角落;尊重时间,应该把友谊传递给知心的朋友;尊重时间,应该让自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尊重时间,应该传递温情奉献爱心。
以钟为友,人生会愈加厚重。
几十年来,记忆中的打谷场,时常在我的魂梦里摇曳,散落一地故乡泥土的芳香,让人无限感慨,久难释怀。
故乡的打谷场位于村北山丘下,有2500平方米左右。走集体的时候,全村一百多亩的水稻都要从这里碾压,晾晒,颗粒归仓。许久以来,这片打谷场是全村人的盼头和希望。
那时候,水稻一年种两季,早稻和晚稻。每到开镰时,田里便人群涌动,热火朝天。有的乡亲头戴草帽,有的肩搭毛巾,有的小布衫勒在裤腰间,男男女女全部弯着腰,对着金黄色的稻杆,一下一下挥舞着锋利的镰刀。吱剌,吱剌的割稻声悦耳动听,被风传出好远。一莆一莆的稻子在人们身后整齐地卧躺着,最后一次留恋着滋养它的田地。
稻割完了,要捆要挑。这挑可是力气活,一百几十斤的稻捆压在肩上,无论路途多远,担都不许离肩,左肩累了痛了换到右肩,右肩累了痛了换到左肩。大家都知道,一旦下肩,谷粒容易脱落,糟蹋粮食,所以,挑稻者必须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他们在挑稻路上,你追我赶,不甘示弱,兴起时,还吆喝几声“哟,嗬嗬”,为自己也为同行鼓劲加油,那阵势好不威风。无怪乎,农村人当时挑女婿,第一句话就问媒人,小伙子能挑稻不?若能,则表示可以考虑,若不能则轻蔑一笑,没戏。
挑回来的稻子要堆码成垛。候在打谷场上的乡亲早早见有人来,迅速迎上前接过稻捆,先外边后里边,一层一层地压住茬,慢慢地往里收,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唯恐时间一长稻堆垮塌或倾斜。一连五六天,稻谷收割完毕,打谷场上便矗立着一排排金灿灿的圆柱形,煞是可观。村里几个老人常常得空来转转,评论一下稻垛堆得怎样,收成如何,白胡子一抖一抖的。
再过十天半月,稻堆的湿气风干后,便可以碾压了。为了减少稻谷沾灰粘砂,乡亲们先用锄头在稻场上细细地刮上一遍,铲平地面,然后挑来水,用瓢均匀地洒一遍,套上黄牛,拉上石磙,一圈一圈细细碾压,直到碾平碾光为止。名曰“压场”。
之后,乡亲套着黄牛,拉着白色的石磙在阳光下碾压。石磙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听起来并不悦耳也不令人生厌。牲口行走在厚薄均匀的稻谷上,转着同心圆一样的圈,一圈一圈地来回转动,不时偷一把稻草边走边嚼,惹得乡亲举鞭呵斥。
到了起场的时候,等候在一旁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拿着木杈,木锨,推板,扫帚等各式工具,各就各位,边说笑边忙碌,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白婶手举木杈,高高挑起一大摞稻草,用力一甩,直甩到三四米外的自家男人脚下。男人见了嘿嘿一笑,夸赞说:“还是俺媳妇力气大呐。”不知谁接上一句:“白天力气大,晚上没力气……”引起一阵哄堂大笑,白婶追着逗笑的后生一阵好打。
很快,稻草清理干净,人们开始扬谷。趁着风向,男人将刚刚碾压下的谷子高高扬起,在风力的作用下,使谷粒和草渣、灰尘分离开。妇女不失时机地用扫帚打着溜子,最后一次净化谷子。老队长用手捧半把新谷,咬一粒,嗅一把,笑得眼、鼻都变了形地说,“谷粒饱满,香着呢。”
于是,乡亲们开始深呼吸,打谷场的'空气真的弥漫着淡淡的新谷香味。他们都喜欢这种香味。这香味让他们忘记了烈日的烘烤,忘记了收割时的腰酸背痛,也忘记了饥渴的困扰。
那时候,我还小,我们几个同龄的孩子,喜欢在打谷场边玩耍,在青草丛里捉着蚂蚱,在松树底下捉着蚂蚁,还有河边菜地的小青蛙。若遇晚上劳作,打谷场架起五六盏用夜壶做的煤油灯,亮堂堂的。全村20多个小家伙过节似的聚集于此,成群结队地在平整光滑的稻场上疯跑、嬉闹,有的玩捉迷藏,有的玩老鹰抓小鸡,有的玩丢沙袋,有的玩跳绳……我最喜欢把一双旧布鞋脱下,当军体课上的“手榴弹”扔向天空,然后寻找、投掷,再投掷、再寻找,乐此不疲。
谷子未进仓前,生产队都要派人守夜。我喜欢缠着父亲一起去。夜色下的打谷场,少了许多白天的喧闹,累了一天的乡亲们回家歇息了。守夜的乡亲常常围坐在一起,一边吸旱烟,一边聊家常,相互逗着乐子,开着玩笑,笑声随风而飘。那时的我,躺在父亲身旁,仰望着星空,听着他给我讲山猴、水鬼的故事,听着听着,我便不自觉地进入了梦乡。
一天夜里,我被吵闹声惊醒,原来是父亲逮住了一个小偷。此贼是本村最老实的社员,声称其父刚刚病愈欲吃干饭,借了几家都未如愿,无奈只得瞒着父亲乘夜深来偷点稻谷,回去弄饭,满足父亲。他还请求不要告发他。那年月,乡亲们一日三餐吃的大多是红薯,南瓜、稀饭,能够天天吃上干饭,是他们最真切的心愿。父亲理解贼人,动了恻隐之心,与其他几个守夜人一合计,让小偷装上一小袋子稻谷回家去了。事后,父亲叮嘱我,不可声张此事……我不知父亲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现在也不太明白,也许对错参半吧。
除早、晚稻外,经打谷场碾压,晾晒,归仓的还有油菜、小麦和黄豆。虽然这些农作物种植面积不多,收成也极其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生产队的经济,丰富了乡亲们的生活。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我慢慢长大了,读书、上班、成家,最终离开了故土。这期间,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各家各户的打谷场比生产队时候的小多了,都建在各家的田头地边,既方便又省力。曾经火热一时的村北那片打谷场逐渐少有人用,冷清多了。后来,乡村不再缺吃少喝,温饱解决了,小康实现了。各类惠民政策加强了家乡机械化运作,提高了农村生产效率。乡亲们的经济条件得以大大提高,各式各样的脱粒机、收割机使得打谷场退出了历史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我看来,故乡的打谷场,碾走了曾经艰苦的岁月,碾碎了游子思乡的愁绪,碾来了丰衣足食的幸福日子。于我而言,故乡的打谷场,永远烙在我的记忆深处,终生难忘。
人至暮年,烙在记忆里的事很多很多,总喜欢把它们一一抖搂出来,在脑海中能够拓出的最清晰的印记,算是少年时代那些四四方方或圆或扁的故事。掰开一个小小的豁牙儿,就能流出听得见的那些细碎的声音,如小溪哗哗滴落于石,那些溅起的水花总在自己的眼前跳跃……
--题记
小的时候,生活的日子里总是伴着“咔哒咔哒……”地响声,那声音是山村心脏跳动的节奏,是山野间传承的音符,是村民祈祷默吟的心歌……
“咔哒咔哒……”这就是农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风匣声。它就和农家的锄头耙耱一样家家都有,不可或缺。
农家的风匣一般安装在灶头的右边,它是一个长约一米、宽约一尺左右六面体木箱式助燃工具,前后木板中间均安装一个进出气方孔,方孔上面又安装了一个小小的木盖子,其作用是封闭进出气空。其中前面的木板为活动板,中间上下有两个圆孔,两支拉杆穿过此孔,拉杆的一头又有一个方木板,四周用麻皮扎着鸡毛,然后涂于熬胶粘住,一头一根长约一尺竖立的握杆,左边下部安装一根木管插入灶头通往燃火处的孔中。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那只风匣似乎年代已久了,风匣的外表已陈旧黝黑,而那拉杆坚硬光滑锃亮,右手握住它来回滑动没有一丝的凹凸感,至今我也没弄清楚那拉杆是用什么木材而做,但那时不可能专门去到哪买这种木材,想必是家乡山中的桦木吧,因为桦木较为坚硬。
使用风匣的灶头上基本都安着一个大铁锅,烧水做饭用得燃料大都是炭,因为那时煤较少也贵,所以庄户人家都要买炭,虽然炭便宜但拉运炭确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农家用得烧炭在离家乡百里远一个叫“大峨芭”的山中,大峨芭主要产炭,当时没有什么采矿的先进设备,只有靠人工挖掘,即使人工采煤但因它的产量高储藏量大,又是本县的矿藏资源,所以才成立了“大峨芭煤矿”,也是当时古浪县三大煤矿之一,唯一产炭的煤矿。
驮炭的主要运输全靠牲口,而农户家大多饲养的是毛驴,驮炭的前一天,那些准备近日急需用炭的人相互商量好后,便在亲朋好友家借好牲口或口袋,因为一次就要将全年的烧炭驮够,每个人家起码需要七八头驴或骡子,自家的口袋不够还要借人家的口袋,口袋大都是毛口袋,那种毛口袋一条能盛四斗半,一次一个人去驮炭困难重重,力气小的人连口袋都扛不起来,不要说还要搭在驴背上,所以必须约上2-3人以上才能完成驮炭的任务,期间还要让驴骡休息饮水吃草,此时必须把口袋卸下来,等牲口缓好再将装炭的口袋搭在驴骡背上。驮炭人约好后,人们都知道哪一个人瞌睡轻就让他翌日早早喊人,走远路赶早不赶迟啊……
天空的星星还在眨着眼看着山村的寂静,月亮还没来得及收回洒在大地的温柔,“走哎,驮炭走哎……”,指定喊叫的那人一声声地喊叫将睡在被窝里准备去驮炭的人都惊醒,其实不仅仅是这些驮炭人,几乎全村的人都被他惊醒了,一声喊叫亦将农家的狗也惊得吠声四起,几个牛肋耙窗中散射出黯淡的煤油灯光,那是要去驮炭人家的灯光,这声喊叫其实就是催着你赶快起来吃早饭,听到喊声,女主人起来到厨房的灶火里点燃柴火,锅中加入少量的水,那“咔哒咔哒”的风匣声夹杂着家人的期盼传遍了整个村子,水开了女主人立马打上两只“荷包蛋”,将笼里有数的白面馒头取出一个,端给丈夫要他吃的饱饱的,因为那时的农家早饭大都是山药拌汤,能吃上“荷包蛋”加白面馒头那就是“另锅子”(方言:专门做得好饭),吃过了早饭,驮炭人和他们的驴骡“咯噔咯噔”踩着村里的那条土路远去了……
烧灶火拉风匣都是母亲的活儿,加火前要将炭放入一个大盆中,倒入水搅拌成糊状,将柴火点燃,母亲右手一边拉着风匣,左手拿着小铲铲上糊炭放在火上,随着风匣的“咔哒咔哒”声,放入的糊状炭一旦加热自然变成了焦炭,而焦炭火旺耐燃,只见那炭火闪着蓝光火头一高一低,一回儿整个灶内一片通红,那些炭烧过后都变成了块状,母亲拿着一根小木棒将炭块压碎,然后在火中来回倒几下,那些碎了的炭块就会从炉齿里掉下,接着再将糊炭放入火中,这时母亲拉风匣的.右手往复快速运动,那火霎时便旺了起来。
风匣响得最欢的便是每年的腊月,那时生活虽然困难,但过大年是传统的节日,每家每户都要蒸馍馍,这个时节父亲便抽出风匣的拉杆板子,将磨得剩下的鸡毛全部撕掉,换上早就准备好的新鸡毛,用麻皮粘扎好,新放的鸡毛因为密封严,风匣拉起来肯定费劲,但输送给灶火的气必然多,这天拉风匣的任务自然是我们姊妹几个,因为母亲还要和面揉面,加工馍馍,什么“花花子、馒头子、鱼儿鸟儿”的忙得不可开交,拉风匣主要还是我,因为我是老大,年龄大力气相对也大,母亲拉风匣是坐着拉,而我因个头矮坐下使不上劲,必须站着拉才能将风匣拉杆拉到底且拉匀称,站着拉也得有特定的姿势,不然一会儿就没力气了,那就是“前腿弓,后腿蹬”,这样才能腰不酸腿不困,家里的蒸笼是用松木制作的四层蒸笼,蒸一笼馍馍需要一个多小时,而风匣不能停止,弟妹还小即使帮我拉也拉不上几分钟就会喊叫,如果我不及时接过拉,他们可不管,立马就跑出去了,这样逼得我不得不想办法,那就是扁工,提前将我伯伯的俩儿子说好,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比我小一岁的弟弟,这样我们轮流交换谁都轻松……
风匣的“咔哒”声伴着母亲的身影,也伴着我成长的岁月,1981年我在母亲手拉风匣的声中,吃过了灶火烧煮的手抓羊肉后,踏上了从军的路,帮母亲拉风匣的活儿自然落在了弟妹们的身上,在军营里我才发现一个连队百十号人,而炊事班的战友们做饭,那大灶前一直放着一个电动鼓风机,开关一拉那风吹得匀称而且不断,那时我就想家乡何时能通上电,母亲能用上这样的电动鼓风机多好啊!1985年我退伍回家,哦,家乡已通电了,那个未变的灶头前也安放着一个小小的电动鼓风机,二弟说:自打我参军的第二年,老家已有了手摇鼓风机,一个十五元钱,每次做饭蒸馍时用着它轻松多了,通了电之后又买了电动鼓风机更好了,而那只风匣早已不见了,已在沧桑的岁月中藏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