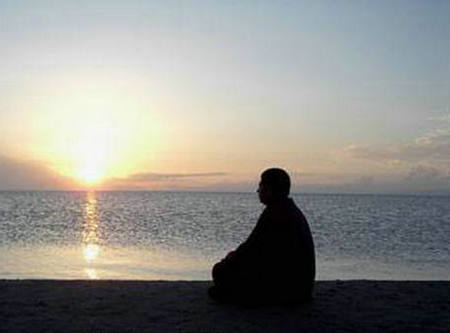
每当过了中秋节,上下班的路上就有了一些卖烤红薯的小贩,推着经过改造的两轮车,上面架着一个铁皮桶做成的烤炉,顶部摆放着烤熟的红薯,发黄略焦的皮散发着特有的香味,弥漫于空中,吸引着来来往往,脚步匆匆的行人。
烤红薯的香味大老远就可以闻到,不时有过往的行人驻足买上一个,小贩们认真地对待着每一位顾客。他们又像一个个恪尽职守的士兵,每天早上出门,到晚上九点以后才借着昏黄的路灯收摊,打道回府,就这样日复一日。
每每这时,我也会停下匆忙的脚步,买上一个品尝,自己喜欢这味道,而更多的是它时常勾起我的记忆。
(一)
儿时,因为种种原因,物质总是那样的匮乏,瓜菜代,杂粮基本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渭北旱塬,红薯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粮食,好在红薯栽种容易,管理简单,吃法很多,因此家家户户都会选择一片地来栽种。
每年过了元宵节,父亲就会在院子里向阳的地方砌一个棚,盖上塑料薄膜,然后从地窖里将保存完好的红薯在棚里育苗,做法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掌握塑料棚里的温度是技术活,每每这个阶段的父亲是非常忙碌的,定期浇水、测温度、按时盖草帘子,容不得半点含糊,不然一家人半年的粮食就泡汤了。
大约过了谷雨,红薯苗就可以移栽到地里,移栽的时候,很是热闹,左邻右舍都来帮忙,架子车上装上一个废旧改装后的大油桶盛满水,扛上锄头,带上经过修剪过根部的红薯苗来到地里。我们小孩子也能帮上忙,要么在挖好的小坑里摆放红薯苗,要么用葫芦瓢浇水,全家总动员,热热闹闹地将希望栽到地里,期盼着秋天的收获。
日子在手指尖悄然流逝,栽种在地里的红薯苗也一天天长大,隔段时间还需要除草。到了暑假,差不多就把地面封得严严实实,绿油油的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跃动。劳作散来的母亲,掐一些红薯叶子回来,拌上面粉,为全家人做一顿绿面,劲道细长的面条拌上葱花哨子,鲜红的油泼辣子,那叫一个香。
(二)
过了暑假,我们进入新的年级,埋在地里的红薯就开始结红薯了。父亲为了给我们小孩解馋,还会用镰刀在鼓起的有裂缝的红薯根旁边挖出一两个给我们蒸着吃。这时的红薯还没有完全成熟,水分不大,因此吃起来格外绵香。但是这往往会遭到爷爷的批评,“又惯着这这些娃娃”,父亲总是一笑了之就算过去了,但是隔三差五还会给我们带回来吃的。
过了二十四节气的'霜降后,红薯就可以收获了。如果没有落霜,父亲还不着急,还会说:“没事,再长几天,这会昼夜温差大,红薯长得快,还能增加产量。”但是如果落霜了,叶子就全黑了,这时就要赶快收获。
看着几亩红薯的收获,我们小孩也是开心的,玩、吃总是不亦乐乎。看着大人们忙着收获,我们兄妹也不闲着,分拣的活是会做的,而且做得很好。
戴上手套,把有伤的和完好无损地分开来。无损的就储藏在院子角落的地窖里,慢慢食用;有伤的又分成两类,轻伤切成片,晾干后可以磨成面粉吃;伤重的一部分洗干净后用机器粉碎做淀粉。
(三)
做淀粉就是将淀粉和渣分开,工序比较复杂。
在逐渐寒冷的深秋初冬,晚上的温度特别低,父亲穿上棉衣和棉鞋在水缸旁过滤淀粉。先在水缸上架好支架,那是一大块四四方方的纱布,四个角用绳子扎起来,绑在用两根木条订成的十字架上。只见父亲的两只胳膊左摇摇,右晃晃,白白的兑了水的红薯浆顺着布眼淅淅沥沥地流到缸里,然后再把那些渣放到旁边早已准备好的竹笼里,那些渣晾干后就被喂牲口了。母亲在父亲旁边帮忙加水,这时的我们已经帮不上忙了,就回到温暖的屋子忙自己的作业或者玩耍。为了使淀粉的颜色更加洁白瑄亮,父亲坚持不用硫磺熏,通常会多过一次水。
经过一次次的过滤沉淀,淀粉一次比一次白。这时候父亲就把水缸里的清水舀出来,留下雪白的淀粉,用大方块布包起来吊在架子上继续过滤水分,差不多过上十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用刀将完全脱水的淀粉块一点点地切成小块晾在院子的阳光下。这时我们又有活干了,搬个小凳坐在旁边防止麻雀贪食。晾干的雪白的淀粉用途更多,可以做凉粉,做粉条。
(四)
做粉条更是热闹。
每年到了寒冬腊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而且结出厚厚的冰了,这是做粉条的最佳时候,因为天气越冷,粉条就可以充分吸收水分,而减少黏度。粉条不但作为家里饭桌上菜盘子的补充,同时也能给并不富裕的家里增加点收入。
当地人把做粉条也叫挂粉条,比较费力,也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计。记得那时村子里有专门以这为营生的人,背着一把特制的铝瓢,背上自己的行头走村串户,生意好的时候大半个冬天都不在家。
我们家挂粉条时,母亲会把本家的一个亲戚请来的,和左邻右舍几家人联合起来,这样就更热闹。
曾经的忙碌热闹情景常常浮现于脑海中。
先要把一部分淀粉加水和成团,然后把另一部分淀粉加温水搅拌成透明均匀的粉芡,再将粉芡与湿淀粉混合搅拌成粉团,这里的水温、水量全凭那个请来的亲戚掌握,也许这就是技术吧。
接下来就是出力活,妇女们这时就是整理木棍,拉风箱烧锅。男人们大显身手了,有的守在大盆跟前递面团,有的在翻滚的锅前拿两根长长的棍子当筷子用,拨弄着下入锅里的粉条,还有的守在盛满凉水的大缸前等着下一道工序。
只见父亲身着单衫,挽起袖子,把面团放入漏勺中,用手背用力锤击团好的面团,面团随着重力挤压成条状入锅,浮起来就成为粉条,这时需要用长棍把基本成型的粉条捞起在冷水中过一遍,主要是为了不黏在一起。最后将粉条用竹杆挑起,晾晒在院子里支好的架子上进行冷冻。母亲和邻居的婶子这会也就忙碌了,一是隔一会给粉条上水,让充分的冷冻,这样既能保持粉条的不粘连,又能保证粉条的口感;另一方面也该给这些忙碌的人们准备饭菜。
等到第二天有太阳时,把冻成冰块的硬邦邦的粉条卸在小桌上用棒椎敲冰块,这时一双双手冻得通红。经过一天太阳的暴晒,晒干水分,等干透后就可捆扎起来或者盘成团存放起来,随吃随拿,这才算全部完工。
粉条的吃法很多,凉拌,炒菜,烩菜,和豆腐等包成包子,有了粉条,家里的饭桌绝不会逊色。
(五)
漫长冬日的生活大多数都和红薯有关联,地窖里储藏的红薯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供家人食用。可以和小米熬成粥,既有米香,又有薯香,拌上窝好的呛菜,色味俱全,总会使我们大开胃口。
秋日里晾晒的红薯干这时就可以磨成面粉蒸馒头,压饸饹,细长的褐色饸饹拌上豆腐萝卜丁葱花炒成的哨子,并不比羊肉哨子拌饸饹逊色。
孩子们正赶上成长的年龄,也没有办法,和大人们一样饮食。我由于身体的缘故,母亲总会从太爷爷那里给我挤上一点麦面。但是,孩子就是孩子,还是喜欢凑热闹,和兄弟姐们吃一样的,觉得这样有趣。
最爱吃的还是母亲做的烤红薯,忒地道。
记得只要碰上蒸馒头,笼屉的下面必有一层是红薯,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出锅后,一家人趁热吃一部分,剩下的放在竹筐中,母亲就会在做过饭的锅灶里放上几根,闭上炉门,让锅灶的余热将红薯烤干,让我食用。薯香还有任性,嚼起来特有滋味。
冬天到了,屋子里的土炕烧着了,晚上,母亲就会在的炕洞里放上三两根红薯,给孩子们解馋,炕洞里的烤薯没有在锅灶里的颜色好看,也没有那里烤的劲道,柴火的味道加上红薯特有的甜香味,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天气越来越冷,父亲就会在太爷爷的屋子里支起了炉子,是那种自己做的,土和砖块的结合,旁边加上一个侧洞,里面烤馒头,烤红薯很是方便。作为孩子的我们就又增添了一份快乐,早上上学的书包里就会加上一块烤得干黄干黄的馒头,晚上回来还可以吃上一根烤红薯,间或母亲还会在上面坐上一个砂锅,烩上粉条、豆腐、白菜还有夏天晒的干菜,饭桌上多了一份只有冬天或者只有过年时才有的一道菜,孩子们开心了许多,吃着也特别的香甜。
现在,父母家里早已不再使用土炉子采暖,但还是会选择带有抽屉的炉子使用,很是方便。冬天的每一次回家,只要提前个父亲电话,炉子里一定会有我喜欢的烤红薯。
岁月带去是总是容颜和生活的变化,始终不变的却是曾经的那一份乐趣,而且随着时光在手指尖的滑过,这份乐趣在记忆里越发的深刻,越来越清晰。
浓浓薯香,曾经的那一份记忆。
乡人爱吃粉条,道地的红薯粉,香弹筋道。
红薯粉好吃是一方面,最为重要的,则是它的易于搭配,可荤可素,可煮可炒,仿佛与什么菜都能搭配得上。做出来的菜品虽不雅致,却朴实而风味独具,热腾腾下肚,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不说别的,你仅就光听孩子们端着饭碗用嘴吸溜粉条时,他们小嘴里所发出的那一串串“刺溜”声响,都让你觉得十分快慰。像极了乡人们过着的日子,虽不宽裕,却平实而满足。
乡人对于粉条的喜爱,便缘于它的这种朴实而又兼容的特性。在每年冬日里赶年集的时候,遇着又干又好的粉条,都会成捆成捆地买回家放着,基本上都是买上一回够一年吃用。虽说镇子集市上平日也有粉条售卖,可毕竟专门卖粉条的摊点儿少,能供人挑选和搞价的余地不大。比不得将过年时的年集上,四邻八乡做粉条的人家,都会成架子车拉过来贩卖。
卖粉条的多了,自然可供选择和搞价钱的机会就大得多。乡人们平素过日子,都是靠毛儿八角俭省着过出来的,趁着这样的时机,也就把粉条大量买入屯在家里,以备过年和平日食用。那个时候,不论是你到了谁家串门,常就能见到他们成尼龙袋子或大纸箱子装着的粉条。而各家所屯着的粉条也是有宽有细,一如乡人们所过的日子。
乡人吃粉条最普通的做法儿,就是大烩菜。几块大肉片子肥瘦兼有,切成片儿的油炸豆腐干黄白相间,再配上点儿如玉色的大白菜,和着粉条在黑亮的炒菜铁锅里一烩,一锅热腾腾香气诱人的粉条大烩菜便呈现在家人面前。就着刚从笼里拿出来的热蒸馍,就是一顿简单实惠的丰盛餐饭。一张石桌,几条小凳,凑上几个只顾低头吃馍就菜的黑脑袋,仅凭听那此起彼伏吸粉条时发出的“刺溜”声,你就能感受得到他们吃得该有多满足。
但这样的饭食,对于那时尚在穷困中度日的乡人来说,却是不常有的,也仅是在有重要客人来了,或是年节的时候才吃得上。当然,这烩菜用的粉条都是先前赶年集时图便宜屯下来的。所需要的仅是从那袋子或是箱子里抽出一大把长粉条,将它们放进菜锅里煮炖,直到香气弥漫了整个灶房。
在大人制作粉条烩菜的时候,孩子们也没闲着,他们有自己的快乐。小孩子会从盛装粉条的袋子里抽出几根长粉条来,用小手拿上一根捏好,然后小心地伸到灶口的火苗上去烤,为自己制作一份简单的小零食。那时的孩子基本都有过烤粉条的经历,它的乐趣并不在于吃本身,而是享受烤制时那样一个神奇幻化过程的快意。
烤粉条就是将粉条伸到火里,与火焰保持适当的距离,使粉条中的淀粉受热膨胀,颜色由原先半透明的禇红色变成膨化后细腻的雪白色,质地从原本的致密紧实而变得蓬松无比,直径也一下子增粗了三四倍。而且,在烤制时因各部位受热的不均衡,粉条膨胀时就会自然而随意地弯曲,似蛇般来回扭动,如烟花绽放般奇异瑰丽。这一切仿佛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给孩子们平添一段奇特而美炒的经历。
只是,这样的烤制过程要有耐心,且不能过于贪婪,你不能指望着这样的美炒过程会无休止持续下去,它需要你努力拿捏好一个平衡的度。这个度就是既要尽量烤得稍长些,又要保证已经烤膨化出来的粉条,不因温度过高而烤焦黑或是被点燃。否则,因为你的一个不小心或是过于贪婪,所有的欣喜都会因为温度过热而化为灰烬。
当然,孩子们烤粉条玩乐是一方面,最终的目的还是图着烤膨化后放进嘴里吃着解馋。所以,并没有哪个孩子会愿意像艺术家搞创作一样,去把烤粉条当作品一样耐心去烤,而是烤好一截儿就放进嘴里咬下来,一边烤一边吃,直到手中的粉条被烤好吃完。这烤粉条虽快乐,却只是饭前的点缀,而那粉条大烩菜才是孩子们心中真正的大餐。只待大人们喊一声:“吃饭了!”几个黑黑的小脑袋就会快速挤过来,一人一碗端着大快朵颐,让肉的香、粉的弹泛起在唇齿之间。
长粉条用来烩了菜,那些在来回搬动和多次抽拿中弄断的碎粉条,也有它们的独特用处。精明的主妇们会把碎粉条用锅加水浆熟后,出锅晾凉剁碎,配上已经挤除水份剁碎的熟萝卜,放猪油在锅里一炒,洒上些调和面,加些简单佐料,就成了美味且香的包子馅料。那香味真真能够称得上是香气四溢,你站在院子里老远就能闻见它们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倘恰好有刚炸过油的猪肉油渣,剁碎了掺进这馅里,那味道和质感就更为丰满了。
若是你放学回家,还未进得屋里,就有这香气扑鼻的炒粉条味道袭来,都不用想,就知道家里今天是要吃蒸包子。那香气能诱得你口水直流,还等不到包子上笼,就会急不可耐地先拿了小勺,在盛馅料的盆子或是锅里舀上一勺塞进嘴里,先吃为快。那咸美鲜香的口感,任你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将它忘记。那是猪油炒红薯粉条馅的味道,那是故乡的味道,更是只有母亲才能带给我们的不变味道。
吃上两口包子馅儿,孩子们欢快地去玩或是写作业去了,剩下母亲在灶间忙碌着。擀皮、包馅、上笼、架柴火,灶间不时升腾起层层呛人的.墨蓝色烟雾。炉膛里火焰通红,蒸馍锅上水汽嘶鸣,母亲手不停歇地忙碌着,脸上不注意就会沾上一小坨白面。灶间的炉火映红了她那沾有白面的脸,那脸上有岁月的印痕,也洋溢着属于她自己的简单幸福。她知道,再过一会儿,包子就可以出锅了,只要她的一声轻唤,孩子们就会像抢食儿的猪娃一样涌进灶房来。
孩子们会不等那包子晾凉,便迫不及待地拿一个包子在手上,然后左右手来回倒着,以防被刚出锅还极热的包子烫伤。尔后,就是极迅速地咬上一口,嘴里接连发出倒吸气的“嘘嘘”声,以便使咬进嘴里的包子快些凉,好尽快嚼烂下咽。既使这包子还很热,孩子们吃起来也是三口并作两口,只几下一个大包子就全填进了肚子里,颇有点儿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情形。这个包子的最后一口还未嚼着咽完,那只黑黑的小手,就又从案板上拿一只包子捉在手里,生恐吃了这个就再没有了一般。
母亲依旧在灶间忙碌着,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模样,脸上有说出不的幸福和满足。她知道,这是孩子向往以久的时刻,也是她忙碌了这大半天所期待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是一家人相守在窄小昏暗的灶房里,享受简单美味食物的时刻,也是她所能带给一家人最为普通和实在的幸福。
说完了做包子馅儿,家中的碎粉条还有另一个重要用途,那就是蒸焖子。
相传,清代时登封名人、礼部右侍郎景东扬,因幼时家贫,过年时无钱买肉,其母亲在煮好的骨头汤中加入粉芡、浆熟的粉条、五料粉,蒸熟晾凉后就制而成了焖子这种食物。因其味美,遂在豫中流传开来。
这样的传说,此前我是并不知道的,只是在后来查找焖子的来历时才得以知晓。我小时候只知道逢了年关,乡人家中基本上都会蒸焖子,而做蒸焖子的主料,就是平日那些折在袋子或是纸箱里的碎粉条。
主妇们将平素攒下来的碎粉条捡干净后,就会加水下锅去浆,等碎粉条吸水加热膨胀后,再加入用红薯淀粉勾成的芡汁,再弄些葱、姜、五香粉和食盐调味,如有肉沫加入更好,若无也可适量加些肉汤。将这些物料搅和均匀后,便可上笼去蒸。笼底铺上打湿的庥布,也可弄些白菜叶垫上,蒸熟晾凉便成了半透明而弹性十足的焖子。
可不要小看了这焖子,它不但继承了粉条弹香的口感,且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凉拌、煎炒、煮炖样样咸宜,兼容性也更为突出。乡人在年节时制作焖子,一则是因为天冷易于贮存,二则是它与各样菜品可自如搭配使用,给主妇们更多选择的空间。
人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有了这焖子,在女人们的巧手下,就可以极容易地幻化出许多种菜品。况这焖子又人人爱吃,几乎就成了年节餐桌上的必备佳品。从而,那平素不入眼的碎粉条也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变,一跃而成为年节餐桌上的主角。
这样的转变,既是乡人对千百年来饮食文化的一种传承,更是主妇们从穷苦日子中提炼出来的生活智慧,在一双双巧手的创造下,利用碎粉条,为家人创造出一餐餐可口菜肴。
于是,那长长短短的粉条,便在主妇们的手中,幻化成美味食物,融进乡人平实的日子里,或烩菜,或蒸包子,或上了年节的酒席,年复一年见证着乡人们的生活变化,吸收幻化成乡人们的筋骨、皮肉。
现如今,乡人们的日子好了,主妇们再不用为一日三餐而发愁。孩子们也不用为吃上一次包子而争抢,但与那些长短粉条有关的穷苦往事,却留在了几代人的记忆里,与独具特色的地域饮食文化一起世代传承。而那片土地上所繁衍生息着的乡人们,则依旧会在年节前的集市上买回几捆粉条,让它们与其它菜肴搭配着食用,随那些长长短短的岁月一起,融入生活,成为乡人最为平实而普通的日子。
红薯又名山芋,既能充饥又能甜口,称得上美味佳品,也是农民在种植的多项农作物当中产量最高的。不但在经营管理上省工省力,而且在食用上男女老少皆宜,吃法多样且从无吃腻之感。
记得刚刚解放那几年,我只有十几岁。那时家家都很穷。为了填饱肚子,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每年为了充饥,庄户人家选择了在地里栽种上春夏两季的红薯,图的是用不着投多大本钱,又省工,而且产量高,一年收下的几千斤红薯储存在地窖里,从冬仨月到青黄不接的春天,心里就有了主心骨。一日三餐里没有粮食也能充饥,从地窖里提上一篮红薯洗净放在锅里,灶里填上几把柴禾,烧上几开儿水蒸熟,一锅香喷喷的红薯端上饭桌,成了天天吃不腻的美食。
到了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年月,刚有生产队那几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生产队收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的,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六、七两口粮。家家吃不饱,生产队仍然偷着在地里的沟边壕沿闲散地上栽上一、二十亩红薯,收下来连薯秧一起分给社员。红薯蒸熟能充饥,而薯秧晒干用铡刀铡碎,装在石磨上磨成面,掺上一半棒子面,贴饼子、蒸窝头,凑合着让一家人糊口填饱肚子。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家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起来,吃穿花都不愁,可受过饥饿之苦的人们,仍然记住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对成年累月吃不腻的红薯情有独钟,多数人家每年仍然栽种上亩八分的红薯,收下来后在院子里挖个小窖,隔三差五地或城里亲朋好友来时,提上点来蒸熟或烤红薯片,让大家吃个生口解馋。又因为红薯含蛋白质,淀粉含糖量都很高,每到春节来临时,家家都把几百斤红薯冲洗净,用粉浆机打碎,用包去渣过滤晒成团粉,再漏成上等粉条,以备过节食用或是送人。
如今,国强民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家家饭桌上的鸡鸭鱼肉、海鲜品,大米白面早已被吃腻,家家都希望吃些五谷杂粮,野菜野果,红薯更受人们的喜爱,被推上了改善人们生活的饭桌,蒸红薯、烤红薯。孩子们还专到超市购买用红薯加工成的薯条、薯片。每到入冬,你就会看到,农贸市场上的鲜红薯、街头卖的烤红薯成了的抢手货。红薯更成了乡里人向城里亲朋好友送礼的上等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