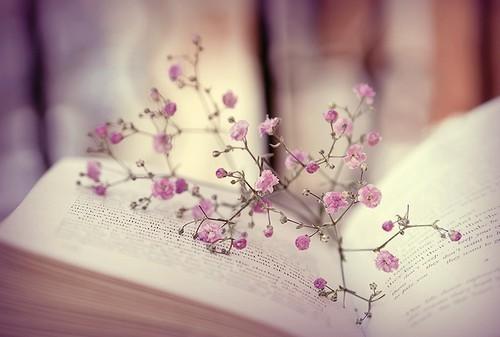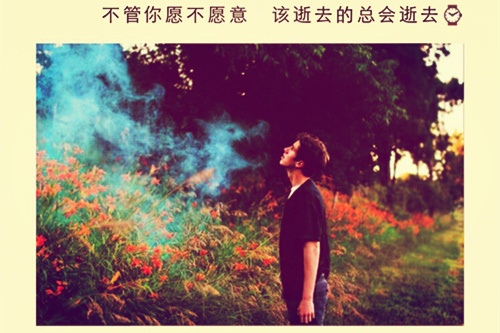
引导语:文人做菜就像文人画一样,随性,却又有雅致的讲究。汪曾祺如此,下面是有关他的谈吃文章的美句,与大家分享学习。
有些东西,本来不吃,吃吃也就习惯了。也就是口味这个东西是没有定性的。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一个人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对食物如此,对文化或者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
——汪曾祺《汪曾祺谈吃》
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
——汪曾祺《汪曾祺谈吃》
汪曾祺 一个“吃货”的修养
在汪曾祺众多的散文中,关于吃文化的文章占据了一大部分。如我们熟知的《端午的鸭蛋》、《蚕豆》、《豆腐》、《泡茶馆》……零零总总写了很多,专收汪曾祺谈吃的文章的书也日见增多,从书名上就可以一眼看出,如:《五味》、《寻味》、《四方食事》、《故乡的食物》、《汪曾祺谈吃》等。如果说以汪曾祺作为“吃货”的“典范”,那么至少应该具备会吃、会做、懂得吃这三个标准。
会吃
汪曾祺因生活的轨迹对于家乡、昆明、张家口、北京等地的饮食都有了解,常常谈起某一食物的吃法,能举出各地不同的饮食**惯。不仅如此,他还能说出一种食物最诱人的时候、最适合的烹调方法。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注音:xiǎn)、野鸭、鹌鹑、斑鸠、鵽(duò)、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不仅吃的种类多,吃的地域还广,再用闲散随意的文字描述给我们,所传达的已经不是“口齿留香”能够涵盖的无穷韵味。在“会吃”这一点上,就已经令人望尘莫及。
他还好吃,从他诸多谈吃的文字来看,他简直是吃尽四方的人。从家乡高邮的鸭蛋到北京的豆汁儿,到湖南的腊肉,包括咸菜,酱菜,野菜,他都要追究,琢磨一番。而且时常要发出毫不保留的赞叹: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老头儿汪曾祺》)
除了生嚼,扬花萝卜也能拌萝卜丝。萝卜斜切的薄片,再切为细丝,加酱油、醋、香油略拌,撒一点青蒜,极开胃。小孩子的顺口溜唱道:人之初,鼻涕拖。油炒饭,拌萝卜。油炒饭加一点葱花,在农村算是美食,所以拌萝卜丝一碟,吃起来是很香的。萝卜丝与细切的海蛰皮同拌,在我的家乡是上酒席的,与香干拌荠菜、盐水虾、松花蛋同为凉碟。北京人用水萝卜切片,汆羊肉汤,味鲜而清淡。(《萝卜》)
“吃遍四方”可以说是对于汪曾祺“会吃”的一个最为贴切的评价,而在其文中所展现的不同地域不同食物的吃法,投**的是对中国饮食文化博大深厚的侧面。
会做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那么汪曾祺本人的“讲究”水平到底如何?
如果用专业厨师眼光去看汪曾祺的厨艺,那肯定是不太够的。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坦率地承认:他所擅长的只是做家常菜,“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燕窝,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对于家常菜,汪曾祺则是得心应手。汪曾祺的`烹饪手艺在当时文艺圈子中很有名。所以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外国汪曾祺研究者来北京采访汪曾祺时,中国文联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在汪曾祺的家中就餐。一次一个法国客人来采访汪曾祺,汪曾祺为其做了道盐水煮毛豆。那位法国人第一次吃盐水煮毛豆,竟然连毛豆壳都吃了下肚。
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我给她做了几个菜,其中一个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吃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很嫩,不糠;而且是用干贝烧的。她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萝卜》) 美籍华人女作者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北京,指名要在我家吃一顿饭,由我亲自做。我给她配了几个菜。几个什么菜,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有一大碗煮干丝。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煮干丝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美国有广东馆子、四川馆子、湖南馆子,但淮扬馆子似很少。我做这个菜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国乡情!我那道煮干丝自己也感觉不错,是用干贝吊的汤。前已说过,煮干丝不厌浓厚。(《干丝》) 汪曾祺做的全是家常菜,然而又全是具有中国民间风味的家常菜。汪曾祺说:招待外国客人,并不一定是规格越高越好。因为他们最希望吃的是有地方特色的菜,越是具有中国风味的菜,他们越是难忘。而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能够做好中国风味的家常菜,何尝不是对于传统饮食文化的继承呢?能够将这些感受转化为散文,让更多的读者感受这份文化的传承,也是汪曾祺散文的独特之处。
了解
光会吃,会做吃的还不能算上是个行家,还要窥得“吃”中的门道,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对于一个人的文化底蕴要求较高,而这也是汪曾祺的散文具有“文化”特点的原因。汪曾祺在散文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融入,诗经、古人笔记乃至于中国地域的地方风俗,使得文字总是给人亲切感和共鸣感。
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现在各地植物称作“葵”,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菜”。“采葵持作羹”说白了,就是冬苋菜稀饭……
由此可见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
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注:汪曾祺:《随笔两篇〈葵·薤〉》。)
汪曾祺笔下的食物都不是单独作为个体出现的,总是会与一个事件、一段回忆联系起来,看起来是在谈吃,但细细品味起来,却能感觉到一种时光的流动,从他笔下的各种吃食读者便能知道时光蹉跎了什么,但尽管世事变换,汪曾祺笔下流露出来的那种从容淡然的态度却让人不禁一叹。
舌尖上的汪曾祺
余显斌
1
汪曾祺是个传说,生活在清风明月中。
我手头有本《汪曾祺选集》,不厚,三百多页,在今天这个动辄砖头子厚的书籍朝外砸的时候,这真叫小册子。
一本小册子,让我反复读。
我把它放在床头,晴日夜晚,午睡醒来,都会看一篇:好文章如美食,不能撑开肚皮吃,这是作贱美食,也作贱自己,我不敢。
三百多页文字如一片月光,汪老在月光里喃喃讲叙着,讲叙着生活小事,谈论着生活里的美,让人听了心里一片清净,一片空明。
2
这本书封面是白纸,大半空白,氤氲着一片山气,下角则用线条淡淡勾勒出市井小巷,还有撑着伞走的人。
封面清新淡雅,和汪老文风吻合。
汪老文字很美,那种美不是溪山云谷,也不是千里大川,是一滴清亮的露珠,映着青嫩的草儿;是一声蝉唱,在柔软的柳条里流泻;是一丝雨线,划过彩虹下的天空。
读这种文字,得如古人般净手,焚香。
读这样的文字,会产生古人一样的慨叹,“齿颊留香”,难以忘怀。
我读《受戒》,读《大淖记事》,竟有种面对唐诗宋词的感觉,心,也在语言的细雨里幻化成一朵莲花,清新优美。
他写独守空房的寂静,用珠子零落的声音衬静,“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空明洁净的语言,不沾灰尘。他写吃的,“昆明旧有卖燎鸡杂的……鸡肠子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片。耐嚼,极有味,而价甚廉,为佐茶下酒妙品。”色香辣五味俱全的文字,圆溜溜如同肉丸子。
他的一支笔,能让文字活色生香。
3
别人的语言美是可举例的,汪曾祺的很难,因为他的语言美是与内容美水乳交融的。因此,其书在手,低头皆美,抬头却张口结舌无法言说。
汪曾祺文中人,都是最底层的小人物,可都清风在怀明月在心。其中人物,有朴实的,如小锡匠;有纯净的,如情窦初开的小英子;有灵慧的,如小和尚明海。另外,巧云的刚强,秦老吉的淡然,叶三的敦厚,都跃然纸上。这些人不同之外,都有个共同点:儒雅。
这是作者对失去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这,也是汉文字沁润过的人,对那个古典岁月的怀念。
翻开汪氏文集,有人敲着碟儿,唱着曲子;有人拉着二胡,把岁月的一份无奈和沧桑,化为一缕天光月色;有人提着篮子,走下高高的埠头,把影子倒映在水面上。
他们生活很苦,可很淡然,很美好,把生活过成了一种艺术,这对于今天沉溺于物质世界中的我们来说,简直是一击暮鼓,一声晨钟。
汪老文集中,小说之外,更多的是散文,是小品。在文字中,他营造着一种美,一种优雅美好的生活。
他写的最深入人心的,当是美食小品。
在文字,他津津乐道,说自己发明了一种吃食,名“塞馅回锅油条”,“嚼之声动十里人”。想想,一个老头儿拿一截油条,老顽童一般“咔嚓咔嚓”旁若无人地嚼着,真逗人。
在《昆明的菜》中,他写炒鸡蛋道,“一掂翻面,两掂出锅,动锅不动铲。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写油淋鸡,“大块鸡生炸,十二寸的大盘,高高地堆了一盘。蘸花椒盐吃”。他自己瞪着别人吃,馋得口水淋漓。又写成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了,大吞口水。
他的故乡风物,在他的笔下也清白如水,美不胜收。
故乡的珠子灯,在他的文字里泛着淡淡的“如梦如水”的光;石榴大而红,但必须留着,“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秦老吉的担子“一头是一个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一头是安放在木柜里的.烧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铜锅分两格,一格是骨头汤,一格是下馄饨的清水”,看着就清爽,更不用说蹲下来,吃上那么一碗。
他用素雅的文字,塑造素雅的生活,美着自己,也美着读者。
4
《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有人发帖,如果汪老还活着,总顾问一职非他莫属,由此可见,汪曾祺清新淡雅的文字,已深入人心。
《汪曾祺选集》封面背页,有他的一副老年照片。老人圆脸,一脸慈祥,是个真正的老头儿(这是大家的敬称),也有一种大厨的富态相。
古人道,“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儿,有一颗美好的心,有一双发现美的眼光,做什么不是一样?写文章,写美好的文字,不同样“如烹小鲜”吗?
现在,还有几人真正这样做了?
老头儿写烹饪,更擅长烹饪。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得意地记载,一个朋友吃了他的一盘凉拌海蜇,上洒蒜花。过了很久,对他谈起,仍赞叹说,又脆,又爽口,清淡不腻。
其实,老头儿做的最精美的一道菜,并非他美食小品中所记载的菜肴,而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读后若问口感如何,答曰:青嫩,爽口,“清淡不腻”,余味无穷。
现在,这样的菜不多了,可惜!
汪曾祺:文坛上的美食家
汪曾祺有一癖好与同行不大一样,作家们上街大都爱钻书店、逛书摊,而他却喜欢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
3月下旬,在向作家刘绍棠遗体告别的仪式上,我见到了被誉为“文坛美食家”的汪曾祺先生,遂向他提出了拜访要求。汪老应允。一周后,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正是汪先生。拜访归来后因琐事未能及时成文,不想近日,汪老竟驾鹤西去。
汪曾祺是个平易的老人。他的家特普通,普通得让人不相信里面居然居住着一位当今文坛上的大作家。
他从小就是个背着书包离开家门不进学校的主儿。读大学时,常常只与教授打个照面就开溜。即便人在课堂上也低着头干自己的事儿,到头来,还说朱自清教授讲课讲得不行,太死板,没吸引力,总是抱一大堆卡片读给学生听。
汪老二十岁发表小说。按理他写京剧《沙家浜》之后本该大红大紫,结果红了别人却没他什么事儿。直到他六十大寿之后发表《受戒》《大淖纪事》等一系列小说之后才“火”起来。
《受戒》是写小和尚的一段生活。由于写得入木三分,以致海内外无数读者来信问他是不是当过和尚,连同行们也这样问。他招架不住便甩出一句:没错,我当过和尚。
汪老没当过和尚。但他曾被日本鬼子逼进山中,在庙里住过半年,那是1937年。他与和尚们一起吃过肉,玩儿过牌。当时庙里有大和尚、老和尚,没有小和尚。但他偏偏在小说中虚构了个主要人物--小和尚。
汪老是个很传统的老知识分子。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他始终坚持用毛笔竖写的格式创作。用钢笔横着书写是他刚学会不久的事。他对用电脑创作大为不解,说:电脑弄出来的东西,那版权算谁的?
汪曾祺先生读的书很多,中外古今名家的诗文歌赋、经传野史、笔记杂谈他都喜欢研读、涉猎。他也什么文体都写,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样样都来,样样都出精品。我想,这与他的带有文化色彩的生活不无关系吧。
汪老还是一位地道的现代派画家。他作画一手挥毫泼墨,一手夹着长长的雪茄,一派大家风度。他作画都在晚上,而且必须喝酒。他说喝了酒才来灵感,喝了酒才不拘谨。
这位写小说的高手,对食道也颇为精通。他若与人谈起吃来,会喜形于色,兴致不亚于写小说。他有一癖好与同行不大一样,作家们上街大都爱钻书店、逛书摊,而他却喜欢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他感到这才是人生之乐趣。
汪曾祺对各地的风味食品、名吃、小吃特有兴趣,每到一地总得品尝几样,以饱眼福口福。在内蒙古,他吃手抓羊肉、羊贝子(全羊),吃得很香。同去的朋友问他好吃么?他眉飞色舞地说:“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汪曾祺对中国吃文化既有兴趣又有研究,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史,他都讲得头头是道,顺理成章。在京城,有的饮食文化部门聘他当顾问,有的请他讲授传统的饮食文化。
汪曾祺喜欢喝酒。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曾经喝得烂醉睡在街头,被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派人扶到住处,灌了好些茶才醒过来。汪老几乎每天喝酒,下酒菜倒不讲究,家乡的煮毛豆荚、咸菜烧鲫鱼、熏烧肉、茶叶蛋、家常豆腐、炒花生等都很投口。他一次喝二三两最适宜,喝到三四两话就多了。天南海北、今古奇观、民俗掌故、特产方物无所不包,对在座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倘若再敬他酒,他还喝,不拗。这时施老太就出来劝阻:“曾祺不能喝了,喝多了,伤身体。”于是大家也不再敬了。汪老的酒德、酒品、酒风极好,从不弄虚作假,从不霸王式敬酒,从不以喝酒凌人,定欲置之醉地而后快。汪老喝酒同抽烟一样,从不讲究,国酒、洋酒、黄酒、白酒,名牌、杂牌他都喝得雅兴浓浓。施老太太是汪老的“知心老伴儿”,在汪先生被错划成“右派”的那阵儿,她还想着法儿给汪老买酒,买他爱喝的“老白干”。
写了许多文章,出了不少书的汪曾祺,却没有写过有关酒的文章。我就此问汪老,先生说:“起笔写的时候就想喝酒,喝上酒了就写不了啦!”
汪先生今虽好酒,但酒量已明显地不如当年。先生说:“我现在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时候了,酒量减了一大半,该属于叶公好龙的那个范畴了吧!”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天两顿酒。
汪曾祺喜欢喝茶。但对茶,他却谦虚起来,说自己是个外行。其实汪老也精于茶道,对茶的优劣、茶与水、文人与茶、世界上有关的茶事、茶话、茶趣,他都能侃侃而谈,叫人听得入神。他什么茶都喝,也不讲究。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甚至是湖南用茶叶、老姜、芝麻、米、盐放在一起擂成的“擂茶”,他也爱喝。汪老喜欢浓茶,浓得发苦,一般人是不能入口的。除了在家里以外,他似乎并不带专用茶杯,走到哪儿就喝到哪儿,给人一种亲切、随和的感觉。
汪曾祺喜欢书法,自成一家。汪老的字,书卷气浓郁,每个字都浸透了属于他自己特有的文人气质和情韵。从小他字就写得不错,学欧阳询。稍长,祖父便教他习《中兴碑》《多宝塔碑》,后来父亲又教他临《张猛龙碑》,大学时喜读宋代的四大家。用汪老的话说:“我什么茶都喝,我真、草、隶、篆都写。”的确如此。他在高邮期间,亲故熟友请他写字,他都答应。且喝过酒时写的字更好。汪曾祺非常怀念故乡的食物,这是因为他的家乡江苏高邮有许多美食。远近闻名的高邮鸭蛋质细而油多。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对此评价颇高。虎头鲨、昂嗤鱼和砗螫肉极细嫩,风味绝佳。炒米、焦屑和咸菜慈菇汤这些平民食物用以应急招待客人,或日常食用。野味中野鸭、鹌鹑、斑鸠和,是难得的美味。鲁迅在《朝花夕抬·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汪曾祺心同此感。四十年代初期,汪曾祺在昆明大学所吃过的蔬菜、瓜果也常常成为他四十年后美好回忆的内容。昆明的牛肝菌、青头菌和鸡枞菌味道鲜香,无可比拟。昆明还多产宝珠梨、石榴、桃、杨梅、木瓜、地瓜等果品。汪曾祺一旦想起这些,就想起昆明,想起那一段穷日子,非常快乐的穷日子。1960年前后,汪曾祺曾在张家口沽源县下放劳动。在寂寞荒凉的塞北,他终日画马铃薯图谱、口蘑图谱,他说像他那样研究且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他把在当地采到的一枚大白蘑带回北京,为家人做了一大碗鲜汤,令亲人快乐无比。但细细揣摩,这甜味中又带着多么深的苦味,甚至隐含着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悲怆。
汪曾祺记不同风味饮食,介绍烹饪方法,并不拘泥于食物本身,就事论事,而是能由此及彼,超脱升华,谈吃而又论道。论文化之道,论艺术之道,在美食家中,这可以说是汪曾祺的独见。针对苦瓜难以教人接受、少有人问津的情况,汪曾祺则肯定说,苦瓜也是一道菜,谁也不能把苦从五味中开除出去。联系到文学创作,他主张评论家、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和排斥。在考查腌咸菜和酱菜的起源时,汪曾祺受到启发,谈起文坛曾一度流行的“文化小说”,认为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
清楚各种“洋”节吃什么的同时,别忘记自己的“土”节,那其中绝不少生动和情趣。这种情趣恰恰源自于自己有滋有味的安排和体会。初春的阳光中,汪曾祺先生,七十六岁的老人,真诚地赞叹着春天,创造并享受着自己的快乐。我们深深感动于老人对生活和生命的那份执著,在他的娓娓细述中,感受到来自春天的清香。
“北京人春天吃萝卜,叫'咬春',春而可咬,这两个字很美。人们的口味也与过去不太一样,过去北京人吃春饼,有酱肉丝、鸭丝、豆芽菜、萝卜丝、韭菜、菠菜等。我爱吃春饼。头茬的韭菜现在就上了,'夜雨剪春韭',春韭肥、嫩、鲜香。
“我是江苏人,南方有一些野菜:马兰头、枸杞嫩芽、荠菜就是这个时候。南方吃荠菜馅的春卷,野菜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我所谓”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这是实话,并非故作玄言。现在北京的荠菜是园子里的'春',茎白叶大,颜色较野生者浅淡,无生气。但还聊胜于无吧。北方的榆钱也很好,这个季节河北的莴苣菜蘸甜面酱可以清火。
“到现在我没有什么忌口的,什么都吃,鲜萝卜就可以喝四两酒。北京的小萝卜特别好,现在就上市了,本地的就三四天的鲜。而冬笋炒肉过些日子也没了,这是应季的东西。特级厨师必须有刀功,但我反对工艺菜,工艺菜可以提高价格,于味道没有多少帮助,菜本身要色香味。我对厨师的判别标准是想象力。现在不方便了,我愿意自己买菜,买菜的过程就是构思的过程。”
汪老能做一手好菜,尤其是淮扬菜。由于在北京很难买到做淮扬菜的原料,只好买别的来代替。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起早锻炼的习惯,而汪老的锻炼则是每日一次去菜市场的早市上练“菜功”。
得知笔者也有贪杯小癖时,汪老请我同他一道饮酒。“那样你会看到我的骨子里,文章才会写得真些。”恭敬不如从命,也正合我意。在饭桌上有一道菜引起了我注意,汪老笑着说:“那是早晨吃剩下的油条,把它切成寸段,中间塞入猪肉馅,两头用面糊封好,用油一炸就成啦!外焦里嫩的,佐酒很有意思,尝尝看。”我持箸品尝,味道不错。先生笑着补充道:“你可以回去仿制和宣传,但专利权可是我的。”笑声过后,先生举杯又是深深的一口。
汪老说:“你别看我写了一些谈吃的文章,其实家居中最多食用的是肉末炸酱面。”说到这儿,汪老起身将他的《蒲桥集》送我一册,我双手接过说:“拙稿请您过目指正后再发。”如今,汪老已长逝,仅以此稿慰先生冥福吧!
汪曾祺不仅精通吃经,而且还有颇为精湛的烹饪手艺,擅长做淮扬菜,只是北京难以买到正宗的做淮扬菜的原料,只好就地取材另找代替。《大味至淡》讲了哪些内容?
汪老谈美食,不同于周作人的冷峻和张爱玲的矫情,也不同于梁实秋的一脸吃客相。汪老总是娓娓道来,信手拈来,别有风味地流露出淡淡的文化气味,都是寻常吃话,百读不厌。不过,汪老也不掩饰他的“馋样”。说到吃,旧时最俗的说法是大鱼大肉。汪老既不避俗,又有化俗为雅的本事。
他曾写过《肉食者不鄙》和《鱼我所欲也》,前一篇专说猪肉,从扬州狮子头到云南宣威火腿,其间包括上海的腌笃鲜、苏州的腐乳肉、绍兴的霉干菜烧肉、湖南的腊肉、广东的烤乳猪及全国到处都有的东坡肉等,百余字一段,特色与做法都已说清,颇似清代才子袁枚《随园食单》的文体。
后一篇说了十来种鱼的食法,看了不能不让人垂涎。当然,汪老不仅写过大鱼大肉,还写过很多上不得台面甚至似乎不值一提的食物。《汪曾祺文集》收有十几篇专写故乡食物的散文,举凡虎头鲨、昂嗤鱼、翘嘴白、�花鱼、鳜鱼、鳊鱼、螃蟹、砗螯、螺蛳、蚬子,还有�、鹌鹑、斑鸠、野鸭、鸭蛋,还有马铃薯、马齿苋、雪里蕻、冬瓜、苦瓜、茨菇、蒌蒿、莴苣、荠菜、莼菜、韭菜、萝卜、木耳、香椿、竹笋、枸杞,还有豌豆、绿豆、黄豆、扁豆、芸豆、豇豆,还有茶干、豆腐、百叶、春卷、馄饨、炒米、焦屑……他都写了,写得那么细致,那么动情,一些平时不大惹人注意的食物在他笔下竟都奇迹般活灵活现,顾盼生辉。当然,汪老所写的故乡食物,绝对不是逗人食欲,更重要的是把深藏在读者心底的那种平时不易流露的浓浓乡情也撩拨起来了。譬如《咸菜茨菇汤》描写儿时在冬季下雪天喝咸菜茨菇汤的感受,他在文章的结尾似有意若无意地写下了这样的两行文字: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即使不是高邮人,读了也会怦然心动,黯然思乡。汪老是谙熟食之五味的,而且每每在文章中津津乐道,仿佛为了借助回味无穷再过把瘾。除用散文记述故乡的食物,汪老还在小说中介绍故乡的食事。一篇《八千岁》写满汉全席,在《桥边小说》中写到连万顺茶干制作的讲究,其精通程度就连一些内行人也为之瞠目。此外,使人最感兴趣也最逗人食欲的要数在小说《异禀》中提到的王二卖的桃花了。他说:“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比这个更香的野味。”台湾作家施叔青读了汪老的《故乡的食物》,不禁心驰神往,要求汪老带她到高邮品尝水乡的美味,可惜未能成行。
汪老对中国饮食文化颇有研究,从古代、现代到当代以及少数民族的食事,他都非常熟悉,尤对各地风味食品、名吃、小吃特有兴致。他在南宁体验生活,不吃招待所的饭,拉上贾平凹跑到街头瞎吃“老友面”(酸笋)。他在内蒙古吃没有什么调料的“手把羊肉”和半生不熟的“羊贝子”,同去的人不敢领教,他照吃不误,并且啧啧称赞:“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他说:“我在江阴读书两年,竟未吃过河豚,至今引为憾事。”看来美食家不仅要有好胃口,还要有好胆量。汪老在昆明住过七年,爱吃那里的菌子。在昆明,每到雨季,诸菌皆长,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菌子的气味。比较常见的是牛肝菌。牛肝菌菌肉很厚,可切成薄片,宜于炒食,入口滑腻细嫩。汪老吃牛肝菌的经验是加大量蒜片,否则吃了会头晕。菌香蒜香扑鼻而来,直入肺腑。百菌中,最名贵的是鸡苁。鸡苁生长在田野间的白蚁窝上,菌盖小,菌把粗长,吃这种菌主要就是吃形似鸡大腿的菌把。
在汪老看来,鸡苁当为菌中之王,其味正似一年的肥母鸡,还有过之,因鸡肉粗而菌肉细腻,且鸡肉绝无菌香。汪老注意到,菌子里味道最深刻、样子又最难看的,是干巴菌。干巴菌像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颜色如半干牛粪,乱七八糟,当中还夹杂了许多松毛草茎,择起来十分费事,整个择不出一块大片,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洗净后,与肥瘦相间的猪肉加青辣椒同炒,入口细嚼,味美得让人半天说不出话来。离开昆明四十多年,汪老偏偏总是念念不忘那里的菌子。有回朋友从云南带来一点鸡苁,他便请评论家王干品尝,王干开始不感兴趣,他向王干传授吃法,王干方才津津有味地慢慢咀嚼。后来,王干每次出差去滇,每餐必点鸡苁,临走还带点回家享受。
汪老不仅精通吃经,而且还有颇为精湛的烹饪手艺,擅长做淮扬菜,只是北京难以买到正宗的做淮扬菜的原料,只好就地取材另找代替。这样一来反倒形成汪老独创的风味,源于淮扬,又并非纯淮扬菜,其中巧妙地融入北方风味。汪老闲时常邀三五知己小酌,亲自下厨,菜不过几品,其色香味绝不让名声显赫的酒楼。
1986年,作家高行健陪同一位法国汉学家到汪老家作客,汪老有意以家乡菜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什么菜呢?说出来令人捧腹,大都是当今高邮人请客拿不上桌的菜,比如汪豆腐、三仙汤,更出人意料的还有盐水煮毛豆,即使普通百姓也不屑一顾。但那法国客人见到雪白的盘中堆着碧绿的豆荚,竟忙不迭地连壳一起大嚼起来。汪老微笑着连忙提醒:“这豆壳是不能吃的。”去了壳,那老外越发觉得盐水毛豆鲜嫩可口。
1988年,美国作家安格尔偕夫人聂华苓访华,中国作协应两位客人要求,安排汪老在家设宴招待,并由汪老掌勺。在他的菜谱中有一个大煮干丝,一个干煸牛肉丝,一个炝瓜皮。聂华苓吃得尤为开心,最后端起大碗,连煮干丝的汤也喝得光光的。
台湾陈怡真来北京也要汪老亲自下厨请客。汪老给她做了几个菜,其中一个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事后,汪老解释:“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吃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很嫩,不糠;而且我是用干贝烧的。”这话就像出自一个菜农或是厨师之口的。
有一次,汪老在菜市场遇见一个买牛肉却不会做牛肉的南方妇女,便热情主动地尽了一趟义务讲了一通牛肉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哩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那位南方妇女洗耳恭听,直把汪老当厨师。
作家邓友梅说:“五十年代曾祺做菜还不出名,做的品种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黄瓜,冬天拌白莱,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干丝’和‘酱豆腐肉’。后来我在他家吃过两次‘酱豆腐肉’。”“两次味道、颜色都不尽相同,看来整个五十年代都还没定稿。”我想,汪老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汪老曾把文学创作比作“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可以说,下厨做菜是汪老文学创作独创性的外延,或是又一种形式的曲折表现。然而,把用于文学创作的思路和方法在执笔之余用于掌勺做菜,这才有了不同于常人的创造。汪老曾经赋诗:
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
更是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做郇厨。
每当汪老把做好的菜送到客人面前时,他只是每样吃两口,然后就坐着抽烟、喝茶、吃酒,十分快乐地看客人们吃,我想,那心情肯定如同把自己精心创作的美文奉献给广大读者一模一样。
“文”味识人汪曾祺
语言不过是一种形式或介质,它要去的是――远方。汪曾祺的语言,始终平淡、平常,但在引领着读者去远方的过程里,一路都充满着魔力,既不借助金光美彩的炫技处理,也非彩云出釉的精雕细琢,不过是一条平淡小溪,难得的是溪水里隐着无数棵青草,弯着腰,一路流淌去。路过的人如读者,碰巧看见了,就站在那里,心里顿时有了异样,夹杂了喜悦,却说不出喜从何来。这大抵是文字予人的美好之情。
二十多年过去,还记得《葡萄月令》里所表达的情怀,那种“冬天下大雪,我们什么也不做”的笃定与闲适,特别有底气。
但凡有底气的人,必从容。
文字里的汪曾祺,一辈子都从从容容的,别有静气。老先生的笔下境界,虽不能至,但我们一直心向往之。
汪曾祺就读西南联大时期,在说起李贺诗歌特点时,他打了一个卓绝的比喻,简直出语惊奇:别人都是在白纸上绘画,唯独李贺在黑纸上,色彩当然要强烈。教授用“夙慧”一词形容李贺的敏锐精确。
一个夙慧的人写出的东西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大有机心――即便营造狭小的格局,也会有辽阔和波澜。而这个世上,夙慧的人凤毛麟角,汪曾祺当真是一个。
汪曾祺的东西,代表着一种本味,这是舌头与味蕾最终依恋的一种本源之味,不过一碟平常小菜,不用大火炝,更无须香料的中和。汪曾祺炒出的菜,只放了一丁点儿盐,余下的,全是生活的本质味道。一个人从少年吃到中年,依旧爱惜,是三月田畈沟渠间的水芹,扑鼻的中药气夹杂着袅袅清气,年年守时的宜室宜家。
这几天,在看他的集子《一辈古人》,清清徐徐,祖父、父亲、师友、亲朋……急缓有韵,就像一个慢性子的人养一盆水生植物,一天加点儿水,半杯两盏的,半年过去,葳蕤一片,也是绿意葱茏,把自己都惊喜一下,怎么这么恬淡平和?
年轻时的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没有顺利拿到毕业证,据说是因他不服从学校安排,不去缅甸当翻译,实则他英语也不大灵光,去了也白搭。没有大学文凭,只能辗转到内地来,当个中学教员什么的。要知道,西南联大当年出了多少风云人物呢?相比起来,汪曾祺的人生始终处在逼仄的灰色地带。
然而,他用一支笔,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硬是把自己拉到了一种叫“烟熏绿”的色彩里,并非如李贺于黑纸上作画的激烈,而是略微收敛的绿,有生机的.永不褪色的绿。绿,又太过鲜艳,所以汪曾祺的绿是烟熏绿,有底蕴有厚度的烟熏绿,耐脏的绿。
说起耐脏,有些人的文字还真不经脏。所谓不经脏,也就是经不起时间的打磨,略微放放,就过了保质期――他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添加了大量保鲜剂,乍吃,挺美味的;吃多了,也腻――还是想起本味的好。
我想,汪曾祺的东西,就好在这里,是本源之味。
读《鸡鸭名家》,好像起了个大早,赶到河边散步,回来时瑟瑟,袖着手,什么也没有,倒裹挟了一身水汽。正是那种簇新动人,衬托得人一天的心情游仙一般散淡,也是佛家说的,自己成全了自己吧。
汪曾祺的小说始终弥漫着水汽,似三月的春汛,淡淡地倒映着浅粉桃花,一眼望去仿佛哀愁。这种哀愁感,有可能贯彻着我们的一生,也可能是青春期遗留下来的一沓旧信,在某个中年的晚上不经意地再次呈现,翻读间,整个灵魂被洗礼一遍,恍惚又成了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迫切地动人着……
我读汪曾祺的文字,无从被割伤之感,只隐隐有清气袅绕,甜蜜地回旋,升腾,笼罩着一日三餐般的恒定平常。或许把书放下,你一样投身世俗,瞻前顾后,不错,是俗事――你知道的,就是这等俗事,从不晓得体谅人,只一味考验人,它一日日消耗你,磨缠你,牵绊你,似乎倘若不警觉,小半辈子就倏忽而去了。
去了,也不要紧,一如黄昏,我买一把新割的嫩韭,坐在屋后草坡上,一棵一棵地择,头顶群鸟飞过,四周水杉垂柳,鼻腔里充盈着泥土的腥味以及枯草的香味儿――那一刻的昏暝,十分动人,缠绕心头很久不去,想起来都甜蜜。汪曾祺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夕照时分,最终幻成笔底烟霞,令人安枕,贪恋,一如他小说里的人物田素花焖的甜菜,烂烂的,吃着吃着,叫人有了心思,眼前的河水汤汤起来,这是有远意了。中国的文人,向来集儒释道于一身,进也守得,退也受得。这一守一受之间,就是圆满了吧?王维,苏轼……不都这样吗?
太阳落山了,我拎着一把嫩韭回家。所谓回家,不过是懂得回头,投入到俚俗化的生活――纵然身无别长,却一样释然;纵然心里虚空,也还能想起把汪曾祺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