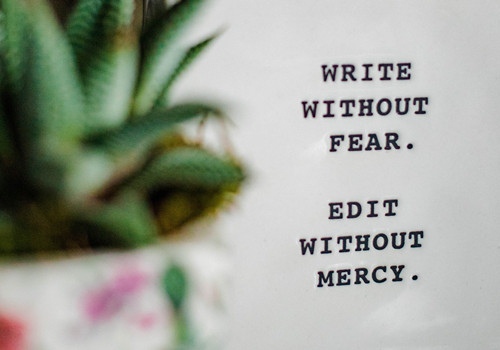
洋洋:莫言老师,欢迎您来到《名人访谈录》。我也知道您这个时候特别忙,也特别累。
莫言:是很累,但接受采访已经成了我的义务,这都是诺贝尔文学奖惹的祸!
洋洋:那诺贝尔文学奖有错吗?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没有错,只是我们国人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错了。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与奥运比赛不一样,奥运会你得了奖,得了冠军,你就真的是世界第一了!但是得了谱贝尔文学奖却不能说你就是最好的,你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有可能一个什么奖都没拿到的,他比你更是一个好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比你的更好,这都不一定。所以对待诺贝尔文学奖不必盲目地迷信。
洋洋:那您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了什么呢?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说明这个作家是个好作家,作品也是值得一读的,仅此而已。
洋洋:在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您认为自己是个好作家吗?
莫言:那当然,我首先是个好作家,所以才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在中国好作家绝对不止我一人。我也不敢说自己就是最优秀的。
洋洋:莫言老师,您太自谦了!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人们每做一件事情必定是想要得到什么,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读了它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那文学作品到底能带给读者什么呢?读者又为什么去读呢?
莫言:我想这因人而异吧!阅读是不能用功利的思维去看,它可以不为什么而存在,就为事受阅读本身。一个人可能仅仅因为喜欢阅读所以就去阅读,一部作品可能会唤起读者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也可能会勾起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还可能会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反省,或者对社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或者让他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所有这一切的感受与体验,都只有在阅读之中才有,不可能是因为有这些感受与体验所以才去阅读的。它不像学习目的那么明确,为了考文凭、评职称、或者为了找份好工作,它就像是看场电影,消遣、娱乐、寻找精神的慰藉,看之前可能对影片一无所知,看之后才有了对影片的观感。
洋洋: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都表现得很极端,比如对历史人物好与坏的评价,或是传统文化的要与不要、再或是文学艺术的崇高与一文不值,真可谓要么捧上了天,要么踩在脚下,哪里还有理性可言?
莫言:纵观中国的.历史,这些非理性的极端声音的确是存在的,而且甚至某段时期内,它会成为一个社会主流的声音。但是不可否认,一个社会的全部声音里,一定有理性声音的存在,当然也会有非理性声音的存在,不过随着时间的积累,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我想最终一定会接受理性的声音。如果把非理性的极端思想比作是某个疾病,我们的祖父、父亲,加上我们自己,三代人有可能会得同一种疾病。虽然祖父的病已经治好了,父亲的病也已经活好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会得这个病。
洋洋:那人类的经验时后人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莫言:我们不能因为三代人得了同一个疾病,就否认经验的作用。我想历史经验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面对历史经验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贤臣告诫君王以史为鉴,但贤臣被杀,君王残暴不仁,最后弄得国破家亡的例子不在少数,这难道是历史经验没有作用?这只能怪君王昏庸无知吧!
洋洋:可以与我分享一下您满意的事吗?
莫言:噢,比如我拿诺贝尔文学奖就很满意啊!
洋洋:是不是不管内心多么强大、多么坚定的人,都希望能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喝彩?
莫言:应该是的吧?一个内心足够强大自信的人,他可能会不顾周围人的反对,执著地坚持自己,这个时候他可能不会去想要鲜花掌声,但是当鲜花掌声来了,他应该会高兴的。
洋洋:有没有拒绝鲜花掌声的?
莫言:当然有,当鲜花掌声是糖衣炮弹,那就一定得小心,能拒绝就拒绝。
洋洋:这就是佛教中的大彻大悟吧?好的,莫言老师,谢谢您!
我正在执行一个特种任务,就是回到古代采访我们领导最喜欢的诗人——陶渊明先生。当我直接到达陶渊明隐居的茅屋的时候,忽然遇见一位小孩,那位小孩正在念陶渊明先生的
忽然一阵龙卷风,把我卷到鲁迅家中,鲁迅先生正在专心致志地为党献出他的一份力量。看他严肃的神情,再看看我手中的手表已经12点多了。时光机的能量快耗完,为了抓紧时间,我不好意思的走进鲁迅先生书房里,鲁迅先生还没察觉到我的到来,我看到他桌子上放了许多写完的书稿。我低声的对他说:“打扰你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迟疑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说:“没什么的。懊!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书房里?”说完,他急忙地把一张又一张的稿纸藏了起来,我惊讶地说:“尊敬的鲁迅先生,我没有恶意的,我是从21世纪来到这里的',我是一名记者,想采访您一些问题,鲁迅先生您本来是投身医学,希望以此来救治中华子孙们,但你为什么又弃医从文?”鲁迅先生涣然大悟的笑了笑说:“因为我发现我们中国人们身上不止是病痛,而是人的精神,所以我弃医从文。”我摸了摸脑子,又说:“请问您告别医学,投向文学,是否是一种胆魄?谈谈你对告别的看法?”顿时鲁迅先生的肚子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空城计”。他又严肃地说:“这并不是一种胆魄,因为我想用笔尖振兴中华民族。我的告别是想追求属于自己的理想。许多人的告别也证实了它的魅力所在。时光机发出了一阵阵的警报声。我急忙向鲁迅先生告别,他还送了我一本书《朝花夕拾》。
经过这次的采访,我受益匪浅。让我懂得了人生自有几时乐,不如回到古时乐一回。
在这些天中,在我的心里,一直挂念着北京外国语学院,新闻系的那个女孩晓颖,和她写的那篇采访我的文章。
我曾在电话里询问过她几次,那篇采访我的文章的写作情况。她说;“正在修改中呢”。
而到现在,已是近一个月了吧,有句话叫文章不厌百回改,我想,她写的这篇文章一定是一篇流芳百世,千古不朽的作品呢。
我记得她采访我的那天是17号,而且是刮着大风的天气。在前一天她就来找了我一次,没有找到我
。因为我看到天气刮着大风,不能摆书摊,就回到宿舍休息去了。上班时,我收到了前台的服务员小李给我递来的纸条。是晓颖给我留下的电话。我便给她打了过去。于是,我们便约好了第二天我接受她的采访。并且约定了在陶然亭公园门口见面。
第二天中午,下了班,我提了一箱书,来到了公园门口,风仍然刮得很大。不一会儿,晓颖过来了。她的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带着一副眼镜,肩上挎着一个手提包子,还戴着一顶遮阳帽。
我们见了面后,互相做了
原来我是想和饭店里的领导说一下,在饭店里采访的。但我又想到了陶然亭里有一个李大钊故居。我前几天参观过,我想到那个地方能避风,也安静。于是,我和她便向那个地方走去。为了找到近一点的路,路上我问了几个行人的路向。
在向李大钊故居走时,风仍不停地刮着,晓颖边走边问我一些问题。忽然,一阵风把她的帽子,
刮到了路边的草丛里了。她走过去,捡了起来,抖了一下土,放在了包子里。
我们来到李大钊的故居的时候,才发现,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已到期闭馆了。我推了一下门,门也上了锁。
我便和她在公园里,左拐右拐的来到了一个写着兰亭序的地方。我走到了一个有大门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儿比较避风。于是我们便决定就在这儿接受采访。我看到牌子上写着四个字“群贤毕至”。由于第一个字是繁体字,我不认识,问了一下晓颖,她说;“是群贤毕至吧,我看到前面写着兰亭序”。
我于是把书拿了出来,摆在了铺开的报纸上。她也放了一张报纸,坐在了地上。她边问我话,边记着笔记。
还不停地用照相机拍摄着。旁边还放着一个小录音机。我把我能回答的都说了出来,以帮助这个女孩写好这篇文章。
过了有近一个小时,采访完毕后,她送给了我一个书签,她说到;“她的文章,可能只能在校园里传阅一下,还不知能不能登报”。我说;“登不登报没关系。现在,你正好练习写作。我也是想帮你一些忙,只要努力,认真写就行。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你向其他报社记者推荐发表一下”。
之后,我给了她一些我写的诗稿,和报道我报纸的复印件。我们收拾了书向公园大门走去。
我边走边对她说;“你家中弟妹几个”?她说;“只有我一个”,我说;“原来你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呢。如果你的.父母知道了,你今天刮着这么大的风出来采访,受这么大的罪,肯定会心疼你呢"。她说;"没事,以后要当上了记者,还要经历更多的风雨呢,这不算什么"。我说;"你真坚强啊"!
这时,风似乎比以前更大了,吹得我们竟然走不动了。风小了点后,我们来到了公园门口。
我给了她我的地址。她说写好文章会给您送过来,就离去了。
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很是佩服。我觉得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坚强,
自信,勇敢,活泼开朗。对困难无所畏惧。而这正是我一生都在想学到的品质。同时,
我也想到了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为师生们做的一个即席演讲;”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
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注脚下的事情,他们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经常的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想到了这几天,这些女孩们做采访报道时的勤奋与努力。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是啊!我们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