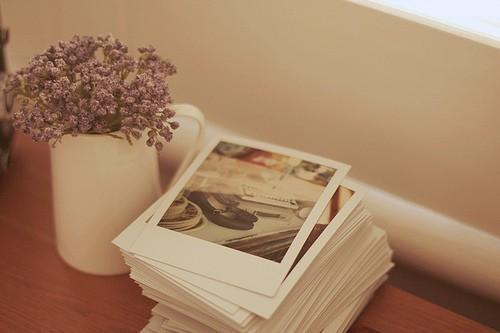姨侄打来电话说***也就是我二姐要从风景如画的江南回来,而且就在今天夜里。我心里一边担心病中的姐姐是否承受得了路途的劳累?一边嘱咐她多加点衣服,因为入冬后家里这几天很冷。放下电话后,我的眼泪一直在眼里打着圈儿,可我还是忍住了。
明天又是冬至了,往年这天给已故父亲烧纸钱都是我跟二姐一起去(我们这里的风俗,冬至烧纸钱意思就是给已故亲人送寒衣),而今年,我不知道二姐是否还能跟我一起去上坟?我不知道二姐还能跟死神挣扎多久?我多么希望死神能跟从小就胆小的二姐擦肩而过,毕竟她还是那么的年轻。
二姐病了,这场病让胆小的二姐惊慌失措,心智大乱,小血管癌,在谈癌色变的今天,姐姐怎能坐怀不乱?当医生告诉她不敢轻易动手术时,跟我在视频里哭的梨花带雨,而我却在她的哭泣声中不敢打开她那边的视频。因为我多么害怕我会忍不住跟她一起落泪,而作为她的亲人,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因为我要用我的坚强去安慰我可亲的姐姐,我要用我的安慰带给她心理上的镇定,我一遍又一遍的告诉姐姐,人,其实从一出生就要面临着有一天我们会走向死亡,我们都会死,只不过看死神对你的态度,以及你自己对死神的态度。我告诉她我们已经故去的父亲,在世时对死神的看法,他说,人,其实就像我们吃的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割了,一茬一茬接着生长,如此循环,生生不息。死,其实并不可怕,怕只怕死之前病痛对人体的折磨,那种生不如死的疼痛才是你心里最深的恐惧......二姐的心情,似乎在我的胡言乱语里渐渐平息下来,告诉我她在化疗中面临的痛苦,对人生的重新感悟,以及对以前种种纠缠不清的道理现如今看法。我无声地关掉了视频,拥在老公的怀里,哭得一塌糊涂,因为我多么不想再失去一个亲人,我多么不愿意像几年前失去父亲那样,再失去一个我可亲的姐姐,我再次感觉到了死神的可怕,因为它对于每个人是那么的无情......
站在父亲的坟前,我们姐妹几个一起给父亲焚烧着纸钱,二姐终因身体虚弱未能前来,所有的一切只能有姐夫来代替,我心里一阵难过。大哥的嘴里一直对已故的父亲诉说着,让父亲保佑二姐能够度过这场劫难,还原姐姐头顶上的那片蓝天。而我跟姐夫早已难过的无语凝噎,我想,假如父亲真的'能够泉下有知,他一定不想他的女儿有任何闪失,因为父亲在世,就一直担心他这个在外漂泊的二女儿。
大哥家门朝西的厨房间里真的很温暖,太阳光一直暖暖的照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亦不知道是不是屋子里被我们兄妹多人拥挤的原因?大嫂忙碌着准备晚餐,已近60岁的她,脸上始终绽放着如花笑靥,她的热情让我们感觉她如母亲般可亲。六哥买菜去了,我则忙着为姐姐买的小鱼去鳞,大姐忙着烧火,母亲则和二姐在一边唠嗑,其余的人站在外面晒着暖洋洋的太阳,这种场面,我们都觉得有点奢侈,因为自从我们兄弟姐妹结婚后,除了父亲故去那天聚的这么齐,好久没有这么聚过了,我不知道,像今天这种场面还能持续多少次?
晚饭吃的很快,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只知道母亲坐在二姐身边,看着女儿把一碗玉米面粥喝光后,高兴的使脸上的皱褶都拧到了一块,而我则悄悄的抹去了眼里的一丝泪滴,因为或许只有我知道,二姐勉强喝的那一碗粥,只是想让我们已83岁高龄的母亲放心,她没事。
姐姐要回去了,大哥手里拿着我们姐妹几个凑得几千块钱交给姐夫,姐夫一步一步的退着,躲闪着不要,因为毕竟这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哪个家里都不容易,况且大哥也已经60多岁了。姐夫一声声的推脱着,诉说着姐妹几个来钱的不易。大哥声音哽咽的说:“钱不是给妹夫你的,是给我妹妹的,给你只是想让你好好的照顾我妹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拯救妹妹,只能这样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这也是我们姐妹几个能做的唯一办法,毕竟今世能有缘做姐妹不容易。”母亲这时走到二姐的身边,“丫头,你们姐妹八个都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把你们从像小猫那么大点一个一个养大成人不容易,今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们当中一个先离我而去,不准你们当中一个给我活到半途掉队。”说完就出去了,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流泪,只知道母亲始终没有再回到我们当中来。而我们在母亲的话语里久久沉默,谁都没有开口,大姐用手使劲的揉了揉眼,好像眼里积满了沙子。
二姐哭着坐上车走了,我们姐妹几个还在商量着怎么拯救姐姐,一如当年我们怎么拯救父亲那样,商量着如何跟死神来个殊死搏斗?可我们终究不知道对死神给我们的这道命题,我们该怎么去把他解开?我始终在想,假如用金钱和亲情的爱能够让死神望而却步,我们一定一点都不吝啬的随时奉陪。可死神,你能让步么?
篇一
尊敬的各位前辈:
今天,诗词、楹联界的各位前辈欢聚一起,庆贺我的老父亲八十寿诞,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向各位前辈鞠躬了!我的老父亲是一位在教育战线劳作了数十年的辛勤园丁,岁月的流转记录了他老人家曾经的沧桑,时空的变幻见证了他老人家的辛勤的操劳。在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他和我们的母亲含辛茹苦,相濡以沫。如今,他们虽然已经
对于楹联,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今天,在诸位前辈面前,我尝试着做了一副对联以表达我对在座各位前辈的感激与敬仰之情:曲水流觞,唱酬间,演绎现代诗坛佳话;清风明月,宴饮中,激励后学圣贤文章。
最后,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谢谢!
篇二
各位亲朋好友,各位来宾:大家好!
玉兔当班增百福,春风送暖赐千祥。今天是公元2011年2月9日,农历大年初七,我们迎来了家父八十华诞的喜庆日子。在此,我谨代表所有的亲朋好友,祝愿父亲增福增寿增富贵,添光添彩添吉祥。
父亲出生于1932年(民国21年),风风雨雨八十年。阅尽人间沧桑,历经磨难坎坷。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和社会历史的大变迁。父亲出生于书香门第、教育世家,自幼聪颖好学,青年时期不辞辛苦、远游求学。于1951年投身教育,兢兢业业四十余年,退休后又被村委返聘任教十余年,为班沟村的教育事业奉献余热。母亲去世后,父亲更是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在祖父母和众多亲友的帮助下,抚养子女长大成人。艰难的岁月练就了父亲乐观平和的心态,战胜困难的勇气。历尽磨难痴心不改、经历曲折矢志不渝。几十年来为国家教育事业奉献青春和晚年。如今桃李满天下,众多学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们姐妹三人都已成家立业,子孙后辈都在各行各业为社会做贡献。
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家庭里的优秀子女脱颖而出。有朝气蓬勃、志向远大的空调技师孙子宋养扬,温柔美丽、
父亲一生勤劳俭朴、宽厚待人、善解人意、和睦相邻,到老年仍笔耕不辍、不停劳作,品德高尚、德高望重;孝敬父母、爱国忧民;进德修身、克己奉公;淡漠名利,节操正气;求真远志、谦恭礼让。至今仍在为班沟村的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为抚养子孙后代不遗余力,回报社会无怨无悔。
如今父亲八十高龄,持家有方、尊老爱幼,良好的家风代代相传。子孝媳贤、四世同堂、膝下承欢、宽厚仁慈、福寿无边,父老乡亲众口皆碑,天伦之乐、安度晚年!
父爱如山,厚德载物;父爱如海,容纳百川。祝父亲福寿无边,幸福永远!祝各位亲朋好友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在此我代表各位嘉宾向家父送上最真诚、最温馨的祝福!祝父亲健康长寿,笑口常开!谢谢!
篇三
各位长辈、兄弟们,各位老师、同学们,各位来宾:
大家好!今天是我父亲八十大寿的喜庆日子,谨让我代表我们兄妹及其下辈21人,祝愿各位长辈和我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愿各位同辈生活幸福,万事如意;祝愿下辈身体健康,快乐成长。 我父亲1950年起就在丁庄从事教育工作,到80年退休,前后共在丁庄教学22年。期间栉风沐雨,饱经沧桑,虽有千言万语,亦不能尽诉。他和故去的母亲一道历尽千辛万苦共同抚养了我们兄妹5人。如今我们均已成人,期间,我们家得到了各位亲友的不少帮助,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记得:在靠工分吃饭的岁月,我的二叔、二大娘家没少给了我家出力出工,给缺少劳力的我们可为雪中送炭。我们记得:分田到户后,先富裕起来的'三叔、四叔家没少给了我家物资上的支援,让依然贫困的我们度过难关。。我们记得:在外工作的五叔无时无刻地不在关注着丁庄所有亲人的成长,是他伸出无私的双手,让在农村的我家、二叔、三叔家从中受益,得惠至今。三位姑家在自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尽力帮助着我们大家。正是前辈们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尽心相助的言行,告诉了我们什么叫一奶同胞之情,什么叫兄弟姊妹之义。请让我代表我们兄妹向叔叔、婶婶、姑姑说声:衷心感谢您们对我们的教导和恩惠。我们记得:三老爷家的叔、婶们和二大娘的兄弟们,只要我家需要帮助,您们往往都是放下自己的事情前去相帮,从不推托。还有所有的邻居、亲戚。不论是石泉庄的外祖父家,还是韦寨马亭、张庄的大姑家、二姑、三姑家;不论是管村、林洼我和大哥的岳父岳母家,还是二叔、三叔那边的姐夫、妹夫家,都能做到宽和为本,亲情为重;都能做到一家有难,大家支援。正是您们朴实善良的品格,让我们父母感到舒心的同时,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久长的温馨。使得我们这个团结的大家庭平安和睦、美名远播。为此,请让我代表我们兄妹说声:衷心感谢您们的真诚帮助,感谢您们为我家所有的付出。我们更记得:在我们筹办父亲八十大寿之际,我父亲30多年前的同事们(也是我的恩师)和学生们主动联系,协助筹划,今天并亲自到家祝贺,这让我们全家备感荣光,这充分彰显了中华传统中“尊老敬敬师”的美德,彰显了我们丁庄人质朴、善良的品德,更彰显了您们重义轻利、知恩图报的性格。 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让我们的情谊永远传递下去,并发扬光大。此情此景,此地此义,所有这些怎能不教人敬重,怎能不让人感谢。在此,我再次向今天前来祝寿的所有长辈、平辈,向我的老师、学长们说声:谢谢!
各位长辈、兄弟们,各位老师、同学们,各位来宾,我父亲风风雨雨80年,历经磨难,他和我母亲一生中积累的最大财富就是勤劳善良的朴素品格,就是宽厚待人的处世之道,就是严爱有加的朴实家风!这一切,伴随他们经历的坎坷岁月,伴随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已深入我们的骨髓,而且这笔宝贵的财富已经渐渐被我们晚辈所继承,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感到特别地满足,感到特别的幸福。
最后,请让我们满载着祝福与希望,祝我父亲生日快乐!祝在座的亲朋好友,在未来的岁月里――天天开心!事事顺利!
从从家乡村口向南望去,崇山峻岭的前端,一个半山窝里,就是外婆曾经所住的村子。从家里出发,走两公里平路,到山脚下,再走大约四公里山路,就能到外婆家。去的时候,山路是曲折的上坡路;回来的时候,就是下坡路了。曾经,这条路每年都有走好几次,路边有什么树木石块,走多长拐弯,现在都一清二楚。但距上次去至今,已经有七八年了。这个村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终的结果就是,村庄消失了。
表哥和表弟从外地回来,和我相约去他们的故乡看看。车很快就到山脚下,再上驶八百米的山路,有个岔路口,右边是通往另一个村的,左边是通往他们的故乡也就是我的外婆家的。左拐上去,行驶不到二十米,只见茅草和灌木侵袭了这条山路。看上去,步行应该勉强可以,但车是肯定通不了的了。
那本是一条“之”字形曲折蜿蜒的山路,不到三米宽,路面坑坑洼洼。往常,主要是行人、自行车和摩托车通行,偶尔也会有汽车去村里。我姐夫就曾经开着小货车去过几次,他说每次去都心惊肉跳。
过去的那些年,我每年都要去至少两次。春节去外婆家拜年是传统节目,暑假期间一般也会去一次。每次去都是骑单车,单车上会放点东西。每次到了山脚下,小歇一会,深吸一口气,然后弓着身推自行车,踏着路面的碎石,艰难前行。中途休息几次是难免的,我经常会鼓励自己,再多走一会,走到前面那个转弯处再休息。到了山顶,也得坐一下。喘着气,吹着山风,极目远眺,望着四周连绵的山脉,倒也别有情趣。也有不快的事,大多数时候,到了山顶,都会内急,只得找个地方排解一下。老家常说累出屎来了,大概就是我这种情况吧。
我每次去,其实几乎空手去的,带的礼物不重。即使这样,每次都累得半死。小时候,去外婆家不是美差,尽管每次去,外婆、舅妈都会拿出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吃不完还能兜回家。我非常钦佩村里的那些壮年男人,单车后面背着两袋化肥,仍能健步如飞,中途也不歇一下。
但现在,即使这样的路,也只能留存在记忆中了。我和表兄弟各执一根木棍,拨开两边的茅草和树枝,不时还抽打一下。因为表弟开玩笑说,如果旁边窜出一条蛇或其他动物,肯定会把我们吓得半死,因此我们得先把那些潜在敌人惊扰开。尽管时隔多年,山路已被植物侵占,但那些标志物还在,比如路边的那几棵大树依旧健壮,比如那几个拐弯依旧提示着我们山路还有多远,再比如站在一个拐角处还能看到山下的房屋与河流。只是行进速度比以前慢多了,而且没地方休息了,但我们一路说说笑笑,倒也很容易消磨掉时间和疲劳。终于到了山顶,眺望着远处的群山,感受着凉爽的山风,舒畅之情难以言表。我们都在城市里打拼,像这种情形,几乎不敢奢望。我也经常去爬城市的山,但不会有现在这种感觉。
山顶离村子还有五百米左右,其实走一百多米,就能看到稍低处的村庄了。只见树木草丛中,只有小舅的砖屋依然屹立,其余的房子已经倒塌了,包括外婆和大舅曾经常年居住的房屋。断墙和梁木掩映在青草之中,一片萧条衰败。村前的梯田,是外婆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基础,如今长满了茂密的草木,与周围的山坡相连,已经看不出哪是良田哪是山脚了。但是村里的标志,外婆屋后那棵高高的棕榈树,似乎更加青翠,更加挺拔。这棵棕榈树,小时候我们经常爬,爬得树干光溜溜的。
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有些伤感。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真真切切看到这一幕,还是有点无法接受。尤其是表兄弟,这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数次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就在十年前,他们还称这里为“家”。即使在外定居,成家立业,每年回到这里时,他们还是说“回家”。现在,家,确切地说是家乡,已经不在了。我们离开这里后,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清明节可能会上山拜祭先祖,但先祖的墓地都在山的另一边,不大可能翻山越岭拐过来凭吊消失的故乡。
这个村庄因为在半山腰,有个很有意味的名字“半岭”,“岭”是家乡话对山的称呼。“半岭”是个自然村,自我懂事起,村里就只有十二户人家,五十来个人。村子很小,只有一条路通往外面,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进了村子,村里的人都能知道。村子小,关系就相对简单,村民热情淳朴。几乎每个村民都认得像我这样的客人,而我也认得每一个村民。平时外村人较少来,过年的时候就热闹很多。每年正月来拜年,最害怕而又最温馨的就是吃饭,总是被横拖硬拽地拉到各家吃饭。往往在一家刚坐下,另一家主人就在旁边站着,拿起筷子吃了一口,下家立马捉住我的手,把我拉起来,大声说“可以了可以了,去我家吃。”而这家则把我按住,往我碗里夹菜,嘴里生气地说“都没吃,吃几口再走”。看着他们争来吵去,我就慢腾腾地吃着。经验告诉我,千万别贪吃,否则到后来的几家根本吃不下去,这样会使主人不开心,以为厚此薄彼或他家饭菜不好吃。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吃了八顿,撑得走路都困难。小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躲起来,到饭点的时候才回到外婆家。但稍微长大了,就躲不了了,他们都必定要找到我才开饭。这种场面,只有这样的小村庄才会发生,较大的村庄,亲疏比较分明。
温情和淳朴是可贵的民风,但穷困才是村里最显著的特征。虽然村小人少,但农田也少,且不好耕种,都是积年累月从各个山谷里开辟出来的耕地,土地小块分散坡度大。就算我两个舅舅家劳动力多,辛辛苦苦一年从头忙到尾也仅仅糊口,难有积余。随着社会改革的来临和深入,平静的山村被外面的动静打破。
我也不知道这个村庄是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但却是看着她慢慢消失的。村里人口顶峰就是五十二人,那还是我小时候,后来就慢慢减少。因为生产、生活极为不便,村里的姑娘想方设法嫁出去,虽然也会有更偏远的山村嫁进来的,但出去的明显比进来的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开始,因为迁移的松动,村里有条件的家庭会迁往山下平地村落居住。而年轻人外出打工,小有所成后更不会回到这个山村。本世纪开始,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始,县里面通过资金补助的方式鼓励落后山村的村民搬迁到条件更好的平地村庄。这种政策加快了“半岭”的消亡,小舅的砖屋才建几年,他也义无反顾地搬下山了,村里剩下的都是不愿离开的老人。到2003年,随着其他老人故去,村里其实只剩下了我外婆,还有轮换上山照顾她的两个舅舅、我母亲和姨妈,很难想象两个人住在一个山村里的感觉。
八十多岁的外婆依然健硕,她甚至还在村前的地里种了几亩菜。由于进出的人极少,农田、村路逐渐长起了茅草和灌木。要是以前,村里人会很快铲除,但此时已经没人理会了。小山村向原生态迈进,连野生动物也回归了。好几次,野猪跑到门前的菜地里,把菜地拱得乱七八糟。舅舅到山下找了个猎人,试图教训一下野猪。他们确实守到了野猪出动,但没有命中过。外婆他们甚至在晚上听到了久违的狼的嚎叫,他们自己都说三十多年没听到过狼叫了。野猪和狼,我久闻其名,但至今未见过真身。
每到傍晚,外婆会坐在门前,望着山下。从这里,透过眼前的松树杉树,可以看到山下的村庄,也可以听到山下的人的喊叫和牛的长哞。过去的很多年,村子里也不时地想起这些声音,在四周的'山里回荡。但最后几年,村里没有了邻居,没有了猪牛,没有了鸡鸭鹅,只有太阳依旧在上午艰难地越过村后的高山垂照下来,而到傍晚穿过树林斜照着村里的每一块地方。山下传上来的喧闹更显山上的寂静,而很快,寂静将进化为死寂。
2006年底,经不住子女们的劝解,外婆还是下山了。村里最后的坚守者撤离了,半岭,这个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村庄,彻底的消失了。
不仅仅是“半岭”,还有很多类似的山村因为类似的原因消失了。“半岭”所属的大村,原本有六个自然村,分布在不同的山腰或山谷,现在只剩下村委会所在的村子了。甚至,2005年,那个大村的编制也撤销了,并入到我家乡所在的大村。据说,降格后的那个大村,现在也只有很少的人家在那里居住,相信也很快就会消失。
对于这种自然有意识的村庄消失,我是持正面立场的,他们应当搬迁到更适合的地方去住,就像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的路上常愿望的:要是外婆家在平地多好啊!当然这种零碎搬迁同时也破碎了几百年延续下来的亲情和乡情,不过这些亲情和乡情在更好的生活面前不堪一击。而且,到一个新的地方,融合进去,也会产生新的亲情和乡情。从山村到平地,从平地到乡镇,从乡镇到县城,从县城到城市,这是我在读书时期就形成的一个改善农村面貌、提升农村水平的路线图。只要条件允许,就应鼓励农村居民向更高一级的空间迁徙发展。让我欣慰的是,这个路线图正在实施,尽管有些人在慨叹中国村庄的消亡速度并引起关注,但谁又能阻碍这个进程呢?
我会时常想起那条通往外婆家的山路,也许过些年再去重走时,那条路已经完全被植物覆盖了。没有人走,路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