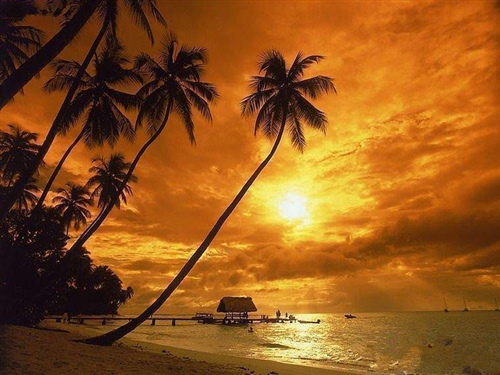从小最爱历史,最大的梦想就是到北大历史系读书。到了大三,确定自己的兴趣还在历史和新闻时,就立志要报考刚刚成立的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其实考研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去北大游学的理由,大三大四那两年,我上午在北航上计算机的专业课,中午吃完饭,就骑着一辆破单车沿五道口、成府路一路骑到北大,旁听各种人文社科的课程。除了新闻传播学院的课之外,历史系、社会学系、中文系、政治学系、哲学系的课堂均出现过我的身影。
在那两年的游学生涯里,我跟北大的很多同学成为了好朋友。那段时间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历史系的阎步克老师和中文系的陈平原老师。阎步克老师在喧嚣尘世之中独守精神家园的`坚毅让我感动,他严谨的治学和考证态度成为我毕生的为文原则,我之所以发条微博都要注明出处,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影响。每当我在俗世之中想放弃理想的时候,一想起他纯净清澈的目光,我就有了坚守下去的动力。而陈平原老师的肆意和潇洒风度也让我明白,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即使清贫,也要有自己的操守,自得其乐。
工作一年后,我成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一名正式学生,圆了自己的北大梦。三年时间里,我一边学习,一边在《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做财经记者,赚学费和生活费。CCER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摆脱文科学生容易出现的书生意气,以为靠一支笔就能指点江山。无论是北大先校长胡适推崇的“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还是CCER灌输的计量理念和宏大视野,为我的新闻工作,乃至现在的经济调查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CCER,印象最深的老师是陈平、汪丁丁和卢峰。我的
到新单位后,不管到哪里,领导对我的介绍都是“北大的高材生”,这让我很尴尬。其实,每个学校都能培养出好的人才,一所好学校,能给你带来的只是好的氛围和更便利的成长条件而已,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阿马蒂亚森说:“每个社会人都具有多重身份,那种把个体身份单一化,进而以这种单一身份相互之间的差异为理由鼓动暴力和冲突的行为,都是不符合理性和实际状况的。”这对于标签化盛行的中国或许很具参考意义。
所以,我更敬佩那些在普通环境下顽强向上生长的人。大哥兼好友段德峰,中专毕业后工作了好几年,做过保安,后来通过自学,成为北大法学院的研究生,进而成为《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的主要创办人和骨干之一,从媒体转型后又创业从事社会公益工作。好友邢梅,在北航英语系自考,从大专到本科,后来又考上南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到新华社下属的报纸工作。如果不是跟他们深入交往后,你很难想象他们勤奋、坚守的毅力和勇气。幸运的是,我的生命里,还在继续出现这样的人:生活在精神文化环境贫乏的小地方和相对一般的学校,但却不断吸纳各种精神养分,并在世俗的压力中坚守自我,不断成长,最终成为绚烂之花。他们是我在社会大学学习的榜样。
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
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他们的孩子都该考大学了。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写报社论写多了吧,这么高的调子。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从大学开始,就自称是“北大的跟屁虫”。对北大人甚是敬重。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传言,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手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经历秋雨洗礼,北京大学校园朗润清新。昨天上午,3000多名大一新生在操场上席地而坐,参加开学典礼。北大校长王恩哥寄语新生: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入学第一课,校长会说什么?好奇的新生得到了恩哥简单又真挚地祝福:做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人。
王恩哥说,北大是精神的乐园,自由的乡土,但首先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知的最高学府。你们历经十余年的.辛苦来到北大,千万不要辜负了这大好时光,要利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吸收一切有益的养分,多去图书馆、多去自习室、多去体育场,不断健全自我的智识,不断丰盈内心的世界。
王恩哥还给新生留了两道作业题:为何来到北大?又将以怎样的身影告别北大?他提醒新生:在燕园的几年,同学们不仅要认真研究怎样做好学问,也要思考如何立身做人;不仅要恪守学术道德,也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用心去慢慢沉淀和培养一种为学和做人的高贵品位;不仅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也为他人、社会和国家发出印有你们标记的一份热度。
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刘震云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开学典礼上。这位35年前的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告诫在场的新生:进了北大并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证明你有好脑子。他建议学弟学妹:在北大,要锻炼自己眼睛的宽度,还要锻炼眼睛的深度,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近些年来,我也听到一些对于母校的闲言碎语,我听到的时候首先不是愤怒,而是想到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兼容并包,北大应有胸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以校友的身份诚恳地拜托在场的学校领导,共同擦亮北大的眼睛,共同擦亮北大这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