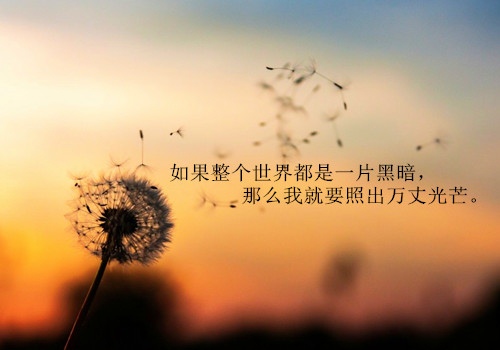1。 煮面炒面,口感还是面正好。
2。 实惠客留香,源自面正面。
3。 好面面正面,好吃天天见。
4。 面香汤更香,吃面别忘喝汤。
5。 面正面馆,管你好吃。
6。 好吃就是面正面。
7。 面品万千,正面更鲜。
8。 正宗好面,营养香传。
9。 一碗好面,正在等你。
10。 面面俱正点,条条皆好吃。
11。 根根面正,缕缕传情。
12。 面正好味来,营养更健康。
13。 营养面,健康面,面面俱到。
14。 优质面材,独领香韵。
15。 好面面正面,百吃都不厌。
每逢身体稍许不适,就餐的时候,意中就会选择面条或者砂锅,当然了,要配一盘酱炒鸡蛋。吃面条用酱炒鸡蛋佐餐是意中的首选,吃砂锅米饭配酱炒鸡蛋却有可能只是意中的个人癖好。
说起酱炒鸡蛋,意中想解释一下,许多人吃面条佐以鸡蛋和酱是很正常的事,但应该注意的是,此酱与鸡蛋非意中所言酱炒鸡蛋。一般饭店供应的面条卤是鸡蛋炸酱,虽然里面的鸡蛋不少,但依然是以酱为主的。而意中所说的酱炒鸡蛋,绝对以鸡蛋为主。而所谓的酱,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烹制好的酱炒鸡蛋,基本看不到酱,只是在吃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出一丝酱意。意中以为,酱能够起到舒缓胃的作用,且效果极佳。
说起酱炒鸡蛋,在意中的生活里,应该是从酱油炒鸡蛋衍生而来的。第一次意中自己炒菜,第一盘就是炒鸡蛋。那时的意中刚刚上小学,中午适逢母亲外出,留给了意中自由发挥的空间。在匆匆忙忙用煤油炉子炒了一盘鸡蛋,临出锅的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又放入了酱油,误打误撞地做了一道酱油炒鸡蛋,居然滋味颇好。虽然因此而受到了姐姐们善意的嘲笑,却给意中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那就是炒鸡蛋不能放酱油,就如同清炒虾仁不能放酱油一样,是一种禁忌,但酱油炒鸡蛋的浓香亦植入了意中的脑海。
上学的时候,到好友海有家去玩,因为海有家远在绥化,去一次就要吃住在海有家里。第一次登门第一顿饭就是过水面条,而卤子就是久违的酱油炒鸡蛋。这是意中第一次用酱油炒鸡蛋佐食面条,那股浓郁的鲜香配上面条的清淡,一下子抓住了意中的胃,同时也印证了这种吃法的真实存在,一度让意中兴奋并屡屡言传。
临毕业的时候,意中与哥八个又一次去了绥化。那时到绥化只能坐火车,而且需要运行四个多小时。中午从哈尔滨出发,八个人背了不少哈尔滨特产的副食品,诸如红肠、松仁小肚、酱猪肝之类的,到了绥化已经接近黄昏,恰巧家中无人,八个人饥肠辘辘地等在楼下,怀抱着那么多好吃的却饿着肚子,对于十八九岁的学生,不啻是一种另类的惩罚,几近煎熬。
终于盼到海有母亲回来,看到高矮不一、胖瘦不同一顺水的八个孩子,海有母亲高兴地扯着大嗓门喊了一声,我的八个儿子都回来了。就赶紧进屋做饭。不用说,主食一定是面条;卤子一定是酱油炒鸡蛋了。那时能吃,海有家中的锅也不大,一锅能下二斤挂面,一出锅,除了海有矜持些不吃,意中要摆摆老大的份不争,剩下的哥六个,一人一碗就没了。再煮一锅,又没了;而作为卤子的酱油炒鸡蛋亦是一碗又一碗,那顿晚饭最终吃了几碗酱油炒鸡蛋,意中没有什么印象,但哥六个吃了六斤挂面却是清清楚楚的。当三锅面条下肚,哥六个拍着滚圆的肚皮的时候,意中与海有已经有了半饱的感觉,饿过劲后真没吃多少,但这顿面条大餐,却永远留在了意中记忆的深处。
其实,说句公道话,酱油炒鸡蛋亦有两个明显的缺欠,一是酱油本身就是提升烹炒程度的,凡是炒菜的时候加上酱油,在提色的同时,烹制者要加快翻炒的速率,否则,就有炒糊的危险。而在炒鸡蛋的时候,如果鸡蛋炒老了,再加酱油,炒出来的酱油炒鸡蛋就有些硬脆了,口感不是很好;而一旦火轻了,嫩鸡蛋加酱油,就有了潮湿的海水黏稠的怪味,虽然很多人喜欢这种“海鲜味”,但于意中来说就是异味了。偶然的一次,因为手边恰好有一点农村大酱,尝试着搁了些,一尝,味道极好。火大了是酱香,火小了是鲜香,尤其是大酱独有的缓解胃寒的功能(意中自己感觉的'),混杂在鸡蛋里,就彰显了其舒缓的效果。意中开始正式制作酱炒鸡蛋这道菜大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很多人看到这道菜还很诧异,而今天小餐馆的餐桌上,已经习以为常了。不敢说是意中首创,比餐馆早了十年却是事实。而且,至今意中还没有看到某个饭店制作这样的面条卤子。这应该算首创了吧?
说到能吃,上学住校的时候,意中最大的饭量是一顿能吃一斤主食,其中有一斤油饼、十个包子的纪录,当然了,最多的纪录却是面条。学校食堂的过水面条,一般有两种卤子,一是猪肉与蔬菜,例如白菜木耳,一种是黄瓜丝麻酱。一般情况下,意中会选择麻酱面。直径15厘米高20厘米的大茶缸,正好能装下半斤面条,于是吃半斤再买,而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吃饭了,很多时候麻酱卤剩了,还可以让大师傅多给点麻酱,真香啊。年轻的时候,对于麻酱面,意中可谓情有独钟,百吃不厌,但凡有机会是绝不放过的,曾经有过连续一个月天天中午麻酱面的纪录,可以说痴心不改。随着年龄增大了,就喜欢热点,甚至烫嘴的热面了。口味也从清香的麻酱面转而麻辣面,别人吃安徽板面,放点朝天椒意思意思,意中却会刻意让老板多来一些,满满一层,意中戏谑自称,都是意中这样吃面的,做生意的老板就赔了,因为所嗜食的辣椒量惊人,如果还供应麻油,就更亏了。
意中家附近有一家麻辣面馆,24小时营业的那种,很火爆。第一次吃的时候,应该是2007年春,天气还有些寒冷,所以吃麻辣面的人很多,当时是三元一小碗、四元一大碗,麻辣面的碗一般都挺大,小碗也比普通的俗称二大碗大一号,并且更深。一般人也就一小碗就够了。当时,面馆还免费供应绿豆芽,一个不锈钢盆,里面盛着焯好的豆芽,顾客随便吃随便添,还有免费的餐巾纸,至于辣椒油、麻椒油更随便用了。而一些独具特色的小菜,例如干豆腐丝、土豆丝、海带丝之类的,一元一小盘,虽然盘子小了些,但一个人是足够的。很多街面上戳大岗卖力气的人,中午会买两个烧饼,来一大碗麻辣面,多浇上一些辣椒油、麻椒油,添个一两次免费的豆芽,就是一顿饭。也有当天生意好的,比平时多挣了些钱,就再花两元钱,来个小菜,甚至来瓶啤酒,或者二两白酒的,吃得热热乎乎的,哈着簌簌麻麻的嘴唇,发着响亮声音走进似暖还凉的春风里。也有会过的另类,一个人连续吃了六碗绿豆芽,仅仅要了一碗麻辣面。虽然当时豆芽只有五角一斤,但意中仍然觉得有些过分了。再后来,小碗麻辣面4元、5元…直到最近的9元一碗,面条上涨速度可以说在所有主食中属于领先。而免费的豆芽变成花钱添加了,你可以选择多来两元钱豆芽,那好,豆芽增加了,面条量下来了,因为碗的容量是有限的,而此时豆芽已经上扬到3元一斤了,而小菜竟然要六元,属于比较贵的,堪比大酒店的价格。餐巾纸也变成一元一包的便携纸抽。好在辣椒油、麻椒油还坚持免费供应,否则,动动就得付款了。对了,大蒜也是免费供应的,不过当大蒜价格昂贵的时候,是限量供应的,张嘴要,就塞给你三瓣二瓣的,没言语就当没这回事。
说起饭店面条的价格,意中吃得最贵的一次面条应该在1988年,是年秋冬交汇之际,意中到广东省廉江县开会,在广州换乘时,在广州火车站吃了一碗昂贵的面条,很简单,就是开水煮的挂面,一元四角一碗,服务员给你在煮好的面条上夹一筷子榨菜丝咸菜完事。不要小瞧了当时的一元四角,那时意中月工资不足百元,大约是在1990年,意中曾经获得市政府一级奖励工资,由原来的76元涨到了82元,虽然只有区区的6元钱,但那是莫大的荣誉。如果90年意中工资才到82元,那么88年加上各种补贴月收入也不会超过百元。每天平均三元多一点,一碗面条一元四角,就相当于现在每碗面条六七十元的水平,很贵了。再说了,只是一碗挂面而已。当时吃面条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两位沈阳年轻人也来吃面,光着膀子,横着晃着,很牛气的样子,面上来了,服务员按照惯例夹了一块子榨菜丝。两个人吃了几口,也许嫌没有滋味,就伸手把桌上盛榨菜丝的盆拿过来,自己往碗里加咸菜。服务员看到了直喊,榨菜是定量的,再吃要加钱的。俩人不屑地说,不知道我们是谁呀?东北虎下山了,吃几口咸菜还敢要钱。一边说一边继续往面碗里加榨菜,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服务员可不惯着你东北虎,大声冲外面喊,警察,有人捣乱。连喊了几嗓子,吓得两位东北虎扔下饭碗就走了。东北虎走了,警察就进来了,真不知道如果这些东北虎在警察面前还能不能牛?说起来,同是东北人,意中并不以东北虎自居为荣,更不要说为了一点咸菜耍威风了。东北人是出了名的豪爽耿直,但性子急并不一定就代表强势,更不能外强中干给人以口舌。说到剽悍,东北人并不上数。真正厉害的还是两湖两广甘肃陕西四川等江南省份的人,看一看建国时那些将帅出自何方,就会发现东北人其实寥寥无几。一个红安县,仅存活下来并被授予将军的就有130人,什么样的人最强横?什么样的人才配称王称霸?不要命的,敢玩命的,提着头闹革命的人不比什么自诩的东北虎要强势得多了?不要动不动就自诩东北人敢玩命,要玩命,东北人差得太多了。
不过自从在广州吃了一碗挂面,此后就再也没有在饭店吃过挂面煮的面条。倒是居家的时候,儿子有一段时间喜食面条,那就是放半碗肉丝,切一些白菜丝,炒好了再加水下挂面,这样的吃法一直伴陪全家好多年,偶尔就来上一顿。
说到家庭面条,要首属好友冀滨家传的豆角蒸面,据说是河北祖传的,先用猪肉炒豆角,加入水要炖时,把擀好的面条撒上一层,撒一层面粉,浇点豆油,然后再一层面条,一层面粉,浇些油。盖上锅盖蒸。熟了把面条与肉炖豆角混合起来一起吃,味道颇具特色。唯一的缺点是缺少了面条的柔嫩,多了些许硬韧。后来意中尝试着进行了改良,把面条擀的软些,就成了一家人喜欢的食品。对此,冀滨嗤之以鼻,谑称不伦不类。
在机械局工作的时候,附近有一家小餐馆,虽然菜肴不出色,但因为有拉面,着实火了一段时间,纯系意中之流喜食面条哄抬起来的。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发现老板开始多收钱,遂断绝了前往。
吃过了拉面然后是刀削面。山西刀削面成了意中在金太阳集团午餐的首选。当时只有三元一碗,还觉得挺贵。不过浇上辣卤,吃起来还是蛮有口感的。
再后来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安徽板面,从4、5、6,一直蹿升到7元一碗,别人吃着觉得贵,反正意中能吃辣椒,觉得物有所值,挺不错的。
都说北京人喜欢吃面条,在北京怀柔的五个多月,倒没有吃到什么像样的面条,偶然吃了一碗油泼面,那豆油还带生油味。倒是临时雇用的第一个纯正北京本地人的厨师,一位中年妇女,面条擀的好。不知道做什么吃的时候,就擀一盆面条,吃起来蛮筋道的。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意中曾经在前门附近吃过一碗打卤面,当时是三角钱一碗,宽宽的、厚厚的,卤子是肉馅与菜制作的,味道不错。最好吃,也是最难忘的,那是1985年第一次到北京,六月初的北京,已经很炎热了。尤其对于生活在东北的人,非常不习惯傍晚了还没有退去的热浪。在大栅栏一个偏僻的角落,意中吃了一碗担担面。当时人很多,没有座位,意中站在窗户边,满头大汗,心情烦躁地吞食着一大海碗汤汤水水的面条,在面汤与辣椒的刺激下,汗出得更多了,热意更浓了。出了一身透汗,反倒觉得一身轻松,并从此记住了担担面。但再也没有吃出那样的境遇,而此后多次去大栅栏找那家面馆,已经不复存在了。
说到面条,尽管林林种种,作法不同,口感各异,滋味不一,但于意中这样居家之人,最多的仍然是挂面。就是从小时候算起,吃得最多的还是挂面。有一段时间可以用粮油供应证上面的粗粮选购挂面头,也就是生产挂面过程中产生的“边角余料”,但因为是用面粉做成的,总比苞米面做的干粮吃起来爽口且不拉嗓子。大人戏谑地说,面条头也不错,吃到肚子里不都是碎的吗?住校学习期间,用面条头做的面汤一度替代了早晚两顿饭稀粥,想一想,三年啊,再不吃也是一千多天两千多顿呐,保守说,五百小水舀子面条头的汤汤水水是进肚了。好在学校的面条头也是可以使用粗粮票购买的。如果人的肚子能有存货,意中贮存最多的应该是面条了,而且是短短的面条头。
意中知道,此生将与面条难解难分,不离不弃,然而与我却是性之使然,心所甘愿。
在面食中,有一种从洪荒的新石器时代就飘香而来的食品,流韵至今,还在弥香长街窄巷,无论是豪华宾馆亦或快餐店面里,就是居家生活都可以见到它的踪影,那就是我们时常食用的面条。难以想象,我们祖先为了将小麦制种成为面粉,要花费了多少精力才研制出盘盘石磨,也不知道他们为了将面粉制种成为可口的面条,又费尽了多少心思,才想出了擀面杖这个简易的工具,不得而知的经过,也无法知晓。
打开尘封的岁月长河,划着记忆的扁舟,在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那个码头上,我不仅看过石磨,还亲自使用过石磨,去磨面粉。虽然不是洪荒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磨,但运转的原理和外貌,还携带着那时那固有而古幽的神韵。
河水清清,码头清幽,杏黄的竹篮在水中晃动,下面自动地漏去泥土灰尘,上面一只雪白的柳制舀子再飘去那些还带有外壳的小麦,这就是曾经洗净小麦的方法和场所。
洗净的小麦要摊在悬空的芦苇编织的席子上,去亲吻毛茸茸的阳光,当有八成干时,就可以一把一把地喂入磨嘴里,咽下的小麦在人工拉推运转的磨牙中被碾碎,在从磨盘之间瀑布般地垂下,这些粗细不均的半成品,必须在经过旋转抖动的筛子和箩子的处理下,才会成为雪白的面粉。磨碾出的面粉,一般是第二三轮回磨的面粉最漂亮,细腻,洁白,口感也好,但从营养角度来说,又无法和其它轮回出面粉相比,含有的微量元素少。每一次磨面粉,妈妈总是将二三轮回磨出面粉和在一起,并收藏在另一个缸中,平素不去动用它,专门用来做手工面条食用。
每一次做面条时,妈妈总是用干瓢(葫芦成熟后制作而成)小心翼翼地将洁白的面粉舀到一个瓷盆中,放到桌子上后,左手又拿起水瓢(也是葫芦成熟后制作而成的),从水缸中舀出一瓢碧清的水,又用右手抄起少量的水,慢慢地滴入面粉上,随手又搅和一下,继续淋水搅和,每一滴水都会在面粉中形成一个“雪团”。当满盆都是雪团时,妈妈才会放下左手的水瓢,挽起双臂的衣袖,伸手去揣面。
揣面的初期,如果发现太软,需要再加入一些面粉,倘若太硬,则需要加水。揣面往往用搓、揉、按、压等一系列方法,最后才将面粉揣成为一个外表光滑、内里软硬适度的大面团。无论做什么品种的面条,都必须让面团刑(放置在一旁)一会,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让水与面充分溶合,形成一体。
揣面,看似动作轻盈,柔曼,但却是一件吃力的事,每一次揣面,我都会发现妈妈的额头沁出汗珠,面刚刚揣好,就是那短短的十分钟,妈妈还要去做其它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将案板驾到平素吃饭用的小号的八仙桌上,并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并取出长约一米五的擀面杖(那时候,由于经常要做面条,一般人家对案板和擀面杖都很讲究,不仅外表光滑,木材一般会选择银杏树去加工而成,因为它木材看似柔软细腻,一旦制作成为物品则不会变形翘走),放置在一侧备用。
随后,妈妈取出盆你面团,放到案板上再次搓揉,直到妈妈认为软硬适中后,才会将面团按压成为一个大大的圆形,并在其上下又撒摊厚厚一层的面粉,在用擀面杖碾压几个来回后,就将它慢慢地卷在擀面杖上,并用双手轻轻而缓慢地向前推滚到案板边缘,然后,再拉回面前,再向前推滚……如此要经过数百次甚至数千次操作。
擀面时,双手要各自握住擀面杖的一端,用力要均匀,双脚剑步,上身前倾。随着滚动碾压的轮回成熟的增加,力度要不断增加,才能够让面逐渐变薄。同时每经过一段时间还要将面糊变成为面皮展开,撒上适量的面粉,以防止它们在擀面杖上粘结。初若荷叶大小,后赛缸口,最后直径几乎和擀面杖一样长。经过数次展开、卷起,并不断擀压,面皮才成为要求达到的厚度。
擀面的事急不得,必须循序渐进,一锅面条的筋斗如何、口感怎样,完全取决与擀面的功夫和细心,以及后来的刀工如何。如果擀工不到位,急急火火地就切成为面条,下锅后即使不成为浆糊,吃起来也十分难以下咽。
如果要做那种玉带面食用,擀出面皮要厚一些,薄如荷叶,擀到这种厚度后,只要将擀面杖从卷起的面皮中间抽出来,将面皮放置在案板中间,只见妈妈用手稍微用力,在面皮上按压一下,将它由圆筒变为长方体。无论菜刀是否锋利,妈妈拿起菜刀时,首先要将菜刀在水缸口的边缘去磨几下,或者拿起一只碗,用碗底去磨几下刀口,这样既可以让刀口更加锋利,又可以让刀口没有卷口现象,从而可以保证切出的面条不会粘结在一起,下锅后更不会相互纠缠不清。
切玉带面,左手扶住面皮,并要随着目视而不断后移手指,其宽度一般在一公分左右,右手的刀也要起落利索,有致。看似轻盈却刀刀到案板面上。切完后,妈妈放下菜刀,然后用双手的'十指,轻轻地夹起一段面皮,然后在准备好的簸箕上一抖拂,瞬间就是一根根韵味十足的玉带,飘落下去。这种面,特别是在锅里煮熟后,更是温润如玉,剔透若翡。
做玉带面,往往是为了家人食用,一则省事,方便,快捷;二是玉带面比较厚重,压饿(土语:消化时间长);三是下锅后也不易溶化了,汤清面实。
倘若家里来了客人,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去大小饭店和宾馆去大吃二喝。不要说家境贫困不允许,就是你有钱还得要找公社领导去披条子,最多也就四菜一汤一壶酒,菜也是家常菜,酒还是散装酒。要吃上那顿饭也要到下午一时多。每遇到这种情况,妈妈总会尽家中所有准备一些菜外,就是要专心地去切一种叫做龙须面的面条,去款待客人。
在当时,龙须面和玉带面的原料是一样的,主要区别是在功夫上。从和面开始加水时,就十分仔细,往往用一只崭新的竹篾做成的把子,去蘸水慢慢淋入面粉中,并不断地用手去抄拂面粉,使细小的面团尽可能不要黏在一起,意图是面浸水要均匀。在揣面时,更是用力去搓揉,要使面团达到一定的硬度。
最重要的是擀面的时间要长许多,也更费力气。擀出的面皮虽然不能够说薄如蝉翼,但,如果不是面皮上粘有洁白的面粉,就足以看到对面的人形。当面皮擀成功后,擀面杖是不能够像切玉带面那样直接从中间抽出的,而是要将绕在上面的面皮,像打开画轴那样展开,并同时将落下的纸一般厚的面皮随势折叠起来,大约有十公分左右的宽度,咋看恰似折叠的丝绸一般柔滑。
切龙须面的刀不能够用普通的菜刀,而是一把专用的刀口和刀身都很薄的硅钢刀。外形和普通菜刀一样,只是玲珑小巧一些。平素,妈妈总是将它擦上油收藏起来,不让别人随便使用。
切龙须面与切玉带面不同,其一,它一般是不用眼睛去看面条如何,一切凭着感觉走,往往是一气呵成后,才会去端倪一下。二是尽管挥刀如梭,动作极快,但刀用力适度,不仅不会伤及案板,就是在面皮下放一张白纸,也不会被损坏。每一次,妈妈将刀放下后,才会深深地喘上一口气,然后才会玩笑地去看一眼自己得杰作。
如果你不仔细看,案板上的面条浑然一体,好像没有切过一般。胸有成竹的妈妈,不慌不忙地拿过一个簸箕放在案板的一侧,然后双手的十指齐动,掐起一段“面皮”,随手向簸箕里扬起,恰若一朵白色的金丝菊一般盛开在簸箕之上,又如瀑布一样从天而降。接二连三抛起的面条,似风中的雨帘,在飘曳;而落下在簸箕中的龙须面,既像渔夫收在一起的丝网,又若织女待理的蚕丝。
就在妈妈切面的时候,细心的姐姐已经燃起了彤红的灶火,在炊烟袅袅升腾的同时,锅里的水开始了歌唱,性急的已经如雾似岚地从锅盖的边缘溜了出来。当妈妈将面条端到灶头上时,锅里的水正好哑然无声。猛火沸水,揭开釜板(木制的锅盖),就将簸箕中面条全部倒入锅中,迅速地有盖上釜板。只须臾功夫,妈妈再次揭开釜板,随手抄起一把漏勺和一双特制的长筷,“疯”了一般地将面条一次一次地捞起。然后放入早已调制好的汤碗里,这种龙须面是不能够盛满的,只能够半碗,并要迅速一边用勺子立即添些面汤,一边用筷子去挑上几下。
当最后一根面条滑落碗里时,你会惊奇地发现,面条已经“长”满了碗。同时,每一根面条也灵性起来,似乎在汤里还在蠕动,似乎有了生命,不断地舒展着身姿,似纠缠在碗里得龙须,也因此而得名——龙须面。
吃龙须面,是一种矛盾的吃法,一种儒雅与粗鲁融为一体的吃法。看过陈佩斯与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条》的人,都不会忘记陈佩斯那狼吞虎咽的吃相。看似不雅的动作,可恰恰是吃龙须面的方法,可以说是吃龙须面的翻版。
吃龙须面,你就是大儒也无法文雅,倘若你文雅则肯定会被认为你少见寡识,不谙世事。因为吃龙须面的人坐在桌前,首先要勺子舀一点汤,去品尝它的咸淡和口味,决定是否要添加调料。然后要用筷子高高挑起,并要同时微开双唇,不断地轻轻地向面条吹气,去冷却龙须面。
当数次挑起、滑下后,凭着双眼的观察,感觉不烫时,便可以身体前倾,微低头颅,用舌头确定不烫后,就一口咬住被筷子挑起的面条,边吃边用双唇将面条吸入口中。会吃龙须面的人,往往就是一口就将一碗面全部吃光,当然,也离不开筷子的帮忙。所以真正吃龙须面的时间很短,而冷却它的时间却比较长。如果你要儒雅地一根一根吃,那定然会丑态百出,出现那句歇后语的尴尬之事:小鸡吃粉丝——绕脖。在农家吃龙须面是作为主食,而在宴席上吃,则往往是作为一种点心。
龙须面,在我国已经有数百年的风骚,雅韵流长。看似普普通通的面条,它的出生却在豪门的宫殿,原本并非是草根百姓的食物。相传它诞生在明朝的御膳房,那时有一个立春吃春饼的习俗。可那一年,御膳房的一位厨师,冒着被驱逐皇宫甚至治罪砍头的风险,独出心裁地制作了细如发丝的手擀面,在青花瓷的碗里,特显灵动,恰似一根根龙须在舞动。但皇上看到时,龙颜大悦,赞不绝口,并下令在以后的每年的二月二这一天,龙抬头的日子里,皇宫所有人食用龙须面(当然,当时皇宫的龙须面多了一道油炸的过程)。后来,这个习俗就传到了民间。随着人们的生活的不断提高,后来就成为了普通百姓家庭时常食用的面条。龙须面,以劲道、可口、筋斗、爽滑的特点,让人吃后余味犹存,口齿留香。也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垂青。
回眸面条的历史,起初它叫做“煮饼”,是将面块擀成为饼状,再汤锅煮熟。到了晋代被改称为“汤饼”,并一直沿用到大唐盛世。到唐玄宗李隆基时,御膳房的厨师为了取媚,才将饼状改为了条状,也形成了生日吃面条的习俗。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后,面条的花色花样逐渐增多。无论铁木真东征西战地戎马一生,是否看到我们现在所说得挂面,但挂面就诞生在他的大元帝国。明朝的江山,是一个放牛娃出生的朱元璋开创的基业,他手下有一个著名的军师叫做刘基,他不仅文韬武略,决胜千里,还对面条情有独钟,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专门记录下八种面条的做法,以传承天下。龙须面就诞生在明朝。努尔哈赤的铁蹄踏过山海关后,汉满文化的交汇,特别是餐饮文化的交流,也使得面条的品种层出不穷。如今的面条,光名字就让人眼花缭乱,品种也林林总总,加上地方特色更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