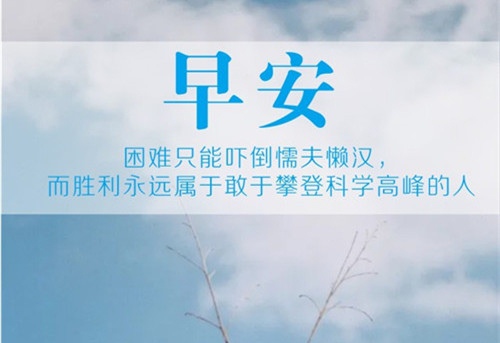
“隐”,即仕的对立面,是相对于仕的隐,脱离开仕,也就无所谓隐。“隐”和“仕”都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即出世或入世。“归”是渊明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如“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等。“归”,主要解释为“返回”之意,“归隐”即返回到“隐”这种处世态度或处世方法,也即“出世”。从“返回”一词中可简要
(一)“居官”时期的归隐情结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从小就爱好大自然,对世俗的事情不甚留心,不感兴趣。不过,年轻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抱有“猛志逸四海,
陶渊明是在二十九岁时去江州做祭酒,但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却看到了许多官场之弊,深深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和少壮时期的热情。所以,他很快就辞官归田。“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是他当时就下过的决心,也曾想坚持下去,但此时的陶渊明毕竟年纪尚轻,内心还埋藏着希望之火,再加上朝廷中又发生了一些“良性变化”[5],重新激起了陶渊明“大济于苍生”的壮志豪情。于是,闲居了几年后的陶渊明,在三十多岁时再度出仕。但这一次,他依旧不是一路欢欣,而是对官场生活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退隐之心更是与日俱增。且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
其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
其二: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
这两首诗写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36岁(据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他此时是桓玄的幕僚,作为桓玄的使者到建康(南京),请求获准发兵讨伐孙恩[6]。从诗歌描写的情形来看,他这次赴京虽然履行了使命,但回来时的情绪却十分不好,诗中通过征途中遭风浪、阻穷湖而不得尽快到家的苦恼,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厌倦官宦生活,向往田园生活的感情;又以归路与旧居相对,以行役之苦与园林安静美好使人留恋作比,表明他对出仕做官所抱的厌倦态度。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记载,陶渊明当时到了京都建康之后,由于亲眼看到了司马道子父子及司马尚之兄弟挟制皇室和他们的专横暴虐,看到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与桓玄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各派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等等,陶渊明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桓玄也起了疑虑。这样,他原先内心的热情消退了,越发感到这次行役没有意义,甚至后悔当初的出仕,又转而思念起园林,想重新回去隐居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
但这次的辞官归隐,没有像辞去江州祭酒那样容易,陶渊明的心中充满了欲隐而不能隐的痛苦,而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更加大了他归隐的趋向。“遥遥从
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是在刘裕帐下任参军。这次出仕的原因更多是由于“畴昔苦长饥”,才“投耒去学仕”,所以从一开始,陶渊明就没有抱太多的热情。且看他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本诗写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40岁,本诗是在他去赴任刘裕的参军的途中所作。在路途中,船在向前行,但归思却把诗人向后拉。异乡的景物没有使诗人感到新鲜,却使他感到厌倦,因为诗人心中所怀念的,是身着粗衣也欣然自得的田园生活,田园笔耕的`素志,才是陶渊明内心的真正寄托。自由自在高飞的鸟儿,在水中轻快地游来游去的鱼儿,都使他这个有了俗务缠身、不得自由的人感到惭愧。所以诗人强调他是“暂与田园疏”,表示“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最终要回到田园隐居。这一次,陶渊明更加坚定地确定了他最终的人生归宿--归隐田园。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初,陶渊明离开了刘裕幕府回到了浔阳,在当时任江州刺史的刘敬宣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
在诗中,陶渊明再次表达了要永久归田的决心,对自己抛弃田园生活而走仕宦之路一再提出怀疑甚至自责,表示“素襟不可易”,即自己归隐田园的素志不可改变,并表示自己的德行要像霜中挺拔的松柏那样坚定高洁。不难看出,陶渊明的归隐决心是越来越大。终于,在他41岁的这一年,从彭泽县令任抽身归隐后,躬耕垄亩,再不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开头两句,如大声疾呼,如大声棒喝,这是诗人对自己发出的召唤和命令。诗人把自己13年中的仕途生活,看作是失路人走过的一段“迷途”,可见痛悔之深。而对即将到来的田园生活则向往之至,情怀急切,语调轻快,不难想象诗人当时的心情。
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为期甚短,他辞官的原因是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隐逸传》,后来萧统作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渊明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在亲故的劝说下,决定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适逢郡督邮来县视察,县吏说:“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解绶去职,在任仅八十余日。《归去来兮辞》就是这件事实和这番心理的自白。他在辞的序言中写到: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出仕彭泽令,本是为了温饱,但卑躬屈膝的官场生活与渊明的个性到底不相容。几经体验,他终于感到挨饿受冻尽管痛苦,但是违背自己的本性更是难以忍受。为了填饱肚子而勉强从仕是错误的,有愧于自己的“平生之志”。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回到田园后更穷了,甚至不得不去乞讨,但他的心却宁静了,因为在隐居生活中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陶渊明归隐田园后,实现了自己居田从文的人生理想,此后他在思想上虽曾产生过功业无成的苦闷,也并未彻底遗忘世事,但他始终不改初衷,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验。毕竟,他是遵循着“自然”的召唤,十分自觉地退出了官场,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田园。
当然,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也常有此类的人生慨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五首·其四》)、“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其四》)、“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深陷在痛苦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相反,他在“自然”中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陶渊明《饮酒》诗中最著名的句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表现了他在归隐中的闲适心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这两句诗是“无我之境”的典范,他解释“无我之境”为“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可见,此时的陶渊明已达到了“庄周化蝶”[8]的境界,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青的山,白的云,盛开的秋菊……都在陶渊明的眼前呈现出最美好的天然形态,没有一丝污垢,没有半星尘埃。他全副身心拥抱着这一切,仿佛化成了它们的一部分。此时再回想官场中的生活,如笼中之鸟,不得自由,“心为形役”,痛苦不堪,他如何会抛弃眼前的归隐而去出仕呢?他要追求的是“复得返自然”,抛弃官场那种“非自然”的生活,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外物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返回到质朴真淳的人生。他不仅自己坚定地做到了这一点,也以此来规劝他的隐士朋友们。
与陶渊明同称为“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为江州刺史所请,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一起在城里讲礼、校书,其办公的地方同马厩差不多,陶渊明还写了诗去嘲讽他们,这就是《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
负婀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寻常,道路
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
陶渊明在诗中对当权者通过虚伪的崇“礼”以达到为自己沽名钓誉和笼络人心的目的,含蓄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对周续之等三人既非其时、又非其地的讲“礼”行为和有召即出的假隐士态度提出了批评,并劝他们和自己一起隐居。陶渊明不仅自己不应征命,还希望别的隐士也同自己一样站稳立场,可见其归隐情结不仅植根在了心中,更深入了骨髓!
入宋后,陶渊明贫病加剧,江州刺史檀道济前去看望,并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劝陶渊明放弃隐居之志出仕。但陶渊明仍不为所动,也不接受檀道济的馈赠。(见萧统《陶渊明传》)在他心目中,“道”不同,非但不相谋,甚至吃一顿饭也是不可以的,毫无松动之处。他宁可敲门乞食,也决不为米弃志。陶渊明坚持己志以终老,在封建社会无数的隐士中,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他不愧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士!
(三)从“徘徊——回归”的诗文主题中解读其归隐情结
在汉魏以来的文人诗中,徘徊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主题。阮籍在其《咏怀诗》中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当代学者袁行
上文已述,陶渊明于公元398年至405年先后投入荆州军府桓玄和北府刘裕幕中,置身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在这政治上最为黑暗、混乱的八年里,他没有找到可以依靠并且值得为之效忠的政治势力。这八年就成了陶渊明一生中徘徊幅度最大的八年。而实际上,他的徘徊从更早就开始了。早在他第一次出仕江州祭酒时,他就“不堪吏职”,很快地解甲归田。这一进退便是他更早一次的徘徊。从青年时代一直到辞去彭泽县令,又徘徊了多年,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田园。“陶渊明和阮籍一样,都徘徊在相互敌对的政治力量之间,无所适从,内心经历着同样的风雨。所不同的是,阮籍以醉酒任诞应付新的当政者,而没有退出仕途。陶渊明则拂衣而去,断然离开了仕途,甘愿躬耕了此一生。”[10]所以,“徘徊——回归”成为陶渊明诗文中新的主题。
在辞彭泽县令之前,陶渊明虽然是钟情于隐逸生活,但是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的选择上,陶渊明有过矛盾的心情。他“遥遥从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归去来兮辞》是“徘徊——回归”这一主题的集中体现。前面已经说过,这篇辞赋是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是时候所作的,当时他将归而未归,但心已经飞归田园,并且设想归途的情景、归后的情景、乃至第二年春天农耕的情景,一一历历在目。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设想一种新的生活,筹划一个新的开始。《归去来兮辞》宣告了徘徊的结束,也宣告了回归的决心,此时,陶渊明的归隐情结已经充分地展现和升华。从此以后,陶渊明不再徘徊,只剩下了回归。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但到了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05年,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