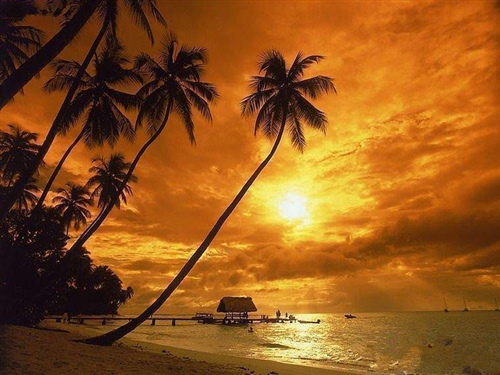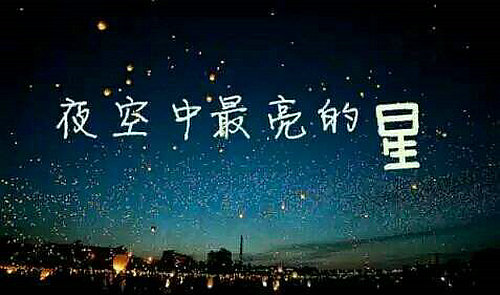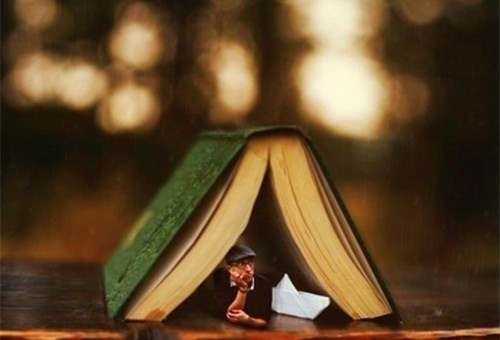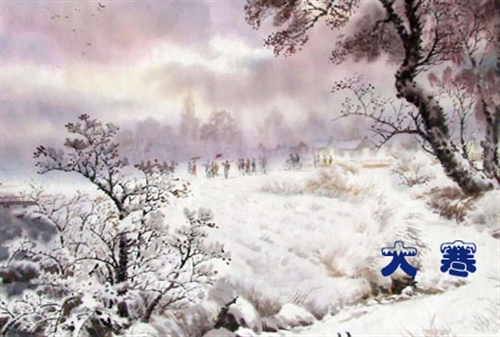
四月的时候,白色的荞麦花就一茬茬开放在故乡的土地上。轻灵的花瓣一簇簇,像缭绕在峡谷间的白云。偶有微风拂过,它们便柔柔地蠕动,小心地挤在一起,发出细细的沙沙声,像是在说着什么悄悄话。
这便是乡村,大别山深处的乡村。这样的乡村在大别山深处多的是,它们歪歪斜斜地随便躺在大山中的某一片山梁上,如干活干累了的庄稼汉躺在干净的草地上眯着眼睛望着太阳。记忆中,那些乡村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荞麦花的芬芳。
有一年,那是荞麦花开得最旺盛的一年,母亲也显得很高兴,在她的脸上,开满了灿烂的荞麦花。我们几个不懂事的泥巴一样的孩子,在荞麦花丛里开始了我们的游戏。瓦蓝的天空中,红红的太阳朝我们傻笑,我们看见那么多的荞麦一起开花,那么多的蜜蜂和蝴蝶烧遍了山梁,心也像烧着了一样,一溜烟就滚进了荞麦花海。我们在里面打滚、藏猫猫,你追我赶,把荞麦苗铺在地上睡觉,或者搭起来盖成小房子,阻挡炽热的阳光,一块荞麦地就这样变成了我们的游乐场。傍晚的时候,我们趴在湿漉漉的麦草丛中,迟迟不肯回家。远处的山梁上,传来了若有若无的山歌。那声音粗犷,调子单一,回声在山谷里四处乱撞,飘到我们的耳朵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然后,就传来了清晰的呼唤声。母亲在叫我们回家了。我们偷偷地溜回了家,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做了坏事。
当夜相安无事。第二天,事情败露,我看见母亲脸上的花突然凋谢,一种阴霾笼罩着她愤怒的表情。她抓起一根竹竿,竹竿疯狂地在我的身上乱击,我扯着嗓子鬼哭狼嚎起来。母亲不管,依旧打。竹竿在飞,母亲的眼泪在飞,泪光中,我看见荞麦花在一朵朵地飘落,它们飞起来,又落下去,像我童年青黄不接的日子。
荞麦是最贱的农作物,不管什么样的土地里它都能够生长。我们这里海拔高,又是山区,黄土地上长不出高贵的粮食,只有荞麦不嫌土地贫瘠,落地就生了根,把个山梁打扮得绿油油、白亮亮的一片。可是,它带给了我童年太多的苦涩的记忆。记得我进城读初中的时候,母亲把我们这土地里出产的最好的粮食——玉米——扎了满满一袋给我交到学校食堂,食堂的管理人员给了我一叠纸做的饭票,上面写着“粗粮”二字,而别人的`饭票是蓝色的塑料做成的,上面的字是“细粮”。我就知道,我的故乡和山外的地方相比,存在着我无法想象的差距。在我的故乡,玉米已经是最高贵的粮食,它们只选择在房前屋后的肥沃的土地里生长,可是当它走出大山,身份就变得卑微了。家乡更多的土地,被一茬茬的荞麦所占据。夏天的时候,荞麦饭成为每一户人家的主粮,当那些金黄色的饭一块一块出现在我的碗里,我就明白,那种略带苦味的夏天将会变得异常漫长。有时候,我宁愿就那样闻着荞麦花的香味,也不愿尝一口那苦苦的荞麦饭。这样的时候,母亲总是变着法子把荞麦做成各种各样的饼。她在荞麦面里放一些从别人家要来的苏打,再加上一点糖精,掺水调和,煎成各种形状的饼,吸引我们兄弟姐妹吃。
贫苦的日子被母亲煎得有滋有味,可是,那样的日子也给母亲的额头划上了太多的皱纹。那时候父亲总是东奔西走,一年没有几天在家,说是做什么生意,结果背了一屁股的烂账,过年成了真正的“年关”,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跑到我们家里来问账,都是父亲在外面欠上的。父亲躲在外面不敢回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一天一天地磨着日子。我们不懂事,晚上的时候,困了就躺在长凳上睡着了。母亲忙到深夜,还要把我们一个个抱到床上。好多时候,我听见她一个人在炉边低泣。那样的夜晚,常常有风吹过我们家破烂的屋顶。
一个女人要独自撑起一片家的天空是多么不容易,我们的头发长了,母亲就学男人一样拿着剃刀给我们剃。这样的事情,历来是男人做的,可是,母亲不得不做。她剃头很疼,一不小心还会把我们的头剃出口子来,所以,每次剃头,我都尽量躲。有一次,她把我哄来,刚剃到一半,我就忍受不了了,站起来就跑。
母亲在后面喊:你给我站住!头才剃了一半呢,这样出去人家会笑死你的。
我不听,依旧跑。
母亲就在后面追。
那是四月的时候,阳光很好,还有微风拂面,我没命地朝山梁上跑。
母亲依旧追,喊。
我一下子就窜进了荞麦地里。荞麦正疯狂地开着花,它们在我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痛苦地呻吟着。我没管,依旧跑。
母亲追到荞麦地边,站住了。
小祖宗,你给我回来,头不剃了总行吧?你看,你踩坏了那么多荞麦!母亲哭喊着。
我停了下来。我看见母亲蹲下来,双手蒙面,哭
母亲蹲下的时候,她瘦弱的身子像一株被我踩踏的荞麦,慢慢地倒下
我小心地挪到她身边,不知所措。我从来没看到她哭得如此伤心过。
孩子,这是庄稼,是我们的粮食,你不能踩,你怎么能够踩呢
我也哭了
那一年,荞麦花开得很好,可是却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大风,大片的荞麦在花尚未落尽的时候就被席卷在了地上,像是捣蛋的孩子在里面打过了滚。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事了,现在故乡的土地通过整合,土质肥了很多,普遍能够种上了玉米,种大豆的效果也不错。夏天的时候,放眼望去,再也望不到荞麦的影子,荞麦花的香气也没有了。
母亲老了,的的确确的老了,脸上沟壑纵横,瘦得像风,加上多病,身子一天不如一天。我们都很担忧,害怕她突然间就离开了我们。那段时间她病重得厉害,什么也没吃。有一天她说,她想吃荞粑。周围都没有人种荞麦了,荞麦饼自然也没有,我特意到很远的一个集市上给她买了一些回来。母亲吃着的时候,精神很好,话也多了起来,慈祥的脸上,开满了迷人的荞麦花。
那一刻,我们兄妹几个像孩子一样偎依在母亲的身旁。在我眼前,一大片绿绿的荞麦在随风轻摇,白色的荞麦花像云朵一样在阳光下自由绽放
(责任编辑:尉克冰)
荞麦花开,总能勾起淡淡的乡愁,勾起了荞麦花、荞麦搅团、荞麦油圈、荞面鱼鱼、荞麦凉粉、荞苦荞茶、荞麦花卷的思念,哪怕千山万水,哪怕天南海北。
前天,远在陕西榆林市定边工作的弟发来了定边县五十万亩荞麦花开的视频,并要求我能去看看;画面中,漫山遍野的荞麦花开得正艳,粉色、白色、紫色的荞麦花,竞相绽放,随风轻舞,恍如天上人间。
八月初正是定边县风光最美的时节,漫山遍野的荞麦花盛开,给整个大地,都铺上了一层粉色。花海、油田、风车、白云、蓝天……夏末满山的红花荞麦映衬着如诗如画的白于山,那是定边南部山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眼望不到边的梦幻粉,美到窒息。定边荞麦花颜色大多为紫色,也有粉色和白色,茎秆纤细而修长,带有渐变的绛红色,簇伞状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婀娜多姿。远远望去,大片花田摇曳在微风里,犹如翻滚的彩色浪花,那片随风轻摇的荞麦地,和像白云一样在阳光下自由绽放的荞麦花。一片片荞麦花竞相怒放,白的、粉的、红的`……是那么艳丽,那么耀眼,那么芬芳,给这里的山川大地增添了无限的色彩和生机……
道路的两旁,无边的田野里,满山的沟壑里……随处可见盛开的荞麦美景。
粉色的花海里,随便来一张照片,都是满满的少女心。
我去过定边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定边县位于陕西省西北部,榆林市最西端,陕甘宁蒙四省(区)七县(旗)交界处,古有“东接榆延,西通甘凉,南邻环庆,北枕沙漠,土广边长,三秦要塞”,是陕西省的西北门户。定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陕西一颗璀璨的“塞上明珠”。虽然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国家首批绿色能源示范县”、“全国绿色环保节能示范县”、“中国马铃薯特产之乡”、“中国马铃薯美食之乡”、“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陕西省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等,但干旱少雨,山不青,水不秀。十年过去了,定边把现代农业发展的如此好,我的确没有想到。五十万亩荞麦在八月初竟相开放,满山遍野都是花的海洋,对于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接酿的定边是多么况观的风景……
望着这一幅幅如痴如醉美丽的画卷,不由使我想起了小时候老家的山山水水。我的家乡在六盘山脚下,泾河岸边,小的时候,也种荞麦,芥麦花总是在这个时期绽放,那时虽然是大集体,但除种植小麦高梁之外是很重视小秋作物的种植的。麦子收了,种荞麦、糜子、黑豆、油菜、高梁,行子里套种的黄豆、白雲豆,糜子谷子地里套种赤小豆;村上还种爪果蔬菜。每到秋收霜降时便是收割的季节,打碾后每家可分到数量不等的五谷杂粮。父亲用五谷杂做酿黄洒,母亲用五谷杂粮做的各样美食,尤其是荞麦搅团、荞麦油圈、荞面鱼鱼、荞麦凉粉、荞苦荞茶、荞麦花卷,现想起都流口水。那时的秋天,天高气爽,层层梯田里,红红的高梁,沉甸甸的谷穗;荞麦田里,一眼望去尽是白色粉色交织的图画,阵阵花香也迎来蜂逐蝶舞。那扑鼻而来的荞麦花香满载收获的喜悦和希望。而现在家乡种粮己经简单多了,一律的小麦和玉米,小秋作物,五谷杂粮几乎不见了,甚至吃的菜就要赶集,还上县城去买。
最近,在去九寨沟旅游,路过川西重镇,川主寺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原上种植了近万亩薰衣草,主要用于参观,拍照;平凉市崆峒脚下的胭脂峡口,种了近千亩长寿菊也在开放,还有更多的玫瑰园,牧丹园,等等;而定边县的五十万亩荞麦的种植,荞花开放吸引游客,荞麦收割则是最好杂粮,面可做更多的美食。看来农业现代化,产生化路还很长。而转变观念,一举三得是不是更重要呢?
荞麦以丰腴的身姿卖弄着,把媚眼抛向了村庄,还有这块土地。她的花儿宛如月色,素白,肃穆,像星光下的冷美人,着一身褐红色薄如蝉翼的纱裙。
正应了这些,被世人宠爱在一身,便给它取了上乘的雅号:乌麦,荍麦,花荞,甜养,荞子,胡荞麦。
这一连串的名字多美啊!听起来极其舒服,让人美在心里,美在骨髓里。它渗入的是一种自然界的灵魂,韵味。在美美的植物灵性里,美得让人窒息。
荞麦喜欢月亮,趁着月光如水的夜晚,它含情脉脉的竞相开放着花瓣,暗送秋波,像人间思念夫君的女子,温柔体贴,秀气可人。荞麦的美以它的叶绿,花白,茎赤,子黑,根黄,称霸植物界,亦具五方之色,奇,艳,美,实为贵。喜寒耐冷不屈不挠。
读着那些美丽动听的别名,温暖,文雅,清静,优美,艳丽。想着古人与祖先对荞麦的钟情与宠爱。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敬仰,尊重。它的植物体内蕴藏着的精气,内涵,它给农民与人类的无私的精神,生命,呼吸。都在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里。
麦子下了地,腾出几亩来。便种上一大片一大片的荞麦。荞麦脾气好,温驯,顺眼。好种,长得也齐整。由着自己的性子,漫不经心的种,撒下些许颗粒,多少施点肥,两三个月后站在地头间,放眼望去,犹如千军万马,浩浩荡荡的,绿油油,齐整整。它全神贯注的疯长着,没时间去打理路人,向农民问个安。
刚出土长成个把月的荞麦苗,水绿绿的,嫩的可爱。不忍心去践踏,但看着垂涎欲滴。我们便去用镰刀割来几小捆,回家做凉拌菜,附着面条与馒头就可以吃。
用水洗净,淘了再淘,在开水中略微浸泡片刻,捞出切碎了,放入盐醋,蒜沬儿,辣椒油,调料。一盘简单的荞麦凉拌菜就盛到了桌上。
低头品尝,仔细看看,釉白的碟子里,嫩绿的菜叶儿搁在木桌上。吃着雪白雪白的馒头,就着荞麦菜,看着就香。少年时的我总是忍不住自己的胃口,被家里人常常叫作“饭桶”。我也希望少吃点,可是我太饿了,没有办法啊,只要看到那荞麦做的烙饼,糕点,荞酥,凉粉,血粑和灌肠,馋得直流口水,碟子和碗底都用舌头给舔个精光光,亮得能照镜子。
这荞麦菜吃起来稍微有点苦涩的味道,但在我们眼里却把它视为宝物,救命稻草。餐桌上的精品,物以稀为贵,你不能顿顿吃啊,顿顿吃,那几亩地的荞麦还打粮食。所以这荞麦也只能图个新鲜,诱惑一下胃口,吃个几顿便就了事了,不能贪,贪得一顿美,饿得十年荒。只能等着荞麦面下来了,变换着法儿做着吃。民以食为天,盼得就是这年景与丰收的希望。
我家的荞麦地靠着村子的公路边上,这荞麦一开花,十里都野茫茫的,香味飘飘。那些花儿的颜色,雪白雪白的,煞是美丽极了,像少女脸上涂上去的香粉。在每一朵花里,都尽情的散发着清香。惹得满荞麦地里都是蜂蝶,成群结队,被这荞麦花儿把蜂蝶弄得神魂颠倒,整天沾花惹草,耍弄着水性杨花的贪婪之心。
花儿开,蝶儿飞,蜂儿来,好热情,好热闹。它们还各自唱起了歌,嗡嗡____嗡嗡____嗡嗡____。不停的在扯开嗓门在炫耀着。我心里在想啊,这些小精灵你真的不嫌累吗?
荞麦花开得正旺时,村子的赵拐子,他们家养蜂。一年四季靠养蜂卖蜂蜜为生,很少种地。他们家的那几亩地都荒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蒿草。这李拐子心眼多,脑子精得很。整天在村口荞麦地边上周旋,一看到我们这些放学的小孩们,就拿点蜂蜜诱惑我们,为的是让我们给他搬运蜂箱。今儿个挪挪,明儿个搬搬,忙活完了,李拐子就给每人一小勺子蜂蜜。我们爬在他家的箱子堆上用嘴吧唧吧唧的吃起来,用馒头蘸着吃,李拐子家的勺子底总是被我们舔的干干净净,省得李拐子去洗。
走时,李拐冲我们诡异的一笑,有活儿干就给你们这些熊娃娃留着。这李拐子可真是人精啊,每当我们放学路过此处,总会小恩小惠一些好吃的,拉拢我们的心。他葫芦里卖得什么药,我们都知道。
每逢荞麦花开时,李拐子就搬弄着蜂箱子,村子的东头到西头都是他们家的蜂。他人虽然有残疾,可她媳妇长得跟仙女似的,是那些年去外地放蜂采蜜时在张掖用花言巧语把媳妇弄回了家。侍候的百依百顺,什么衣服都穿了,很享福的。这些都是大人说的,我们只知道这些。
放蜂的日子一直到村子里荞麦花谢,荞麦籽熟了时才收工。转眼间,天气冷了,蜜蜂也要过冬,躺在箱子里也不太出来了,收工完时,农活也相应少了,村子也安静了。这时赵拐子一巅一瘸的`挑着扁担,两头系上木箱子转村下巷,吆喝着去卖蜂蜜了。他心里高兴的劲儿比蜂蜜还甜哩!
俺村里,祖祖辈辈都有种荞麦的,有种荞麦的就有养蜂的,尤其是赵拐子养的声势大,蜂多。荞麦在粮食里是一种极其有营养价值的一种农作物。在父母那个贫寒的年代,大多是为了填补口粮,那时粮产量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不计较吃好吃坏,只要吃饱穿暖,小肚子不遭罪就行。荞麦用的都是农家肥,疯长着,颗粒也丰满,我家的荞麦一打就是好几石(dan),窑洞的木櫈子上整整齐齐的码了几溜溜长,挤在一起端庄的很。吃不完,当家里牲口喂,作饲料,或变卖一点钱,把日子充实一下,再苦再累也是一种美美的幸福。常常看到父母在窑洞里来回东瞅瞅西望望,看着自己种的庄稼打下的粮食,心里乐呵呵的。
关于这荞麦啊,还有个故事呢。说俺村在若干年前考上了一名大学生。家境贫穷,他刻苦努力,勤奋好学,结果考上了大学。当时村子像炸开了锅似的。方圆几百里都知道俺村出了个“秀才”。村子的人即羡慕又自豪。这自然给村子里增了光添了彩。
后来外村人把自己的闺女接二连三的往俺村介绍,谁不高兴呢!“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而如今是“小伙子不出门,媳妇子送上门”。真是好事连连,双喜临门。就连俺村那虎头虎脑,傻里傻气的狗蛋,年过三十多了,还有人上门给提亲呢!真是一人栽树,十人乘凉啊。那狗蛋嘿嘿一笑,拔腿向村子里的胡同深处跑去,嘴里结结巴巴的叫嚷着说:俺要娶媳妇了,还要…还…还要生个娃咧。他一溜烟的消失在村子尽头。
话说那个大学生几年后,也告别了家乡的这片热烘烘的土窝窝,曾经养育他的那片荞麦地。他跋山涉水寄居在大城市里了,有了工作,事业,家庭。有一年回家探亲,父亲劳碌在田间。正是荞麦开花荞麦熟了的时节,他与老父亲走在田径上。低头便瞅了大半天,问父亲说:这白花花,黑子子,红杆杆是啥东西。老父亲抬头看了儿子一眼,说:娃!你忘了根了啊!这是荞麦,你小时候还躺在荞麦杆杆上睡过觉呢!
“红杆杆,白花花”这个典故我一直流传至今,被人们取笑那些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讽刺忘根忘本的人,同时告诉我们不论你身处天涯海角,还是官位多大。可有一点,故乡那些曾经的苦难与贫穷,永远都是我们人生的起点,只要记住艰苦奋斗,才会有美好的幸福!
红杆杆,白花花,黑子子,开在黄土土里,长在黄土土里,迎着那轮艳丽丽的太阳,开花了,籽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