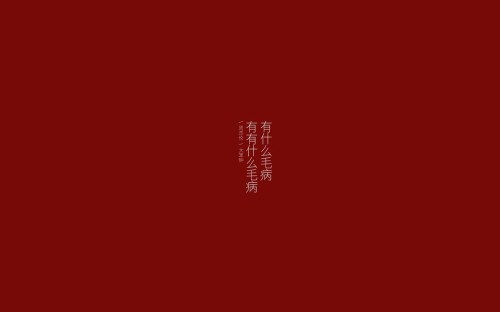在上个世纪70年代,山村的孩子大约没有没看过露天电影的。我们那个小镇的人,可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有三处,一个是种子站,它就在我们小镇的西头,离它最远的东头的人家走过去,也不过是一刻钟的时间,所以那里一放电影,只有种子站是有灯火的,小镇的房屋都陷在黑暗中,男女老少都被吸引到银幕下了。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是部队,一个是十三连,一个是十七连。
如果是在种子站的广场放露天电影,那么下午的时候,一些老人就把座位给摆好了。老人们
那些挎着两个板凳占座位的老人,都是有老伴的。而那些孤老头子,拎的则是一只板凳。所以拎一只板凳的瞧不起拎两只板凳的,觉得他们成了老伴的奴隶;而拎两只板凳的又瞧不起拎一只板凳的,觉得他们身边没个人陪着,缺乏派头。我奶奶过世早,我爷爷属于拎一只板凳之列的,但他从来不提前去占座位,他总是在电影开映前才提着板凳过去。他并不急于把板凳放在前排的空地,而是抽着旱烟,先看一会儿扫在银幕上的画面,觉得有趣,就随便找个地方放下板凳;觉得无聊,就挎着板凳放开大步往回走。走的时候他总要大声吐几口痰,好像那些未打动他的画面是几缕不洁净的空气,阻碍他的气息流动了。
有一回我去种子站看电影,远远看见我爷爷提着板凳大步流星往回返,我以为电影不演了呢,一问他,他竟然气呼呼地说,今天演外国电影《死了不屈》,有什么好看的呢!他一向讨厌外国电影,说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没有什么好货,更何况那电影名也让他生烦,什么叫死了不屈呢,人在人世间辛辛苦苦走一遭,尝遍了苦水,死了还有个不屈的?!听着他牢骚满腹地发着感慨并且大口大口地吐着痰,我觉得他比电影中的人还有趣。其实那部电影叫《宁死不屈》,他把名字记差了。那以后他要是蹙着眉看什么不顺眼了,我就会适时说一句“爷爷,死了不屈”,他就不绷着脸了,他笑着用烟袋锅敲我的头,骂我是个调皮捣蛋的丫头,将来肯定不好往出嫁!
露天电影多是在夏天放映的,所以人们来看电影时,往往还拿着根黄瓜或者是水萝卜当水果来吃。当然,人群聚集的地方,也等于是为蚊子设了一道盛筵,所以看电影归来的人的脸被蚊子给叮咬了的占多数。人们在散场归家的途中,往往会一边议论着电影,一边谩骂着蚊子。
看露天电影,还得看天的脸色。它和颜悦色,不下雨,不起狂风,你观赏得也就滋润。而如果看着看着突然落了雨,人们又没有预备雨具的话,那简直就糟糕透顶。人们撇下板凳,纷纷挤进种子站的仓库,孩子哭老人叫的,像是一群难民。而如果遇到大风的天气,悬挂着的银幕被风吹得一皱一鼓的,那上面投映出的风景和人物全都变了形,人看上去不是歪嘴就是折了
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都不在我们小镇,它们是驻扎在山里的部队,一个离我们稍近一些,有五六里的样子,是十七连;另一处则要远很多,在打石场那一带,距离我们起码有十五里的路途,是十三连。老人们是绝不会去这两个连队看电影的,他们的腿脚经不起折腾了。而大人们就是去的话,也是选择十七连的时候多。能够去十三连的,都是如我一般大的孩子。大家相邀在一起,沿着公路,走上一两个小时,到达连队时已是一身的汗,而电影往往已过半场,看得个囫囵半片的。回来的时候呢,山路上阴风飒飒,再赶上月色稀薄的夜晚,森林中传来猫头
所以一说去十三连看电影,家长都不乐意,我们只有偷着去了。如果运气好,我们可以拦截到
因为驻扎在我们小镇附近的这两个连队经常放电影,我曾经认为世界上过着最幸福生活的就是那些当兵的人。连队的战士格外欢迎孩子们来看电影,他们会把自己的板凳让给我们坐,还会用茶缸端来热水给我们喝。当然,战士们对待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孩的态度,比对待我们这些十一二的毛头小孩更要热情,他们喜欢围坐在大姑娘身边看电影。
我们家的邻居有一个姑娘,叫青云,青云是个大姑娘了,她喜欢去十七连看电影。凡是有关电影的消息,最早都是她发布的`。因为十七连的战士跟她很熟。要放电影了,总有人给她通风报信。她个子很高,腰肢纤细,头发又黑又亮,喜欢梳两条大
爱上青云家的,是小钟和小李,他们总是结伴而来。小李好像是部队的文书,不太爱说话,又黑又瘦的。小钟呢,他不胖不瘦,浓眉大眼,肤色跟青云一样白皙,在十七连当伙夫,所以有时他会偷上一些豆油带给青云家。青云一烙油饼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十七连的人又给她送豆油来了。青云那时中学毕业,在家务农,那一年的秋天她去看护麦田,得了尿毒症,住进医院,不久就死了。她死的时候小钟正回南方探家,他回来后并不知道青云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而一直在连队没有下山的小李也不知情。等到又要放电影的时候,小钟和小李来到青云家,听说了青云的事后,两个人都呆了,小钟还落了泪。人们依据泪水,判断青云跟小钟是一对,小李只不过是个陪衬罢了。
青云没了,我们得知电影消息的源头也就断了。从那后,我们很少到十七连去看电影了。不久这个连队就换防到别处去了,他们留在营地的,不过是几顶废弃的帐
前不久,托孩子的福看了场电影。放映厅装修气派,视、听效果俱佳,再考虑到偌大一个厅总共大小四对观众,都不好意思说七十元的票价贵了。只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由得想起小时候人山人海免费的乡村露天电影,它为我相对单调贫乏的童年平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以至于我对电影的记忆大部分来自那个年代。
公社放映队由两个大姑娘组成,她们的鼎鼎大名连几岁的孩子都能脱口而出。来了新影片,就会轮流在公社下辖的几个大队各放映一次,而我们大队有十个生产队,每十场电影各生产队才能轮着一回。当然,对于从小独自上学、即使打架也不麻烦家长的农村孩子而言,只要有消息,就算周边大队,我们也会欢呼雀跃组队前去,尽管偶尔也会因信息有误败兴而归。
如果是本生产队放电影,坐拥主场之利孩子们心情当然激动,洋洋得意地在同学面前散布消息,许诺给谁谁留座位,但其实这是空头支票,一则夜幕下黑压压一大片人头,找人并非易事;二则组队去看客场,统一行动更为重要。白天,队里会安排两人去上一个放映点挑设备:两副担子,一副是木头箱装着的放映机、发电机和幕布;一副是铁皮盒装着的影片。放映地点通常是各个生产队的禾场,这里地势开阔、地面平整,我们队的禾场就是队里唯一的一块水泥坪。黄昏时分,禾场的一端临时竖起两根笔直的杉木柱子,正方形白底黑边幕布的四个角以及音箱用绳子牢牢系在柱子上。正对幕布十几米远处摆一张方桌,用来安置放映机,桌子的一条腿上绑一根竹竿,顶端挑着一盏灯泡。而为了减轻噪声,汽油发电机则根据电线长度放在较远的地方。从立柱子时起孩子们就会时不时溜出家门关注着禾场里的一举一动,大人们提早收工准备晚饭,同时不忘提醒孩子们扛凳子占据有利位置。最好的位置当然是放映桌的四周,不仅视角正,而且可以看到影片进度以及放映员换片情况。虽然物资贫乏,大人们一高兴,也会炒些黄豆,每次母亲抓给我一把,多得需要我双手去捧。
放映员的食宿安排在队里体面的人家,通常是队长本人家里。对此我从小就能坦然接受,反倒是如今京城的基层政府还坚持着年底慰问贫困党员,据说住廉租房的小公务员送温暖时发现对方的家比自己家更“温暖”,安抚的话竟无从说起。以我的狭隘,排除疾病、事故等意外因素,允许自由发展的现阶段党员还需要救济,真不知如何体现其先进性? “贵宾”们用完晚餐夜色正好,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气定神闲地用绳索缠绕发电轮,猛地用力一拽,发电机突突响起,放映桌旁的电灯逐渐明亮。借着灯光,放映员摆好放映机并开始调试,以确保光影正好覆盖幕布的整个白色区域。放映机前方的孩子们则不失时机地伸出一只只小手在逐渐发散的光柱中挥舞,一个个黑色的手影出现在幕布上,引来一阵笑骂声。一切就绪,若是队长无意威严地讲几句,电灯一灭电影正式开始。
一般而言,正片之前会有二十分钟左右的一个加映,通常的名字叫《祖国新貌》,主要介绍科技、工业和农业的先进典型。虽然与周围的现实相距甚远,但我依然相信他们一定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某个远方,自豪感和向往感油然而生。
如果记得没错,一部电影大约四到五个片子,也就是说放映员要换片四到五次,而拥有两台放映机的文明铺区电影院,则可以做到基本上无缝换片。放映机上两个影片盘,前满后空,放映时胶片由前向后缠绕,当前一个盘全空时就需要换片,打开电灯,放映员将前面的空盘调换到后面,事先准备好的下一个放映盘则挂到前面。换片的间歇整个场地开始嘈杂,主场的家长们会大声吩咐孩子们回家“舀杯井水来”,他们并不一定是炒黄豆吃多了口渴,更有可能是放心不下家里,毕竟队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外人,而孩子们则不情不愿,即使渴得喉咙冒烟。电影很快得以继续,放映员借助另一张空盘将刚换下的胶片盘倒带以便下次使用。有时会因为胶片放映次数过多出现断片情况,放映员只好再次开灯,将断片头继续缠绕至后盘。得以延续的电影或多或少地跳过了一些情节,如果失去的恰恰是关键镜头,会引来一片“哎呀”声,这种懊恼之情现在也会碰到,当你看电影或电视剧时,前一秒男女正宽衣解带,下一秒天就亮了,你一定想骂广电局的娘,因为很可能正是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自己“审查”完了就毫不留情地剪掉一些镜头,全然不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因为经过大致选择,有电影的晚上天气通常不错,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如果仅是刮风,随着幕布前后摆动,电影人物和字幕会发生些许变形,又或者只是有点儿小雨,银幕上淡淡地出现一条条细线,大家会克服困难坚持将电影看完。但如果雨越下越大,放映员会说“今晚放映到此结束,谢谢观看“,意犹未尽的观众们只得嬉笑着各自跑回家。
若是客场,影片是否看过不是问题,问题是父母能否放行。父母“开恩”当然是有条件的,一是努力帮着做家务;二是至少让他们相信家庭作业已经完成;三是同去的人数足够多,最好有大人领队。好位置当然不能奢望,能在开演前赶到就不错了。个儿高的还可以站在后面,孩子们则会寻些干稻草圈成一个草垫子坐到最前排,因为离幕布太近,脖子仰得生疼。偶尔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也会去幕布背面观看,人物和字幕都是反的,很是影响观影效果。电影结束后,点齐人数一同回家。行动一致只是开始,不一会儿,孩子们就受不了大人的不紧不慢,把先前的草垫子变成一支支火把,不顾劝阻与同方向其他队的孩子一起飞奔而去,在蜿蜒曲折的田埂上跑成一条长长的火龙。
当年看电影的情形大体如此。至于内容,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但为了说明乡村电影对孩子们的深远影响,只好勉为其难例举一二。最先战争片毫无疑问是孩子们的最爱,所以,当八一电影制片厂硕大闪光的五角星片头出现时,无论是早期白边黑底,还是后来黄边红底,都会引起一阵欢呼。同样原因,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农兵塑像片头也颇受欢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上甘岭》等“打仗”的电影,简单“粗暴“、爱憎分明,一遍又一遍百看不厌,经典镜头和台词常常被孩子们挂在嘴边。我至今记得《平原游击队》里,队长李向阳带着任务回村时,鬼子炮楼前的更夫煞有介事梆梆梆地敲着更喊着“平安无事喽”,孩子们把这一幽默变成了晚上呼朋引类的暗号。我们还发明了一种名叫“打枪”的游戏,根据手心手背大致均分为敌我两队,各自散开后便“兵戎相见”,只要再次发现“敌人”,“Pia”的一声然后报出“敌人”的名字和位置,对方就必须离场。被对方发现就意味着“死亡”仿佛人人都是神枪手。无规矩不成方圆,游戏也是如此,虽然这些规矩未必讲理,就如魔兽争霸里,残得哪怕只剩一滴血的兽族剑圣,一个跳劈照样可以用长长的“西瓜刀”将脆皮的人族大法师砍个人仰马翻魂归祭坛。
后来则是武侠片独领风骚。《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南拳王》《神鞭》,无不引起孩子们对十八般武艺品头论足争论不休,以至于班上一向不起眼的胡姓亲叔侄俩儿地位猛涨,因为他们家胡德彪老爷子跑江湖卖狗皮膏药专治跌打损伤,在我们眼里俨然武术世家,虽然年长的侄儿打哭叔叔时用的招数跟我们平常泼皮无赖式打法并无二致,但谁又能确定他们不是“艺不外露、藏巧于拙”呢?其实,我一直固执的.认为我看的第一部武打片不是《少林寺》,而是《神秘的大佛》,里面有:古刹、和尚、宝藏、帮会、软鞭等武侠元素,尽管武打场面少而简单。对这部电影情有独钟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剧中人物“小和尚”成了班上一个发短头尖、眼小脸长同学的外号;二是剧中常以花脸出现的大反派“怪面人”启发我们制作面具晚上出来吓人。我们的做工相当简单,就是撕张作业纸掏几个窟窿,再用墨水、锅底灰弄些图案,而当我透过自己的面具看到对方的面具时,其实有些失望,恐怖效果完全来自臆想,只不过大家都在“做戏”罢了。直到某天孩子娘贴着护肤面膜出现在我眼前,禁不住心生感慨:如果当年能有这样一张神器,绝对吓得小伙伴们噩梦连连。
谍战、反特片如《保密局的枪声》《黑三角》,情节紧张扣人心弦,尤其前者风流倜傥的我党特工,打入敌人心脏凭借机智和勇敢一次次化险为夷胜利完成任务,大受孩子们喜爱。喜剧片《笑比哭好》《快乐的单身汉》轻松幽默,时不时引起大人、小孩儿一阵笑声。农村题材电影《月亮湾的笑声》《喜盈门》,虽非孩子们喜闻乐见,却常常成为大婶、伯娘家长里短的谈资。节奏拖沓的戏曲类电影的确不太受孩子们喜欢,但至少《徐九经升官记》和《卷席筒》例外。前者,徐九经扮相滑稽令人捧腹,同时他不畏权贵智断争妻案让人拍案叫绝;后者,小叔子替蒙冤的嫂嫂顶“罪”赴死大义凛然,刑场上被同父异母高中状元、巡抚家乡的哥哥所救后,故意戏弄嫂子,几次滚开嫂子为他裹“尸”的草席,令人大呼过瘾。还有些电影尽管内容已然模糊,但我忘不了他们充满诗意的名字,例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待到满山红叶时》《野火春风斗古城》。当然,偶尔也会见到译制片,例如罗马尼亚电影《复仇》。孩子们记不住外国人拗口的姓名,分不清他们各属什么阵营,只好用“好人”“我们这边的”“坏人”“敌人那边的”来进行角色描述。还记得一部《新天方夜谭》,这部电影里吸引孩子们眼球的元素很多:孩子作为主角、飞毯、王子和公主、魔法宝石和法力无边的玫瑰花。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电和电视的普及,尤其录像机的出现,露天电影逐渐退出乡村舞台。当然,也短暂出现过个体放映户取代体制僵化的公社放映队,受邀于红白喜事,但终究市场过小难以为继。
《新天方夜谭》里,仙女因为感激被从桃核里解救而送给小主人公一颗宝石,说是可以救他三次性命。第一次小主人公因卖宝石而被贪婪的恶棍逼入绝境,借助宝石他和小猴子夏克蒂莫名其妙上了飞毯;第二次用在了他被假国王的卧底推下飞毯;第三次则是让王子起死回生。回忆到此处,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说是救命三次,其实前两次明显被宝石所坑,最后一次也似乎事不关己。从而我推导出一句似乎颇些哲理的话:上天给了你某种天赋,并非他想让你因此获益,而是自以为是地赋予了你责任。但短暂得意之后是长长的悲哀,我发现自己早已不再单纯,看电影、电视剧时也会如大多数成年观众一样,“理性”地分析其是否合乎逻辑、哪个镜头穿帮了:比如女战士是否能从裤裆里掏出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古装戏里出现了高压线架、皇帝手腕上金表晃眼等等。正因为所谓的“理性”从而挑剔,即使再给一场乡村露天电影,我也找不回当年单纯的快乐。
有一些事,在记忆里,淡淡的都被遗忘,或沉默在岁月的长河里了。有一些事,在不经之间,轻微触碰,便就会从心底泛起。也带着点点斑斓的印迹,模糊不清还残留在脑际里那么一丁点,记忆里的思维。回想起来,那己过去的岁月,觉的,有一种淡淡的感觉……。
茪荫任茬,三十年岁月,戛然而去。曾经记的,那小时候,看过的电影,连环画,之类的影片,小人书。现在回想起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印象了。也叫不上它的名字了,但也记不得看过的内容了。只是那时候,特别喜欢的,看的,还是那些,什么武侠影片。崇拜那些电影里的`,什么武林高手,和那会飞的那侠客的轻功。那什么,那大俠的,所为什么很历害的,是那一种绝招。每看完一场喜欢的电影,就讲电影的谁的武功最高,那么历害,
甚至,回去弄—个袋子装上沙子,偷偷的,也是练个起来,练个不停。那时候,听说附进那里有过事的,准会问,“演电影不演”,或,“有电影没有”,知道消息了,晚上就再也坐不住了,是非要是一定要去看的。
昨天,在傍晚时分,夕阳也坚守它一天的侍命,逐渐隐曦在山的,那一边。晚风带着冬季的寒意,掠着正个山坡,在山坡上忙碌的我,在吃过晚饭的时候,村里,大队的耸的高高的,高音喇叭里,荡过来了刺耳的声音,飘进了我的耳朵里,喃喃的听到,“晚上大队六点,放电影了,有空可以去看了”。
对于我,这现代的时代,早已跟以往不同了。电影我早己不感兴趣了,电视,电脑,碟子,基本上随时看,随时有。也不觉的稀奇,平日忙碌也是很少看电影的。对于,我小儿子来说,看露天的电影,那是稀奇,还是头一回,带着多少年,没有看过露天电影的我。吃了晚饭,带着一份稀奇,便跟儿子一块,去大队戏园,欣赏露天电影去了。
电影的放映处,便是村里的戏园,残破的院落,堆积了许多杂物。粗大的泡桐,和杨树,闭涩的长在墙角落里,院里人数渺渺无几,泛白的影布,晃动的画面,衬盎着士地上那凌乱,泛白的残雪,在月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茫。
去了,电影早以己开始了,声音响亮,划过了长长的夜空。月光青辉,在夜晚那萧风的掠过时,拂在身上一陈冰凉。厚厚的棉衣,也阻不了袭来的寒气。望着依析的放影画面,觉的,有一种冷漠,凄清的感觉,直袭着我的眼窝。
没有小时候的那份热狂,也没有儿时的那份激情,儿子说“这是啥”我说,电影机子。儿子,不停的围着放影机东瞧西望,转来晃去。
看着这电影,朦胧模糊的我,于是,我抖抖身上的的烟灰,看着儿子,对电影放映的画面,头也不回,一阵稀奇之后,儿子说,“回了走”,“爸!”,那走吧,一留烟的匆匆的离开了零星散乱的人群,奔像一股寒风之中。
今晚,来了一场稀奇的电影,却看了一会不是滋味的感觉。那一种儿的。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岁月里,诉说着,那己远去的故事,故事!还带者点那暖暖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