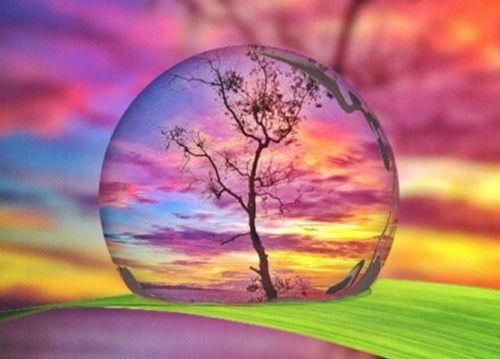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我最大的目的就是领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来参加这个招待会。”
——12月6日,莫言出席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关于“来斯德哥尔摩除了领奖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时,他如是答。
“我知道我得奖后,马悦然先生背了很多的罪名。我和马先生只有三面之缘,我们只是三支烟的感情,他多抽了我一根。马悦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令我佩服。”
——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莫言回应与马悦然私交甚好的传闻。
“我要学习这位先生(瑞典演员约翰-拉巴乌斯)站起来读。但是我不管是站着读、还是坐着读,都没有他读得好。”
——12月9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朗读自己的作品《狼》时,老实地评价了自己的水平。
“莫言老师你幸福吗?”“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我起码今天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的读者来听我讲话。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上神秘的笑容。因此我幸福。”
——这段对话发生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莫言在朗诵结束之后接受师生提问,一位男生抛出了这个时下很流行的话题。很显然,莫言也知道这个流行语,迅速给予反问。
“中国现在文化多元化,每个人可以很方便地把时间消磨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文学,那样电影导演、音乐家不都没饭吃了,就饿坏了。”
——12月9日,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对中国严肃文学前景表示担忧,但莫言认为“不必过于担心”。
“我父亲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莫言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后仍然是农民的儿子。”
——12月6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述自己的生活态度。可以看出,他没有失去农民的那份淳朴。
“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问莫言得奖后的“烦恼”、“喜悦”,莫言吟诗作答。
“我过去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没有人来理睬我。前几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走,好几个年轻姑娘追着我照像。我一下知道,哦!我成了名人了。”
——12月6日,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莫言谈获奖后自己生活的“小小改变”。
“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解读自己的名字。
“如果要问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最希望回到我的书桌前坐下写小说。有人说一个作家获得诺奖后他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了。但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要努力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打破这个魔咒。”
——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莫言谈自己眼下最大的愿望。
“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谈自己的创作灵感。
“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谈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
“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谈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他没有用处。”
——12月11日,莫言在诺贝尔晚宴上的致辞。
“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政治奖。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
——12月6日,莫言出席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时谈自己获奖的意义。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12月8日日,莫言在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谈文学创作。
“历史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活在历史之中,所谓的现实马上会变成历史。因此所有的现实都是历史的延续”。
——12月9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与师生交流时谈历史的重要性。
“越是优秀的作品,越是容易被曲解。只有主题明确简单的小说才不会被曲解。中国有部《红楼梦》,中国人一直在解释,越解释越糊涂。”
——12月9日,斯德哥尔摩大学。主持人问莫言如何看待读者不理解他的作品内容。
我在河之彼岸,守望曾经归来,归来无望。
月光下,我用繁冗拖沓的文字祭奠我的青春,纪念我死去的友情和迟到的爱情。
因此,在那个习惯于悲春伤秋的年代,你陪我看了多少个日薄西山的景致,我陪你看了多少个破晓阑珊的夜,我们彼此静默的坐着,不言朝夕。
即使世界遗忘了你,也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在你生命的伊始之日,道一声:生日快乐!
无论多么落寂和苍茫,那些身影总会过目不忘。
总在不经意的年生,回首彼岸,纵然发现光景绵长了十六个年头。
因了命途中的你们,我才没有荒芜了青春。
我把你们的故事收入我的音筒,放在生活之上,我的记忆之下,
提笔伏案之年,窗边,是心灵奔向青春的.黑色河流,突兀的世界。
有些人,在不经意间,就忘了;有些人,你想方设法,都忘不了。
我总喜欢逆着时光,寻找我青春的足迹。
当笔下肆意挥洒的心情化为文字,我将用它记录永生。
黄昏是青春短暂的悲伤。
所以,兵荒马乱也要轻装简从。
回首,才看见我们是以快乐的心情写悲伤的青春。
满腹经纶是黔驴之技,易于迁延与迟滞。
当时光碾过青春,我将以快乐注解悲伤。
在年生里,我们因无知荒唐而美丽。
把每一个句子后面加一个完结的句号,记作虚无而迷惘的守候。
久远是迷途里酝酿的酒,愈陈愈香。
安然的在被窝中躺过一世春秋,浑噩自知。
极度的顺从是悖逆。
呆坐在眼睛里的空洞和茫然,凝结成氤氲的哀伤,在青春的天空渐渐延伸和漫散。
我们总是以诗般的语言刻画自己在青春的罅隙中的那般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