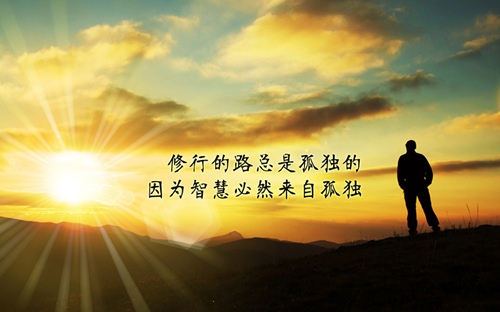2017年芒种优美
布谷鸟,我一直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每年春夏时节,清晨,人们还没起床,布谷鸟的叫声便不绝于耳。“咕咕——咕咕”的声音很大,音调圆润,清脆悦耳,酷似“光棍儿——好苦”,以致成了开玩笑打诨对方的戏语。习惯了北京城里生活的人们,从小就认同了这种叫法。所以,只要听见布谷鸟叫了,就知道,芒种到了。老人讲,“芒种、芒种,过了芒种,不可强种”。有的庄稼该收了,有的再不种就来不及了。稍稍大了一些,知道有个节气叫芒种。
芒种,是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的意思。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每年的6月5日左右,太阳到达黄经75°时为芒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指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故又称“芒种”。
芒种时最适合播种有芒的稻谷类作物。有一种说法;播种一定要在芒种前完成。过了这一天,即使播下种子也没有了收成。这种说法有无根据,从来没有人质疑过。
印象中那是个特别纷繁的季节。我年轻时在东北兴凯湖下乡,同样是芒种前后,气候却是与北京大不相同。北京人已穿上单衣迎接夏天了,兴凯湖的积雪还没化干净呢。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枯草丛生、荆棘满目。只有雪化冰融汇成的潺潺流水,预示着春天来了。
兴凯湖的春天,比北京要晚上两个月,虽然已不像冬天那样寒冷,但一早一晚仍然是寒气逼人。五月至六月初,正值这里最忙的季节。兴凯湖——这里的大米好吃,但是种水稻的活儿却是十分艰苦。每年芒种前,必须把经过培养的种子播下去,否则秋天将丰收无望。对于我们这些城里来的青年人来说,不仅播种的农活没干过,见都没见过。
那天,我们到了地里,举目一看,只见一望无垠的水田,真是壮观。再往脚下一看,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水田里薄薄的一层冰在天光的照射下反着白光,顿感凉意由脚下袭来。
人拉播种机,一米多长,中间一排漏斗,两面一边一个木轮儿,木轮插满了叶片,中间有条绳子。拉播种机的人把绳子往肩膀上一套,拖拉着播种机在前面走,种子就播在了地里。这活儿看似简单,干起来却非常累,别的不说,就是光脚往水田里一站,光凉劲儿就够你受的。
那时候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带头儿的,就有跟着的。
年青时思想单纯,对工作更是满腔热忱。下乡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满脑子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看着先到水里的人痛苦的表情,心里着时犯怵。
“怎么样啊?哥们儿,行不行啊!”站在田埂上的人们尽量地拖延。
“够呛!你下来就知道了!”
北京人有句老话:发昏当不了死。豁出去了,来吧!咬了咬牙,脱了鞋袜裤腿儿一挽,飞身跨到田里。嘿!那叫一个凉。
划割肌肤之痛,冰冷透骨之感使人倍感难受。脚下淌着碎冰,不一会儿,变得麻木没有了知觉。等一拉起播种机就更不用说了,一脚下去,稀泥有近半尺深,脚下冰水侵袭,身上自觉寒冷,逼得人们不由得的向前奔跑,劈沥啪啦,溅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田根据地形高低,大小不同,短的几十米,长的一百米,两个来回儿下来人已累得气喘吁吁,但是心里毕竟不觉得那么冷了。就这样,每天要工作要十个小时以上。虽然当时没有一个叫苦的,但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不管你是谁,也不管是哪儿的人,只要下到田里,就不可能不干。
兴凯湖的春天,天气变化无常。早晨还是晴空万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变天了。这里变天儿,一般先有预兆,多是扑面刮起一阵冷风,紧跟着乌云翻滚着涌了上来,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剎时间,就让你领教什么是瓢泼大雨。这雨下的,十几米以外就看不清人的面孔,密集的雨点儿砸在人们头上,让人发懵。
大家谁也没有躲的念头儿,因为知道也没处躲,况且,这时又有谁愿意当“逃兵”呢?大雨滂沱,天昏地暗,人们呆立在水田里,如同一樽樽石雕蜡像,任凭密集的雨点砸在身上、肩膀上,生疼生疼的。人们无奈地听凭着大自然的洗礼。
时间不长,随着头顶上的黑云散去,雨过天晴,接着依旧是阳光灿烂。沐浴着雨后的阳光,清晨的寒冷,劳作的辛苦,早已被洗刷得干干净净。
“咕咕——咕咕”,不远处布谷鸟的叫声不断提醒着人们,今天是“芒种”,必须把所有的种子播撒在田里。干吧!无退路可想,大家振奋精神,拉着播种机在水田中飞快地奔跑。人们仿佛忘记了劳累,只有一个念头,把所有的种子播完。
夕阳西下,通红的晚霞,浸染天边,水田中斑驳的身影终于停了下来。这时,有人发现田埂上还有两包种子没有用完。连长吩咐大家,每人动手,就是手捧,也要把它分完。黄橙橙的种子,画出优美的抛物线,射向空中,又散落在水中,溅起了无数小小的水花。地平线上渐行渐远的红光,映照在大家古铜色的脸上。漫天飞舞的稻谷,水田里人们挥动的手臂,形成了一个多么曼妙的画卷。
“咕咕——咕咕”,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听到这熟悉的叫声,眼前总会浮现出那年那道风情,稻谷的种子,金黄色的种子,嫩芽白白的,纷纷扬扬的飘向空中,迎着落日的余晖,缓缓的,洒在了肥沃的土壤中。
芒种,曾让我们懂得了“春不种,秋不收”。过了芒种,不可强种。
2017年芒种优美散文【篇二】
像一位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好汉,像一位急急忙忙回娘家的少妇,芒种,就这样匆匆行走在麦香的田野上,站立在五月的节气中,循环在岁月的年轮里。
林清玄说:“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高粱的波浪是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的盛放是芒种。”热情的太阳,用它最尊贵的金色,为这个节气定格了永恒的色彩;多情的月亮,用它最皎洁的月华,为这个节气披上了梦的衣裳。
节气,吐露着大地的心事,响应着万物的成长。一年一度,年年岁岁,节气都迈着同样的步伐,却带着不同的心情,像报晓的雄鸡,像赴约的情人,如约而至。
“芒种”是立春过后的第九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思是指小麦、大麦等有芒作物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大豆、玉米等大秋作物正值播种,又是播种的季节,所以称做“芒种”。芒种的两头,一头连着收,一头连着种;一头辞旧,一头迎新。
辞旧迎新的中间,是农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勤劳和辛苦,是农家“连种带收、样样都忙”的忙碌和紧张,是“春争日,夏争时”的“三夏”大忙季节,也是诗人“东风染尽三千顷,折鹭飞来无处停”的诗情和画意。
清澈明亮的阳光下,一些红杏已经出叶,一些石榴正在开花;而一些小麦已经走过“三秋”的苍茫风雨,穿过“三冬”的冰天雪地,经过“三春”的姹紫嫣红,来到“三夏”的大忙季节。
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到处都是忙碌着的农民,古铜色的脊梁,闪烁着收获的喜悦,挥舞着的银镰,诠释着芒种的内涵。如雨的汗珠、发烧脸庞、酸疼的脊背、干裂的嘴唇,是麦田里的农民对生命最原始的体验,对光阴最深切的感受。
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提篮送饭的小女,小心翼翼的走在热火朝天的野径上,路傍的田地,昨天还是金色的麦浪,今天已变得碧波荡漾,清新鲜活。黝黑的土地饱尝了艰辛的汗水,躬耕的田亩亮出了别样的风景。
芒种时节的农村,虽是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但大观园里的红楼女儿们,却情思袅袅,闲情似梦。如花似玉,冰雪聪明的红楼女儿,面对百花凋零、红消翠减的景致,自然会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于是芒种这天,她们在天上人间的大观园里,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花神仪式,饯送花神归位,亦表达水做的女儿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
千古名著《红楼梦》记载了这一盛况: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颗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大观园里的女儿们都齐集饯行花神,充满了浪漫与欢喜,到处可闻听到女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所以这一天也称“女儿节”。
经典里的芒种,濡染墨香,千古风流;季节中的芒种,耕耘日子,收获光阴。站在芒种的节气里,眼前清风拂动的绿柳,翩翩起舞的蝴蝶,正在演奏一曲芒种的节气歌,远处夕阳下归家的牧童,晚风中荷锄的农夫,正在描绘一幅盛世的和谐图。芒种,经历了夏日的雨淋,经历了熏风的陶染,经历了辛苦的耕耘,缓缓的融入秋日的成熟。
1.
2.
3.
4.
5.
6.
芒种的优美
每年的芒种节,都是农事最繁忙的季节,即所谓“芒种忙,乱打场”。这个时节,正是新麦登场,石磙在麦场上被老牛拉着“吱扭吱扭”滚动,轧着小麦的时候。生命中经历的几十个芒种节,在记忆中多渐渐淡去,留下的只是很少几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那个芒种节,虽然至今已经60年了,我却记忆深刻。那年,麦子已经收获,黄豆也已经种下。恰逢端午节,而家里除了新收的麦子,并没有其它什么好吃的。那天上午,十几岁的哥哥带着六七岁的我下到湖里捉鱼。哥哥什么也没带,我也只挎了一只小篮子准备装鱼。我问哥哥怎么捉?哥哥没说什么。来到湖边,哥哥脱掉鞋子,卷起裤腿,下到水并不太深的湖里,我在岸上看。转眼工夫,哥哥竟然摸到一条大黑鱼。现在想来,那条黑鱼也足有两斤重。也只有一个小时多,哥哥摸到三条大黑鱼!哥哥告诉我,黑鱼一般都卧在水底的淤泥里不动,好捉。
那个端午节,我家美美地吃了一顿鱼汤泡馍。那鱼汤真鲜!那件事,也是脑海中我与比我大8岁的哥哥在一起的最美好的记忆。在之后的生活中,我与哥哥各走各路,没再有什么交集,也就没什么话题可说。这是题外话。
在此之前的另一个芒种节,反正与吃黑鱼的芒种节靠得比较近,我为家人惹了一个大纰漏——我的脚割破了。
那应该是国家实行互助组之前,土地还是自有。那天,老家的叔叔们也来了,大家一起割麦子。吃过午饭,父亲把上午用过的几把镰刀又磨了一遍,放在门后以便下午用,就去午休了。放在门后,大概就是怕小孩子乱动。他们哪里知道,我偏偏动了那刚刚磨好的锋利的镰刀。我竟然把其中的一把镰刀拿过来,把右脚放在刀口上!顿时,脚被割破,鲜血涌出!我惹大祸了!我一声惨叫,惊动了父母亲,他们一起都来了。父亲把我抱起来,母亲用高粱面朝我的脚伤处敷,流血止住了。现在回忆,当年也只是四五岁年龄。奇怪的是,父母亲并没有骂我打我或者训斥我。随着渐渐长大,记忆更清晰,也始终没有父母打我的记忆。我意识到,我的父母亲是多么疼爱我!我的右脚被割破的伤疤至今还在,它与父母亲的疼爱留在心中一样清晰。
大饥荒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已经是一个即将上中学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却吃不饱饭。但只要学校放假,我就像大人一样下地干农活,为家庭挣工分。那年的6月初,我到区中学参加升初中
大约有20年时间,与芒种节年年都是“无缘对面不相识”了。真正又过芒种节,是最近二十几年。
这些年,我数次与妻一起去农村亲戚家,帮助收麦子。说是收麦子,其实就是做些协助的活儿,比如往车里装麦子,捡落下的麦穗,摊摊场,自然,也会弯下腰割一会儿麦子。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实行,现如今的农民真的彻底从土地里解放了,他们不用再弯着腰一把一把割麦子了,自然更不需要我这个帮忙的人那样劳动了。尽管如此,芒种时节只要来到农村,还是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农忙味儿,像“起五更睡半夜”,“泼麦摪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等等,都涌满胸怀。
参加全省午收开机现场会,是我最近几年过的最“隆重”的一个芒种节。那天,在我省小麦主产区的我市,又在麦田一望无际的南照镇。下了车,立即被满眼的金黄所感染。现场会就设在地头,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早已摆开阵势,只等一声令下。果然,简短的开机仪式结束,与会的最高首长高喊一声:“开机!”各台收割机立即马达轰鸣,驶进麦海。一垄垄麦子被机器吃进,转瞬吐出麦秆,麦粒则装进机器的袋子里。这是我这个已进入老年的过来人见到的最壮观的麦收场面。
回望刚刚使用过的午收开机现场会会场,突然,那会标令我感慨起来:记得十年前参加过一次市里举办的全市午收现场会,那会标上写的是“开镰”,现在会标上则是“开机”。一字之差,浓缩了多大的时代变迁啊!今天的农民再也不用那么“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了。今后的芒种节会更有新意的。
芒种的优美散文【篇二】
芒种,是在布谷鸟固执的鸣唤中分娩的,是在农民的擦拳磨掌中跑来的,是在跳出农门的农家子弟的惴惴不安中闯来的……
进了芒种,便是仲夏了。《易经》将八卦之一的离卦置于仲夏,而离卦象征太阳,象征火,又含有丽之意,是附丽的意思。事实上,芒种时节,一方面万物生长尤其离不开太阳,要依赖于太阳的光和热;另一方面,那些刚收获的麦类及油菜等农作物也离不开太阳,必须晒干了才能收藏。于是在古人看来,将离卦置于此,其实就是在强调“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一最根本的自然规律。
元人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说:“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徐锴解释:“谓麦谷为芒种是也”。老祖宗创建芒种这个节气,其初始本意就是表示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有时细细想来,真得佩服老祖宗的聪明与智慧。他们在科学极不发达的春秋秦汉时期,硬是凭着仔细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准确地划分出了二十四节气,并且沿用至今。
芒种时节,微醺的南风成天一个劲的吹着。它有时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小娃娃,翻着筋斗地在麦穗上跳跃着,撩逗得麦穗舒服地摇晃着,沙沙的笑着;有时,它看见紧紧趴在麦穗上的花大姐(七星瓢虫)还在呆头呆脑地、执着地捕食着蚜虫,就恶作剧地将它吹下去,看着可怜的花大姐跌得头晕眼花,它竟嘻嘻哈哈地跑远了;它时不时地轻轻地掀起人们的衣衫,或者调皮地吹掉人们头顶的草帽,吹乱人们的头发,给人们制造点小小的麻烦;它有时又像是一张温柔的大手,轻轻的拂过那一望无垠的麦田,麦子簇拥着,摇曳着,做着积极的回应,于是,麦海里,金色的浪头就一波接着一波地漾向远方……
乡间小路上,来来往往看麦子的人骤然多了起来。他们慢腾腾的走着,时不时地停下,掐两穗麦子,搓一搓,揉一揉,放在手心数一数,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收成;偶尔,捏起一粒扔进嘴里,享受着满嘴新麦清新的气息,对于割麦的时辰,肚子里便有了一个底。在地头上,大家聚到了一起,看着麦子的成色,相互品评着各自的收成。
芒种,是农民的节日,是收获的开端,丰收的起点。芒种的命名并非一句完整的话语,也非一段优美的抒情,而是一个带条件的假设句。虽然生活已带给我们很多喜悦,但前面的云霞还不知道色彩。多少年来,对芒种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只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始终黏附在农村的温床上。看着天下雨,就不由担心起母亲的油菜是不是又要欠收了,小麦是不是晚熟了。这是一个需要强烈的阳光炙烤的时令。雨水应该节制一些,少一些,太阳应该灿烂一些,骄一些。若没有锋芒毕露的阳光,便没有翻滚的麦浪和金黄色的麦芒,便不是虎口夺食的端午,便不是抢收抢种的季节。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合着中原的气候特征。豫北平原处于黄河中下游,因而,历书中对节气的定义可以说是对豫北气候的准确描述。芒种在历书中又称五月节,每到这个时节,青涩酸牙的杏儿慢慢地变黄变甜,满村的槐花均匀地洒落一地,像薄雪;枣花也开了,拇指大小的椭圆叶片根部,碎金一样的花儿吐露出细细的香,淡淡香气盈满巷子,招引着采花的蜜蜂。石榴完全丢弃了羞涩,满树艳红,一朵一朵的喇叭,唱着芒种时节的高音。香椿的花一大串一大串的,显出一种很俏的白。艾的茎粗壮,叶已开始翻白,为着端午节走上各家的门楣而努力着。
信步走出村子,村边梨树的果子已如蒜头大小。经冬的大葱和萝卜,都孕育了种子,紧紧地抱着。四周全是麦田,无边无际,风过麦海起波起浪。对于豫北而言,芒种时节收割的不仅仅是麦子,还有大蒜,种的也不止是谷子,同时有大豆、玉米、花生、芝麻、绿豆、晚棉等等。还要把育好苗的辣椒、茄子、西红柿等蔬菜,种进地里。因此,俗语的三夏大忙“收、种、管”,需要招前顾后,哪一头都得罪不得。虽然十好几年没有割麦、放磙、扬场了,但想起来就背上发疼、脸上发烧、胳膊发软、嘴唇发干、心里发慌!就想起一大早的布谷叫,想起麦棵中刺脚的萋萋芽,想起一片云影移过来时的清凉,想起故乡麦地的爹娘!
走进乡村,站在地头,望着金黄色的麦子,记忆在麦芒的扯动下,瞬间里展开了一幅幅愰在眼前的画卷,这些画卷有童年的也有青年的,它们总在麦田间若隐若现。
记得小时候,对放麦假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心情,在“吃杯茶”的声声鸣叫里,眼巴巴地盼着。终于有一天盼到了一纸《夏收公约》,放麦假了!于是一帮娃娃们推搡着、打闹着,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定下了这个夏收捡拾麦穗的目标。此时,村里许多房前屋后的墙壁上,也被人们刷上了许多诸如“快收快打,颗粒归仓”、“当心火灾,安全夏收”的标语。夏收的气氛一下子被渲染了出来,人们顿时感觉到紧张了许多。
长大一些,才知道收麦是最累人,农民说那是累死人不偿命的活。靠天吃饭时,麦子长得稀用手拔,后来水利条件好了,水浇的麦子又粗又壮,就改用镰刀割了。芒种一到,无边的麦田翻起金色的麦浪,人们望着丰收的庄家露出欣慰的笑容,早早的把镰刀磨得飞快,养精蓄锐,就等着开镰了。俗话说:“麦熟一晌,蚕老一时。”早上还有些泛绿的麦子,经过中午干燥的熏风一吹,一下子就变黄了。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一起成熟了,收割不及时会焦在地里,白天收割就要掉麦粒。最能
芒种时节,在农村里没有闲人,中年人、青年人是麦田里的主要劳力,老人和孩子也早早的来到田地里做力所能及的劳动。实在不能下地劳动的老人才在家里打扫打扫麦场,还要附带着看年幼的孙子或孙女。那真是“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忙。三麦不如一秋长,三秋不如一麦忙。”
割麦子是一件既累又脏的劳动,无处不在的麦芒扎的人难受不说,弯腰弓背一镰一镰收割的架势,更是让人腰酸腿疼。落在麦棵上的尘土也在收割时再次飞起来,被吸入嘴里、鼻子里,嗓子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吐一口唾液,里面就有黑黑的东西一起吐出来。有风吹来,也是烫人的,似乎要把人体内的水分统统挤出来。腰和腿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按着后背直一下腰,一看,脸上的汗水和尘土早和了泥,个个都是大花脸。
芒种时节,承接着春播夏华,背负着一年的幸福和希望,抢割、抢运、抢晒,忙着收获成熟的金黄,翻耕、点种、载秧,忙着播种绿色的希望。广袤的原野田垄上,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处处是古铜色的脊梁。芒种浸泡在淋漓不止的汗水里,张望铁叉的光芒。黎明的晨光里,挥舞的银镰闪烁着丰收的喜悦,日上三竿的时候,抹一抹满脸的汗珠子,从菜园子里拔出一棵新蒜,疲惫地坐在躺倒的麦棵上,就着喷香的烙饼或者油条送进嘴里,顿时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似乎把一捆捆的成熟送给了新的生活。
芒种,刚把金黄浪涌去,便见新禾万顷新。它把整个五月喧嚣得充实而又底气十足。
十多年过去了,芒种的劳作景象已经大不相同。远处,一台联合收割机轰鸣着开过来,麦子们的震颤,传染一般,营造了金黄的麦浪;虽然,对于麦子们而言,已不再是农人手执镰刀弯腰的谦恭,但站在麦田地头,我亦然不会忘记,我是从麦地光着脊梁的长辈身上学会了坚韧、勤劳、感恩,也从麦田里收获了粒粒饱满的果实……
“芒种”两个汉字的组合,就像一茬庄稼与一茬庄稼的倒茬、接替,让季节变得充盈,也使人生充满了希望和梦想……
芒种的优美散文【篇三】
芒种前后,满树的杏儿便抛出一张张金黄的媚靥,惹得蜜蜂嗡嗡地围着香甜的杏儿转;惹得小儿手噙口中,盯着树上金黄的杏儿团团转。偶尔有一两个熟透的杏子落地,小儿发现了,便以极快的速度奔过去,捡起。顾不得擦土,扑通一声,急急地扔入口中,牙齿轻轻地一碰,嚼也来不及细嚼,咕咚一声咽下去,却愣是没尝出这杏是啥味!
满树杏儿摇黄的时候,也就是地里麦子由青转黄的时候。
随着气温的越来越高,太阳也越来越毒辣。漫山遍野的麦子也就一天一个样的变化着:麦叶干了;麦穗黄了;麦粒硬了;麦秆脆了……
微醺的南风这时候也在成天一个劲的吹着。它有时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小娃娃,翻着筋斗地在麦穗上跳跃着,撩逗得麦穗舒服地摇晃着,沙沙的笑着;有时,它看见紧紧趴在麦穗上的花花媳妇(七星瓢虫)还在呆头呆脑地、执着地捕食着蚜虫,就恶作剧地将它吹下去,看着可怜的花花媳妇跌得头晕眼花,它竟嘻嘻哈哈地跑远了;它时不时地轻轻地掀起人们的衣衫,或者调皮地吹掉人们头顶的草帽,吹乱人们的头发,给人们制造点小小的麻烦;它有时又像是一张温柔的大手,轻轻的拂过那一望无垠的麦田,麦子簇拥着,摇曳着,做着积极的回应,于是,麦海里,金色的浪头就一波接着一波的漾向远方……
天气是那么的明朗,空气是那么的透明。远处坐落在麦海深处的村庄更是那样的宁静祥和,显得在这样的太平盛世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惬意……
田间如带的乡间小路上,来来往往看麦子的人多了起来。大家一般都是慢腾腾的走着,时不时地停下,掐两穗麦子,搓一搓,揉一揉,放在手心数一数,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收成;偶尔,捏起一粒扔进嘴里,享受着满嘴新麦清新的气息,对于割麦的时辰肚子里便有了一个底。在地头上,大家聚到了一起,看着麦子的成色,相互品评着各自的收成。无意间,有人问,啥时芒种?有人就说,今日芒种。听的人一脸惊喜,眼睛随之一亮说,哦!今儿个就是芒种呀!
老祖宗创建芒种这个节气,其初始本意就是表示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有时细细想来,真得佩服老祖宗的聪明与智慧。他们在科学极不发达的春秋秦汉时期,硬是凭着仔细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准确地划分出了二十四节气,并且沿用至今。
过了芒种这个节气,就要开镰收麦了。经过一年的辛劳,眼看着到手的丰收景象,不管是谁,他喜悦的心情怎能按捺得住呢?所以,父辈们在每年芒种这一天的明亮眼神都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蓦地,在无垠的麦海里,一声声眉户小调传了过来,那一定是等待收获的人们幸福的吟唱。在风中,这悠扬的小调还带着些许的乡野气息呢!听着他们如痴如醉的吟唱,使我不由得想起帝舜做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我仿佛看见,在几千年前的晋南,人们在付出了极度的辛劳后,在将要收获的季节,帝舜和他的子民们面对丰收的景象,沐浴着和熙的东南风,陶醉地,顺口吟出了名传千古的《南风歌》。是呀!在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在尧舜禹的故乡,只有我们这些辛勤劳苦的乡人们,才有资格吟咏这名传千古的《南风歌》!
村人们在眉户小调的音乐中回到家里,心里便有了数:哪块地的麦子熟得早,哪块地的麦子还得放两天……
此时,碾麦场早已经压光扫净,就光等着新麦入场了。家庭妇女们也闲不下来,她们满脸汗满手面地忙着为夏收季节准备干粮;铁匠铺也成天叮叮当当地响着,一块块的钢铁被烧红,经过锻打、成型、蘸水,一把把锋利的镰刀被打了出来,又安上长长的木柄,被人们买回家去。
县乡的集市上,这时候也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以卖杈把扫帚为主,人们就又称芒种前后的集会为“杈把扫帚会”。因为,一旦开了镰,谁也忙得顾不上赶会了,所以,芒种前后的集会便显得热闹异常。
小学生们更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在布谷鸟的声声鸣叫声里,眼巴巴地盼着。终于有一天他们盼到了一纸《夏收公约》:放麦假了!于是娃娃们推搡着、打闹着,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定下了这个夏收捡拾麦穗的目标。
村里许多房前屋后的墙壁上,也被人们刷上了许多诸如“快收快打,颗粒归仓”、“当心火灾,安全夏收”的标语。夏收的气氛一下子被渲染了出来,人们立即感觉到紧张了许多。
夜深了,巷子里终于静了下来。突然,不知谁家的院子里传出嘶啦嘶啦的声音,这一定是睡不着的人们在磨着镰。是呀,在这个即将收获的夜晚,谁能睡得着呢?因为,今天芒种一过,明天就要开镰割麦了!
1.
2.
3.
4.
5.
6.
芒种节气的
赵城百姓流传着一句民谚:“收秋打夏,别误了存才的《挂画》。”这是用衬托的手法称赞蒲剧名角的精湛技艺哩!其实,农忙时节,即使素有雅兴的农家戏迷,也是不肯看戏的。
过了六一儿童节就要交芒种,夏收在逼近。时常想起过去收麦时节的一些事儿。
五十多年前兴修水利,从霍泉挖渠引流四五十里,我们村里才有了大片的水地。每年,芒种到了,旱地麦就先“开镰啰”,村民们马上会百倍地紧张起来,一时间农村里呈现出一种“龙口夺食”的繁忙气氛。因为在随后的一个多月的收麦期间,农家人有三怕:狂风乱胡刮,冷子满地砸,促雨淋麦场。假如丰年歉收了,没能颗粒归仓,简直就是割农民身上的肉,要农家人的命啊。
农谚说:“收麦要有八十三场雨。”即八月种麦雨,十月过冬雨,来年春天里返青、拔节雨。人们盼望风调雨顺,就是要降水到节令上。有了大水渠,庄稼就有保障;浇地也要浇到点子上,在庄稼生长的每个阶段不能缺水。你再想,人们从明姜“四月八会”就为收麦做准备:不是修木杈买木铣,就是挑镰刀选扫帚。望着路边的滚滚麦浪,心里盘算着将要大打一场声势浩大、场面壮观的“农民战争”:一群群人马奔向黄蜡蜡的田野里,弯腰挥动镰刀,真像鸭子凫水,身后面紧跟着搂铺捆束麦个子“妇女组”,第三队人马肩挑的挑,车拉的拉,通往麦场的路上,好像蚂蚁搬家似的,好不热闹。战斗的打麦场里的妇女们,追赶催促着挂碌碡碾场的牲口,她们翻呀翻、抖呀抖、起呀起,放下耙舞扫帚,挥汗如雨。怪不得人们把夏收叫做“打夏”,因为小麦脱粒重在三快(快割、快运、快打)得“打”字上:一者凭人力拿连枷拍打,二者靠畜力用磙子碾压。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在祖宗传下的土地上劳作,比刀耕火种能进步多少呢?
麦场一般在村子边上。在缺少机械运输工具的时代,把远近地块割倒的麦子集中到场院里起来,既花时间又费力。有时就近磙压临时野麦场:大麦成熟早,芒种前就可收获;麦茬地经过深翻后,再进行一番耙耱,洒水、滚压,最后,用葫藜条耱子弄瓷实了,正好救驾碾打麦。
那些老扇车闲置了;扬场是技术活,也是男人的专利。那些碾压脱粒后待扬的麦堆如小山似大坝,好把式们要趁晚风借月光一木锨一木锨扬干净麦粒。一场起了堆马上就摊场,连场碾压,巴不定那一天,一阵阵忽雷闪起落下臭雨,麦子泼场了;连夜子生出了黄芽芽:那将是农民的一大不幸啊。
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人不少,工效低;地不少,产量低。一季下来,拨拉算盘后,按人口也分不到多少糊口的粮,又有谁能解决农民的吃粮问题呢?
毕竟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夏收期间,渐渐地在集体麦场里有了拖拉机曳挂着双排架子碌碡在飞奔旋转,渐渐地听见打麦机彻夜地隆隆地响。那些年,农村里有时放映露天电影,银幕上出现农业机械化的镜头时,村里人无不欢呼雀跃,好像明天就能看到现实中的景象。然而,那是一个身心疲惫的年代。
今天,功能各异的农业机器先后出现在田地里。打夏时,看着联合收割机开进麦地里,只消等着拿粮袋装麦颗。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
芒种节气的散文【篇二】
蝉的话一多,阳光的味道越来越浓。青青的秧苗舞蹈在村姑的指缝。
麦穗举起头颅,在民歌声中受孕,丰收的希望在汗水里灌浆。河流越淌越细弱,弱得经不起阳光轻轻的抚摸,丰肥的是牛曲,却被父亲的鞭子轻轻赶着。
芒种,所有农业节令里比金子还值价,谁也浪费不起他的一分一秒,谁也承受不起这个节令的重担。一出秋天的节目就在这时彩排,在大地上,鹧鸪声斯力竭的报幕,唤出一套套伺候农业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土地上完成。
种子们纷纷从冬天的回忆里出发,从乡妹子温情的眸子里出发,他们要越过锄头的肩膀,他们要翻过镰刀的门槛,重先回到农人的粮仓。因此这更确切的说是一个节日,常有天边的滚雷为他们的出发击掌。
牛啊,别被一丛青草留住目光,你每一枚足印都是粮食通向人们肠胃的关健印章。
芒种节气的散文【篇三】
芒种,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而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正如林清玄所写的那样,背负着稻子,承担着麦穗,吹拂着高粱的波浪,散发着六月的的光芒……芒种时节,不但是文人笔下“东风染尽三千顷,折鹭飞来无处停”的田园诗意,也是“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粮”的怡然自得,更是农家“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打火夜插秧”的紧张,还有“连种带收、样样都忙”的辛劳和五谷丰登的愿望。
“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忙”。芒种时节,承接着春播夏华,背负着一年的幸福和希望,抢割、抢运、抢晒,忙着收获成熟的金黄色,翻耕、挖渠、载秧,忙着播种绿色的硕果。广袤的原野田垄上,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处处是古铜色脊梁。黎明的晨光里挥舞的银镰闪烁着丰收的喜悦,日上三竿的时候,如雨的汗珠滴落在割下的麦穗上,抹一抹满脸的汗珠子,就着大葱卷起的煎饼,把一捆捆的成熟送给了新的生活。“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镜面似的秧田里,俏丽的姑娘宛如散花的天女,把绿油油的禾苗抛向天空,灵巧飞快地插上了青秧行行。
走进一望无余的田间地头,呦黑的土地饱尝了艰辛的汗水,躬耕的田亩亮出了一道风景。前几天的金色麦浪变成了如今的碧波荡漾,鲜活的乡野让旧容换了新颜,辛劳的耕耘把点点的淡绿变成片片的深绿,把片片的深绿融成墨绿的海洋。
眼望轻风拂起的绿浪,捕捉一组芒种的节气季歌,醉人的气息,经历了夏日的雨淋,经历了熏风的陶染,经历了辛苦的耕耘,缓缓的融入秋日的成熟,采摘高阳下希望。
1.
2.
3.
4.
5.
6.